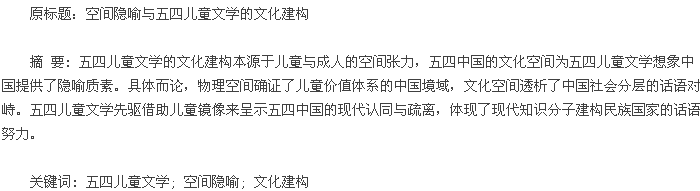
五四儿童文学作家结合中国的现实塑造了一系列儿童形象,通过这些儿童形象,我们可以揭橥其与中国形象之间的微妙关联。由于“民族政治”对文学的楔入,五四儿童文学无法获得纯粹书写儿童世界的条件,儿童世界之外的儿童本体、社会语境、民族国家建构等问题也被纳入了儿童作家的文学视野。以儿童的成长为中心,将其置于中国特殊的时代语境中,这种文化空间与儿童的成长之间的关系折射出作家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思考。五四儿童文学中环绕儿童本体的空间形态参与了其文化想象和价值建构的过程。具体而论,物理空间、文化空间构成了其空间结构的两个重要组成要素,它们的联接和互动构织出了五四中国的情境现场,也为五四儿童文学想象中国提供了参照场域。
一、物理空间: 确证儿童价值体系的中国境域
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得中国爆发了强大的民族危机,在对中国社会强大的劣败感受中,国人在注目于外国文明的伟力的同时也将关注点返归中国本土,开启了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反思之路。要建构“现代中国”必须要直面中国现存的境遇,在意识到“中国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要建构现代中国”等问题后,基于这些中国问题来设计“现代中国”的具体形态。循此逻辑,五四知识分子自觉地将儿童的存在体验延伸于民族与国家深层结构的思考之中,予以整体观照和辩证推演,扩充了其探询社会人生问题的思维视域。
五四儿童文学先驱多将儿童置身于封闭逼仄的房屋、祠堂、客厅、街道、十字路口、宿舍、茶馆、药铺、饭场、坟场等空间,其主导的空间基调和氛围黑暗且阴冷: 汪敬熙的《一个勤学的学生》) 中有,“各房间里全是黑黢黢的没有一点儿灯光。”[1]杨振声的《渔家》中有,“那窗上的纸经雨一洗被风斗吹破,上面塞的一些破衣裳。所以那屋子里面十分惨淡黑暗的了。”普生的《完卵》中有,“天气越发阴得重了,刚才灰色的天空现在变成深黑色了。”[3]王统照的《春雨之夜》中有,“黄昏过了,阴沉沉的黑幕罩住了大地。虽有清朗月光,却被一层层灰云遮住,更显得这是一个幽沉、静美、萧条的春夜。”[4]王统照的《湖畔儿语》中有,“本来这个地方是很僻静的,每当晚上,更没人在这里停留。况且黑暗的空间越来越大,柳叶与苇叶还时时摇擦着作出微响。于是我觉得有点恐怖了。”[5]王思玷的《偏枯》中有,“金日脚从大殿的红山墙映到了小院子里,像一片血雾。人们的愁惨的面庞,都像浴在血里。”[6]孙俍工的《隔绝的世界》中有,“在一阵很冷酷的雨点飞过去了以后,接连着的就是一股寒凄凄的风夹着黑墨的夜,紧紧地压迫而来,差不多使那李在大街后面的那楹茅房很凄凉地打了几个寒颤。”[7]这里所书写的物理空间呈示出的主色调是压抑和逼仄的黑暗,它是儿童生存的现实境地,黑暗的空间给人的生活投射了令人窒息的重压。与此相关的是,很多五四儿童文学的故事情节的时间点主要设置在“深夜”或“冬季”。
为什么要将故事放置于这样一个时间点上呢? 这主要因为这些时间点隐喻了一种悲凉黑暗的氛围,与强大的空间一起,构成了“非人间”的时空体。黑暗进一步加速了空间的移位和消歇,进而模糊了空间的界限。既然没有边界,那么也就没有中心。那无处不在的空间重压显然不是从某一个固定的方位延伸出来的,它更像是一张巨大而无形的网,看不见、摸不着,却始终发挥着作用。
在这里,与其说空间是一种方位参照体系,毋宁说它是一种价值反映体系; 它不仅是人物活动的场所,而且还作为一种文化情境参与了人事的进程。
正如鲁迅所言,“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8]。这种空间呈现形态给人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重压力,儿童被置于一个由黑暗和虚无主宰的空间之中,没有“过去”可依,也没有“将来”可望,主体拥有的只是瞬息之“现在”。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讨论社会“结构化”时,尝试将空间概念作为研究人类生活模式以至社会形成的结构因素。按其说法,“场所可以是屋子里的一个房间、一个街角、工厂的一个车间、集镇和城市,乃至由各个民族国家所占据的有严格疆域分界的区域”[9]。人在具体的生存实践中利用空间的不同方式或手段,直接决定了空间的文化特征。刘半农的儿童诗《相隔一层纸》并非直接描写儿童,而是用朗朗上口的诗句书写不同阶层之间的障碍与距离: “屋子里拢着炉火,/老爷吩咐开窗买水果,/说: ‘天气不冷火太热,/别任它烤坏了我。’/屋子外躺着一个叫花子,/咬紧了牙齿对着北风喊‘要死’! /可怜屋里与屋外,/相隔只有一层薄纸! ”作为五四儿童诗的先驱,刘半农的这首儿歌中渗透了非常强烈的阶级间的矛盾与差异,“屋内”与“屋外”的空间厚度只有一层薄纸,然而却有着天壤之别。刘半农借助儿童诗来表达对“成人世界”的看法,想要传达给儿童的也是这种成人世界的经验。
叶圣陶的《小铜匠》对此问题也有深刻的揭示和书写。陆根元是一个很难适应高等小学的学生,在他的意识中,自己与周围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小说的开篇细腻地描摹了他的内心感受,“觉得与平日有点两样,周身不大舒服,但是形容不出”; 在周围好奇的目光中,他“只想什么地方有个洞,自己隐藏在那里,不让他们这么看”; 站在操场上,“他觉得自己的微小,飘飘然几乎没有重量,差不多不能稳定地站着”。他很难融入这样一个学习的空间氛围之中,失望和孤寂始终围绕着他。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变成这样呢? 其原因是他的母亲去世了,父亲出去了,剩下他一个人。他的生活被“悲哀的网网住了”,“仿佛周身在哪里压迫拢来”,使得他无力承受“先生们一样的威严”以及同学们的冷眼,这种外在空间的重压让这个孩子失去了同龄人该有的快乐,成为一个被老师遗忘和忽视的“低能儿”。对于这种现状,王统照在《湖畔儿语》的最后深刻地将此问题揭示出来: “家庭啊! 家庭的组织与时代的迫逼呀,社会生机的压榨呀! ……这样非人的生活!
现代社会组织下贫民的无可如何的死路! ……同时,我静静地想到每一个环境中造就的儿童……使我对着眼前的小顺以及其他在小顺的地位上的儿童为之战栗! ”在这种境地中,儿童纯洁善良的天性被社会强大的力量压制着、摧残着( 徐玉诺《认清我们的敌人》) ; 儿童美好的梦想只能化为泡影( 王统照《雪后》) ; 儿童灿烂的笑容也只是“最后的安息”( 冰心《最后的安息》) ……在一切意义和价值被抽空的语境中,黑暗和虚无切断了生命之流,世界是一个缺乏连续性的时空体,整体运动着的历史消逝了,人际关系陌生而反常。在静态的时间中流逝的生命无处栖息,主体存在的意义被遮蔽了。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一切都令人怀疑,于是人们就只能在这种不确定的怀疑和焦虑中,感受着存在意义的不在场性,行为的意义悖谬由此生成。在这里,儿童文学作家不仅要呈现儿童的现实际遇,而且还要反思在现实境遇面前儿童的反应和精神状态。五四时期的儿童书写主要还在揭示“儿童问题”,出发点还是“为了儿童”。只有经过了“为了儿童”的现实考虑之后,才有更深层次的“为了把儿童纳入想象的共同体中”[10]。
在五四儿童文学作家的意识中,空间充当了判定儿童价值的容器,他们既发现了那些被空间吞噬的“弱性儿童”,又试图发掘那些对抗空间的“强力儿童”。当然,前者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后者,多数儿童在这种空间的重压下表现出无助且无奈的精神状态。如在床上温着美梦,呆呆地不愿起来的小峰( 汪敬熙《一个勤学的学生》) ; “脑子里所充满的只有悲苦恐怖,只昏昏沉沉地度过那凄苦日子”的翠儿( 冰心《最后的安息》) ; 在主人的逼问面前,俯着头、垂着手,“表示出脑筋的作用停滞的样子”的阿美( 赵景沄《阿美》) ; “仿佛一只小鸟中了弹子将要毙命”的小孩( 孙俍工《隔绝的世界》) ; “如同从远处跑来的一个陌生人,默默地坐着,缓缓地行着,呆呆地侧看着”的霍君素( 王统照《纪梦》) ,等等。正如露丝·本尼迪克所说,“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11]这种集体记忆形成强大的思维定势,剥夺了主体修改和涂抹自己以往记忆的认知自觉。要超越既定的空间秩序意味着背叛,而这种背叛所滋生的心灵重负势必会动摇主体的行动和思维意识的生成。在五四知识分子的思维意识中,这种空间文化中的“奴性人物”是没有时间性的,只有空间性,他们只想适应环境( 空间秩序) ,最终只能被环境( 空间秩序) 所改造。在面对现实空间秩序的挤压时,很多儿童不能调节和整合自己的空间意识。他们只能无奈地去适应而不是去反抗,在没有怀疑和否定的永恒常态中艰难地获取自我的生存保障,确立自己的社会定位和人生选择。
可以说,传统的力量化为空间的秩序,将其影响延长到现在时段中来。在这种封闭和沉滞的物理空间中,外来文化讯息是无法折射和渗透进来的,儿童即使获得了某些现代文明的信号,也难以真正形成自觉的意识,最终被习惯的规则和日常的秩序吞噬得无声无息。当然,也有这样一些儿童,他们能调节和整合自己的空间意识,他们的精神始终流动,在虚无的空间境地中绽出可贵的生命意志。在叶圣陶的《阿凤》中,阿凤对于婆婆的打骂始终保持坚忍的精神意志,在作家看来,“伊这个态度,有忍受的、坚强的、英勇的表情”。在赵景深的《红肿的手》中,面对“我”的刁难,小全用“我不”、“我不去玩”、“我不跪”这样的否定语言予以反抗,这在我看来有一种“英雄”的样子。当然,儿童主体地位的确立是建构未来中国的第一步,如果儿童不能在现存的空间境域中彰显作为未来国家的“人”的品格,那么其之于未来中国的价值也只能是缺席的。因此可以这样理解,上述这种空间境域为儿童的主体价值的确立提供了检验的平台,只有那些离弃了沉沦状态,拥有自我独立的精神品格,领悟未来筹划的儿童,才能摆脱成为他人的影子和化身,成为未来国家的精神支柱。
二、文化空间: 透析中国社会分层的话语对峙
通过对物理空间背后文化意义的探究,为我们研究中国社会空间的文学分层提供了条件。物理空间与文化空间一起,构成了五四儿童文学想象中国的重要畛域。伊夫·瓦岱说过: “传统社会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它的影响足以说明传统思想体制特点( 我们也可以用神话思想一词来概括它) : 这就是既存在于空间也存在于时间中的绝对基准点。”[12]这意味着传统的思想和精神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它会形成一种权力,渗透于主体存在的时空体中,以此来影响、规训个人的行为,对个人的行为进行道德判断和价值评定。在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中,有形的空间位置的秩序是与无形的文化身份、价值秩序联系在一起的,是具有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和规范人言行的重要载体。
在五四儿童文学作品中,“儿童”与“成人”的对立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中最为基本的关系网络,他们拥有着不同的话语体系,其对峙与冲突表呈了中国社会分层的文化特质。五四知识分子意识到了儿童与成人的对立,并将其视为儿童文学内在文化构成的重要维度,予以审视。冰心以小孩子的口吻十分贴切地写出了两种群体的区别: “大人的思想,竟是极高深奥妙的,不是我们所能以测度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是非,往往和我们的颠倒。往往我们所以为刺心刻骨的,他们却雍容谈笑的不理; 我们所以为是渺小无关的,他们却以为是惊天动地的事功。”[13]颇为相似的是,周作人通过对儿童游戏习性的考察,发掘了成人与儿童的重大分歧: “现在,在开化的家庭学校里,游戏总算是被容忍了; 但我想这样的时候将要到来,那刻大人将庄严地为儿童筑“沙堆”,如筑圣堂一样。这些东西在高雅的大人先生们看来,当然是“土饭尘羹”,万不及圣经贤传之高远,四六八股之美妙,但在儿童我相信他们能够从这里得到一点趣味。”[14]五四儿童文学中处处可见儿童与成人的对立,成人或者是家庭的主宰者,或者是学校的教育者,他们要么扮演不经意的“闯入者”,要么扮演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启蒙者”。儿童与成人并非完全和睦相处,他们之间的冲突从未停止过。在《一课》中,叶圣陶指出,儿童最为核心的一种精神品质就是“动的生命”,主人公连上课也念念不忘随身带着的蚕,想着和其他小朋友一起泛舟的乐趣。在他的眼中,严肃的教育课堂只是正襟危坐的成人一厢情愿的安排,这一点也不适应于他。
他的思绪随着蝴蝶飞到了窗外,深密的相思开始了,在窗外自然之声与室内沉滞之声的对照中,“他不再往下想,只凝神听窗外自然的音乐,那种醉心的快感,决不是平时听到风琴发出滞重单调的声音的时候所能感知到的”。在其另一篇小说《义儿》中,义儿不满陈腐的教育,他与成人( 老师) 的对立是很直接的,他大胆地回击成人对于他的无理斥责,公然挑战教育体制。对此,顾颉刚指出,《义儿》是可以和《一课》合看的,“明明是很有生趣,很能自己寻出愉快的小孩,但社会上一定要把他们的生趣和愉快夺去了。甚至于最爱他的母亲,也受了社会上的暗示,看着他的生趣和愉快,反而惹起了她的恼怒和悲感”。这种对立正如叶圣陶的《小铜匠》中根元的级任老师所认定的他与学生的关系: “我们与他们,差不多站在两个国度里,中间隔着一座又高又厚的墙,彼此绝不相通。”那么,两者能否有融通的可能呢?
小说中有人接着提出“你先生何不把这座墙打破了?”此话一出,“大家默然”。由于对立的双方都有一套自足的话语系统,都打上了主体意识的话语“密码”,所以当两套相异的话语碰撞时,对话交流常常以“中断”收场。“双向隔膜”的话语排斥力就产生了。拥有话语优势的一方总是以压制的方式规约着事态的进程,彰显出符合话语权力者的价值取向。相反,儿童和儿童之间似乎有着能超越身份、地位的和谐关系。叶圣陶的《阿凤》中有这样一个场面: 当杨家娘当着我的三岁的儿子打骂十二岁的阿凤时,“他终于忍不住,上下唇大开,哭了”。这里有“恐惧欲逃的神情”,更有儿童之间心灵的自然相通,“我从他的哭声里领略到了人类的同情心的滋味”。冰心《最后的安息》刻画了两个完全不同出身的小女孩,他们的友情和心心相惜勾勒了一幅美好的图画,与上述儿童和成人之间的关系有着极大的差别: “她们两个的影儿,倒映在溪水里,虽然外面是贫,富,智,愚,差得天悬地隔,却从们的天真里发出来的同情,和感恩的心,将她们的精神,连合在一处,造成了一个和爱神妙的世界。”当然,这种美好的人际关系只能发生在儿童之间,一旦有成人的介入,一旦这种关系牵扯上更为复杂的社会网络,就变得不那么简单和纯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一些“特权儿童”身上的某种优越身份( 富庶家庭出身) ,使得他们的思维、行为、心理与一般的儿童有了区别,他们世俗味很重,颐指气使,他们与成人一道虐待处于社会底层的儿童,自动地将自己与其他儿童区分开来。如毫无同情心地向另一个小女孩嘴里塞进劈柴刀把的青莲( 徐玉诺《认清我们的敌人》) ; 又如随意折磨、打骂贫困儿童小全的“我”( 赵景深《红肿的手》) ,再如随意支配阿美生活,把她当成玩耍工具的少爷( 赵景沄《阿美》) ……他们的行为完全缺失了儿童与儿童之间的心灵沟通,构成了成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毕竟后者的关系更为直接和现实,也更为真实地体现当时社会结构的关联。社会空间“允许某些行为发生,暗示另一行为,但同时禁止其他行为”。空间对个体的行为的规约和约束是始终存在的。儿童和成人的冲突往往会生成多样性的权力关系,但是,这种空间位置的僭越是有界线的,僭越和界线相互依存,界线如果无法僭越,那界线的意义就不存在了; 同理,僭越如果毫无阻力,那它也毫无意义可言。在这种界限和僭越的双向互动中,彰显了彼此所表征的文化特质及社会现实境域。
“儿童”的独特意义在于其与“成人”的对立性,而且彼此互为他者。“他者”身份的确立为“自者”身份的建构提供了条件。“人类理解自我的方式就是要把自己所属的人类群体划出来,与先于自己的群体以及自己进化后脱离的群体相区别。确切地说,成人被理解为非自然、非兽性、非疯狂、非神性———最重要的是,非孩子性。”[16]可以这样理解,认知的最好途径并非站在自我的视角上来理解自我,相反,从对立者的角度来反观自我也许是一种相对深刻和理性的认知方式。儿童与成人的对立展示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层,两者的张力对峙深化了儿童文学的内在涵量。一个显见的道理,五四众多知识分子对于儿童自然属性的推崇,其实质是对于成人世界缺失了这种美好性灵的批判。丰子恺的话可能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心声: “在那时,我初尝世味,看见了当时社会里的虚伪骄矜之状,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于是变成了儿童崇拜者,在随笔中,漫画中,处处赞扬儿童。现在回忆当时意识,这正是从反面诅咒成人社会的恶劣。”[17]儿童与成人各站立于文化空间的一端,彼此相互参照。综上,这种双向力量的较量、抵牾,意向在空间中的纠合和参照,使得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视域有效地融汇在一起,从而生成出“包围—突围”的叙述空间。当然,在时间向度上,这两条情节线以不同的速度、节奏和频率纠合在一起: “包围”折射了外在社会历史演进的诸多讯息,打上了作家较强的社会历史批评色彩; “突围”所显示的则是主体内在时间意识的价值取向,作家深刻复杂的意识流动从中得以窥见。在这种流动的空间里,意义可从多语义、多层面予以观照、生成、展现,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有机地联接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在五四情境中,尽管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有着较大的差异性和非对等性,但是它们最终还是融通于“想象中国”的宏大叙事之中。
三、空间的互动与文学话语的张力
五四新文学“拿儿童说事”直指“老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在破旧立新的逻辑中,开启儿童文学想象中国的伟大工程。如前所述,儿童与中国之间存在着可以相互建构与想象的空间,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探究五四儿童文学作品中所营构的儿童形象,揭橥符号表意系统呈示中国形象的可能性形态及精神表征,以此探究五四中国的现实境域与未来中国的文化走向。
就五四儿童文学而言,儿童并非创作主体,他们只是成人知识分子观照和审视的对象,正因为儿童作家的缺席,使得儿童没法站在自我的角度上言说自我,儿童的书写和言说只能依靠成人来完成。质言之,儿童形象的营构并非儿童“自塑”而是由成人“他塑”来完成的。这样一来,围绕着儿童主体的儿童观念、儿童翻译、儿童教育、儿童形象、儿童思维、儿童审美等范畴的建构是基于成人的自我考虑,即通过他者来确立自我。然而,即使成人设身处地地站在儿童的角度来言说儿童,也难以消除儿童与成人微妙复杂的差别。这使得这一时期的儿童作家陷入了难以平复的两难境地: “一方面他们界定儿童、开创儿童世界就必须拉开儿童与成人的距离,强化儿童的非成人性; 另一方面他们要阐发成人的启蒙理想又不能放任儿童超然的非成人性,必须再一次拉近儿童与成人之间的距离。”[18]拉开儿童与成人的距离容易办到,中国自古就比较漠视儿童的自主性,将其称为“缩小的成人”,五四知识分子在肯定儿童的主体性的同时将儿童与未开化的原始人进行比照,肯定他们的自然天性。这种言论从生物进化学的知识上升到人类学的视野来考量儿童的心理、爱好、特质等问题本无可厚非,这也很好地为他们宣扬“儿童本位”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正是这种将儿童与原人的类比,顺理成章地将儿童从成人主宰的社会网络中疏离出来了。然而,这种疏离并不意味着切断了儿童与成人的内在关系。在启蒙为主潮的五四时期,儿童与成人一样,都不能脱离其所在的社会现实,两者都承载着设计未来民族国家的使命,这要求成人作家将自我的理想与儿童的理想有机融合在一起,儿童的成人性必须彰显,而这又与前面所述的儿童的非成人化发生了抵牾。可以说,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依赖成人的话语参与,成人教化和启蒙儿童,也在此过程中确定了两者的空间身份。两者的生命形态也因空间话语的此消彼长而呈现出殊异的轨迹。
时间与空间是始终扭结在一起的,谈论儿童的时间意识实质上是儿童在特定社会空间及文化空间的时间感。这其中,儿童的生命感将时间和空间联接起来: 儿童在空间中,但儿童不仅仅是空间的构成物,他有生命,时间才被呈现。儿童将其生命意识注入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才会具有儿童的时间性。五四儿童文学想象中国的时间隐喻是通过空间场域中儿童的生命体验、感知来呈现的。质言之,存在如下两种截然不同的时空图示:
一是儿童生命被动地钳制于既定空间,自身成为空间的一部分。这是一种不流动、静态的时间形式,空间并未因儿童的生命存在而改变其所辐射的话语形态。在这个空间形态中,儿童生命是被动的,时间是被给予的,儿童的成长被吸附于僵硬的空间结构中而窒息。如那些麻木、无语的儿童庸众,那些无助且无反抗的病态儿童,毫无痛感地接受了外在空间赋予的命运。由于他们的生命被他们的“奴性”、“愚昧”等消耗了,因此,生命是无时间性的,他们也不可能创造了自己的时间,他们的生命的时间静止了、停滞了,最终完全变成空间性的。
二是儿童生命反抗空间的吞噬,自我生命赢得时间。在个人和社会并立的空间中,儿童用成长去充盈和创造空间,通过其行为的冲击去获致时间的意义。与前者不同的是,它是一种流动的、可能性的时间形式。如那些不被命定的新儿童,他们在空间的压迫和同化的情境下,意识到了本真存在的意义和绝境处境中的自我主体,或者“外突”,或者“反抗”,将其成长注入了生生不息的动力。这时的生命就是时间性的,并孕育了创构全新的时间意识和生命形态的可能。
应该说,五四儿童文学先驱对于儿童成长的考察源于其对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全面洞悉。儿童的成长所隐喻的时间意识不仅是儿童社会化的表述而已,也是观照儿童之外的民族国家精神气质的话语资源。这使得儿童成长书写超越了私人化的展示,而有了公共社会性的架构和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汪敬熙. 一个勤学的学生[M]/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小说( 一) . 太原: 希望出版社,2009: 3.
[2]杨振声. 渔家[M]/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小说( 一) . 太原: 希望出版社,2009: 6.
[3]普生. 完卵[M]/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小说( 一) . 太原: 希望出版社,2009: 24.
[4]王统照. 春雨之夜[M]/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小说( 一) . 太原: 希望出版社,2009: 27.
[5]王统照. 湖畔儿语[M]/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小说( 一) . 太原: 希望出版社,2009: 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