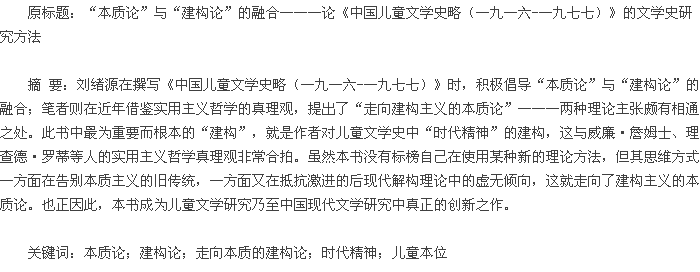
刘绪源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一九一六– 一九七七)》①(以下简称《史略》)是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收获,其中有很多新的思考和真的发现。
我试图整理这本着作的研究理路和学术价值的时候,思绪中不断地出现另外两部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着作:杜传坤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②(以下简称《史论》)、吴其南的《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③(以下简称《文化阐释》)。为什么在我要评价《史略》时,会出现这两部着作如影随形的情况?思量之后才明白:刘绪源的《史略》与杜传坤的《史论》和吴其南的《文化阐释》这两部着作,提供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儿童文学史研究的方法和观念。
本文是要对刘绪源的《史略》作出学术评价,不过,如果引入《史论》和《文化阐释》这两个参照物,将更有利于看清刘绪源的《史略》的及时而可贵的学术价值,将我们对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思考,朝着正确的方向,更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下去。
一、《史略》:建构主义的文学史观
在《史略》一书中,刘绪源颇有用意地作为“附录”,收进了《“建构论”与“本质论”———一个事关文学史研究的理论问题》一文。这是一篇意味深长的文章,触及了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的重大分歧。简而言之,刘绪源批判了杜传坤在《史论》一书中反“本质论”(刘绪源称其为“离开了本质论的建构论”)的解构主义文学史观,倡导“本质论”与“建构论”的融合:“离开了本质论,建构论就是无本之木;同理,离开了建构论,本质论就是无源之水。建构论只能是对本质论的补充、修订或补正,当然偶尔也会有革命性的重建,但从根本上说,不可能取代本质论。 ”“建构论和本质论,合则两立,分则俱伤。 ”
①最近,我增补、修订拙着《儿童文学的本质》,在批判近年儿童文学学术界的几位学者反“本质论”及其造成的不良学术后果时,借鉴实用主义哲学的真理观,提出了“走向建构主义的本质论”这一理论主张。我以为我所主张的建构主义的本质论与刘绪源的融合本质论和建构论的主张颇有相通之处。不过,我也想就建构主义的本质论的含义稍作申明。我的建构主义本质论建立在后现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真理观基础之上。罗蒂说:“真理不能存在那里,不能独立于人类心灵而存在,因为语句不能独立于人类心灵而存在,不能存在那里。世界存在那里,但对世界的描述则否。
只有对世界的描述才可能有真或假,世界独自来看———不助以人类的描述活动———不可能有真或假。”“真理,和世界一样,存在那里———这个主意是一个旧时代的遗物。 ”②罗蒂不是说,真理不存在,而是说真理不是一个“实体”,不能像客观世界一样“存在那里”,真理只能存在于“对世界的描述”之中。正是“对世界的描述”,存在着真理和谬误之分。同样,在人文学科领域,本质也不是一个“实体”,本质不能像客观世界一样,“存在那里”,本质只能存在于人“对世界的描述”之中,即本质是由人的语言“建构”出来的。
《“建构论”与“本质论”———一个事关文学史研究的理论问题》一文发表于二〇一〇年九月。这时,《史略》一书有了计划,但尚未动笔。我认为,刘绪源是以此文在思考自己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方法。他在质疑杜传坤的具有xuwuzhuyi色彩的后现代解构方法的同时,也认定了他要采用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只有谦虚地承认既有的本质,充分尊重人性的和文学的传统,在本质论的基础上尝试新的建构,我想,我们才有可能达到新的境界”。
③但这是在理性意识的层面,其实,在实践中,他却不自觉地同时运用了后现代的建构主义方法。因此,在我眼里,刘绪源的《史略》采用的就是建构主义的本质论。
刘绪源所质疑的杜传坤的《史论》一书的“建构论”,其实恰恰是没有建构能力的“解构论”。吴其南的《文化阐释》也基本与杜传坤的《史论》是同一种情形。在《史略》中,刘绪源并没有像本质主义那样,将儿童文学看作是像石头一样的不言自明的实体,而是当作观念的建构物。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独具慧眼指出了从未有人指认过的儿童文学: “在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开山作品———《尝试集》中,儿童文学其实占了一半以上! ”④文学的历史有没有规律?作家作品、文学思潮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文学史中重要事件的发生是纯粹偶然的,还是存在一定的因果逻辑关系?对这些因“现代性”与“后现代”理论发生碰撞而产生的文学史研究上的问题,刘绪源与吴其南有不同的回应。吴其南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曾出现过许多文学思潮,虽然前后也有时间的连续,但更多时候则呈现为一种并列关系”。⑤吴其南虽然用了“虽然”、“但”这样的词语,表示前后事物有区别,但是,“时间的连续”与“并列关系”其实是同一种形态。吴其南想说的是,“文学思潮”之间并没有因果、逻辑关系。所以,他“遵循文化本身的现实,本书的结构也是桔形的”。总之,在他笔下的儿童文学史,“许多文学思潮”不会发生交集关系,而是像桔子瓣儿,单摆浮搁地拼凑在一起。
在放弃本质论研究的吴其南眼里,中国儿童文学史这个“世界是一头洋葱,除了洋葱皮还是洋葱皮,洋葱就是由一层层洋葱皮组成的”。⑥于是,我们在《文化阐释》一书中,清清楚楚地看到,信奉“解构论”的吴其南放弃了对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进行“真理”的建构。
但是,刘绪源则与吴其南恰恰相反,他的《史略》“是对近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中比较优秀的创作的鉴赏与批评,同时也在努力寻找它们之间的关系”。①“笔者认为,文学史不应只是系列评论的汇拢,也不只是史料长编,文学史写作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能发现不写史、不从史的角度研究就无从看到的秘密。所以说,文学史写作是要研究这一段历史中特有的文学问题和与文学相关的问题,找出此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性的东西来。亦即运用史的眼光,通过史的视角,给关注某一时段文学的人们提供有益的参照。 ”②这样的文学史观就与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夏志清、写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顾彬不谋而合了。顾彬自信地说:“我所写的每一卷作品都有一根一以贯之的红线。 ”③同样,夏志清写《中国现代小说史》,也在企求“从现代文学混沌的流变里,清理出个样式与秩序”。④刘绪源的文学史观,甚至与主张解构主义的郑敏也有相通之处。郑敏说:“我们能对这种文本间、文史间、文学与人之间的踪迹作出一些阐释,找出一些内在关联,我们就写成某一种文学史,而且是穿透现象外层的文学史。
这种史观也迫使我们更多创造性地去钻研作品及作品间的关系,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将作者生平、作品分析按照编年史的方法汇集起来,作为史实的资料。 ”⑤上述可见,刘绪源关于文学史研究方法的思考,其思想是透彻的,其目光也是深邃的。
我想这与他坚持本质论研究立场直接相关,因为本质论研究必然会具备凝视、谛视、审视这三重目光。而杜传坤的《史论》和吴其南的《文化阐释》之所以在思想体系上混乱不堪,在学术主张上矛盾频出,同样是因为他们采取反“本质论”这一学术立场,放弃了凝视、谛视、审视这三重目光。
二、“儿童本位”论:《史略》的“一以贯之的红线”
我这里要着重谈的是刘绪源在《史略》一书中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建构”,那就是成为他的儿童文学史研究之灵魂的“时代精神”的建构。刘绪源在《史略》一书中反复论述到“时代精神”。他说:“纯文学要有先锋性———这也就是时代精神。这里的先锋性,既指文学形式上的,也指文学内容上的,也就是,作品要给一个时代的文学带来新东西,要有新突破。
而且这突破是通过审美的方式实现的,它不是借文学作品说思想,更不是图解一个时期的政治或政策(过去那些被称为有时代精神而其实只是图解概念图解政治的创作,其审美价值恰恰是最成问题的)。 ”⑥那么,如何确认时代精神呢?
刘绪源又说:“当时代向前了,回过头来看,过去那些声音,是不是真理,或是不是最高形态的真理,它将一目了然。用现在的话说,此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时当地的声音,因为有权利或金钱的支撑,在某一阶段放得很大,并且自称为最高真理,这并无大用,因为还要等待时间的检验,实践的检验。时间一过,真相毕露,鬼话就是鬼话,丑态就是丑态,失败就是失败,这是任谁也掩饰不过的。所以,只有经后一时代确认了的,才是真正的时代精神。 ”
⑦在这里,刘绪源确认“时代精神”的方法就与威廉·詹姆士、理查德·罗蒂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真理观非常合拍了。我认为,刘绪源的《史略》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明晰地建构起了他所认定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时代精神”,那就是“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儿童本位”论成了刘绪源笔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根一以贯之的红线”。刘绪源的儿童文学观是与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一脉相承的。
在《史略》中,刘绪源引用了周作人强调“文学是个人的”,“要叫出他自己所要说的话”以及儿童文学是“为儿童的”,作家应该葆有“赤子之心”这些话之后,说道:周作人“希望作家本人仍拥有赤子之心,这也就使说自己的话和为儿童二者有了交集,也许,这是解决这一儿童文学最复杂的理论问题的唯一方案吧! ”
①在《史略》一书中,刘绪源就是将这“唯一方案”作为一种历史展开中的儿童文学理想来看待的。
不论是从事理论、史论还是评论,儿童文学研究者都应该通过对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建立一个有理想指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并且将其作为建构儿童文学的理想方案的指路罗盘。
在这个意义上,儿童文学研究者需要更为澄明和高远的思想想象力。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来看,如何对待“现代”和“当代”的“儿童本位”论,是检验儿童文学研究者思想想象力之高下的根本性指标。刘绪源是当代“儿童本位”论的重要诠释者之一。
事实上,刘绪源在考察、评价一个甲子的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时,就是拿周作人的现代“儿童本位”论和他自己诠释的当代“儿童本位”论作为衡量的标准。
刘绪源所肯定的,如冰心的《寄小读者》(对此我另有不同看法)、凌淑华的儿童小说集《小哥儿俩》,他都认为符合周作人的“儿童本位”的标准,他所否定或怀疑的,如叶圣陶的《稻草人》(指单篇童话)、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四十年代的政治童话等,也都不符合他参照周作人的理念所设定的当代“儿童本位”论的价值标准。正是因为有了现代和当代形态的“儿童本位”论这条“一以贯之的红线”,《史略》成为“由一种生命气息吹嘘过的”(歌德语)儿童文学史着作。
三、“一个历史学家必须先是一个批评家”
韦勒克说:“文学研究不同于历史研究之处在于它不是研究历史文件而是研究有永久价值的作品……研究文学的人能够考察他的对象即作品本身,他必须理解作品,并对它作出解释和评价;简单说,他为了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先是一个批评家……除非我们想把文学研究简化为列举着作,写成编年史或记事。 ”
②(想到杜传坤的《史论》和吴其南的《文化阐释》的实际着述状况,我还想补充一句,除非我们想把文学史写成没有统一的审美价值标准,评价之间可以相互矛盾的“碎片”式拼凑。 )“为了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先是一个批评家”,这是韦勒克对文学史写作提出的一个必须满足的条件。刘绪源作为一个儿童文学批评家是当之无愧的。
不仅如此,因为写作渐露经典气象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一书,他还是一个十分出色、具有原创性的儿童文学理论家。不仅如此,因为写作《解读周作人》、《今文渊源》等着作,他还是一个优秀的成人文学批评家。这些资质,为《史略》的写作带来了广阔而深邃的审美眼光和令人信服的审美判断。
我甚至想起了钱锺书评价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那段话———“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论,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③关于中国的儿童文学史家应具有的儿童文学批评家这一资质,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其批评的视野必须包括世界尤其是西方的优秀儿童文学,因为非如此,一种端正而有高度的儿童文学审美价值尺度便不能建立起来。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儿童文学研究,尤其是儿童文学史研究,没有世界性眼光,就没有看清中国的眼光,因为没有世界性眼光,就会像一个处于自我中心状态的幼儿,不能把中国儿童文学作为一个对象化的存在来把握。作为儿童文学批评家,刘绪源是拥有世界性目光的,他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以及一大批儿童文学批评文章可以作证。
在《史略》一书中,他所放出的经过长期洗练的审美眼光是令人佩服的。 《史略》一书紧紧围绕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进行分析评论,然后以此为主线牵连出文学史的重要“经验、教训和规律性的东西”。
怀着自己努力建构的“时代精神”(思想史的眼光),运用端正而有高度的审美价值观,刘绪源不断地阐述出自己的独到而重要的审美发现。对我曾在拙着《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中指出的,周作人的“儿童本位”理论与叶圣陶的童话创作存在着“错位”这一文学史的重要现象,刘绪源更进一步指出:“《稻草人》这样有明显意图伦理(即有预设的观念,并有很强的说明性)”的创作,“可说是那一时代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主潮和缩影”。①他还具体分析《稻草人》这篇童话:“我感到整本集子里,真正失败的,恰恰是这一篇。 ”②他分析叶圣陶童话创作停笔的原因:“可能也是他无法再往下写了吧?”“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写不下去了。 ”③刘绪源对《稻草人》这篇童话所代表的传统进行了大胆的否定:“叶先生写不下去了,这样的写法却留存下来,并发扬开去。
我想,这本身,也和《稻草人》结局相似,这也是一个文学上的悲剧。 ”④这样的观点,明显具有重写文学史的性质了。对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等童话创作,刘绪源具有辩证的眼光,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其“童趣”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对张天翼“图解概念图解政治”的这种创作模式却是坚决否定的。
刘绪源认为,《大林和小林》有其成功的一面,但是“同时也有极不成功的一面,其不成功处因为有它的成功一面的遮掩,所以贻害更甚!可以说,自此书问世以后,它的消极影响一直在误导中国儿童文学,直到新时期以后还不能真正消除……我所指的,是它开创了一条图解革命理论的文学创作之路”。⑤《史略》一书中独到的审美发现很多,这些发现是名副其实的对文学史的“建构”。
比如,刘绪源发现了“战争”儿童文学中(即吴其南的《文化阐释》中所说的“红色儿童文学”)的一些名着的“带路”模式(小八路把日本侵略军带进包围圈或绝境),从而对儿童文学让儿童参加战争提出了质疑:“这样的雷同,看起来是一个技术问题,再往纵深思考,就能发现,让孩子参加战争(即使只是文学上———文学必然要受到生活逻辑的限制),这本身有多么不合理。 ”⑥刘绪源的这种审美目光是深刻而犀利的,这既源于他对儿童生命的深切理解,也源于他对过去历史的深刻反思。刘绪源发人深省地提出了儿童文学“如何走出战争”这一重大问题。他敏锐地指出:“事实上,战争过后,对于全体人民,尤其是对于儿童,还有一个从生活上和心理上走出战争的工作要做。战争终究是生活的特殊形态,是违背日常人生的常规常理的,即使是正义战争的参与者,在战后也仍需要逐渐平复战争激情,回归日常生活,要让对日常生活的渴望、让日常生活之美重新回到心灵的最重要的位置。
这个任务,我们的儿童文学没有完成(《长长的流水》、《玉姑山下的故事》等少量作品则较好地暗示了这样的方向)。 文革开始时,红卫兵们欢欣若狂:我们没有赶上长征,没有赶上抗战,也没有赶上解放战争,但现在,我们赶上了文革!他们后来的打砸抢烧杀,与此前的文学对战争状态的神圣化渲染,有没有关系呢?我以为是有关系的。 ”⑦读这样的阐述,真的像钱锺书所说的,“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 它也让我想起顾彬说的一句话:“只有具备一定的思想史深度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学。 ”⑧我以为,刘绪源的这一思考,触及的也是成人文学的重要问题。面对刘绪源《史略》的澄明而高远的审美眼光,我不禁又联想到杜传坤的《史论》和吴其南的《文化阐释》两书。尽管采用文化研究方法的这两位学者,都允诺要进行文本内部的审美研究,但是由于他们都对世界尤其是西方的优秀儿童文学缺乏了解,更没有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儿童文学审美价值观,因此,在对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的审美判断上,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混乱、矛盾,甚至谬误。
比如,对《稻草人》这篇童话,杜传坤认为,“其艺术上的成熟也是毋庸置疑的”,“此篇中的描写都是儿童化的”,“既有趣味又容易被理解”,“对于稍微了知人事的儿童来讲,是非常具有情感震撼力的”。①再比如,刘绪源所指出的张天翼童话“图解革命理论”的“贻害”和“误导”,在杜传坤这里,竟然变成了“为童话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介入现实、实现其政治教育目的作了成功的尝试”,②“虽处在某种政治自觉性之下,却没有落入图解、说教的庸俗化陷阱,开拓了政治教育童话的新天地”。
③对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吴其南也认为,“其真正的成功并不在这个主题,不在这个叙事大框架,而在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充满情趣的细节,在这些细节后面鲜活生动的儿童心理,在这些细节、心理与革命教育主题、叙事框架形成的张力,在这些细节、心理对教育主题、叙事框架的突破”。④吴其南的这种评价方式,是忽略了文学审美的整体性原则,而以局部(“充满情趣的细节”)代替了整体。他没有意识到,像张天翼这样的以趣味作为手段,以教训作为目的的创作,是更加不能以局部“细节”作为艺术评价的基础条件的。
我感到,吴其南和杜传坤并没有端正儿童文学审美价值观,所以也就不能“建构”出儿童文学史的艺术展开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性的东西”。于是,我得到的印象是,杜传坤的《史论》、吴其南的《文化阐释》虽然涉及的作家作品很多,但是,我从中得到的文学史的样貌和观念,却比所涉作家作品不多的刘绪源的《史略》少了很多很多。究其原因,除了缺乏像刘绪源那样的对二十世纪历史具有穿透力的思想之外,儿童文学审美批评能力的欠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因此,关于“现代”的理论话语(含现代性理论和后现代理论)是儿童文学研究的最为重要的语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刘绪源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一九一六-一九七七)》虽然没有标榜自己在使用某种新的理论方法,但是,其思维方式却是一方面告别本质主义这一传统,一方面抵抗激进的后现代解构理论中的xuwuzhuyi倾向,而走向了建构主义的本质论。正因如此,《中国儿童文学史略》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真正的创新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