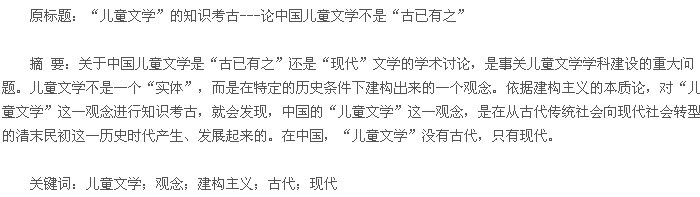
自觉地进行学术反思,在我有着现实的迫切性。我的儿童文学本质理论研究和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在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上,面临着有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它们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我愿意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
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要回答本质论(不是本质主义)的合理性和可能性这一问题,而与这一问题相联系的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起源即儿童文学是不是“古已有之”这一问题。
这两个问题,是儿童文学基础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上的重大问题,需要研究者们进一步重视,充分地展开思想的碰撞和学术的讨论。
本文倡导建构主义的儿童文学本质论,并借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以及布尔迪厄的“文学场”概念,对“儿童文学”这一观念进行知识考古,以深化本人对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这一问题的思考,同时也期望目前走入困局的对这一文学史问题的讨论,能够另辟蹊径,柳暗花明。
一、建构主义本质论:儿童文学史论的一种方法
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理论方法非常重要。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理论决定着我们所能观察的问题。讨论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这一文学史的重大问题,必然涉及到研究者所持的儿童文学观。对儿童文学本质论的认识和思考,是讨论这一问题的学术基础。
近年来,有的儿童文学研究者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一些观点,发出了反本质论(有时以反本质主义的面貌出现)的批判声音。我想,我的本质论研究也在被批评之列。甚至毋宁说,由于我出版了《儿童文学的本质》一书,理所当然地首当其冲。我自认为,自己的研究尽管含有一定的普遍化、总体化思维方式,但是,基本上不是本质主义研究而是本质论研究,努力采取的是一种建构主义的姿态。在反本质论的学术批评中,吴其南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学者。他在《20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一书中说:“这些批评所持的多大(大多)都是本质论的文学观,认为现实有某种客观本质,文学就是对这种本质的探知和反映;儿童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儿童文学就是这种‘天性’的反映和适应,批评于是就成了对这种反映和适应的检验和评价。这种文学观、批评观不仅不能深入地理解文学,还使批评失去其独立的存在价值。”
〔1〕(P6)“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不是文学本质论的代名词,不是所有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论阐释都是本质主义的。本质主义只是文学本质论的一种,是一种僵化的、非历史的、形而上的理解文学本质的理论和方法。“”建构主义不是认为本质根本不存在,而是坚持本质只作为建构物而存在,作为非建构物的实体的本质不存在。”
〔2〕但是,吴其南的上述论述是将本质论和本质主义不加区分地捏合在了一起,他要否定的是所有“本质论的文学观”。从“儿童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儿童文学就是这种‘天性’的反映和适应”这样的语气看,他似乎连“儿童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天性’”也是反对的。吴其南是经常操着后现代话语的学者,他的反本质论立场,我感觉更靠近的是激进的后现代理论。但是,我依然认为,吴其南积极借鉴后现代理论,探求学术创新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尽管我依然坚持儿童文学的本质论研究立场,但是,面对研究者们对本质主义和本质论的批判,我还是反思到自己的相关研究的确存在着思考的局限性。其中最重要的局限,是没能在人文学科范畴内,将世界与对世界的“描述”严格、清晰地区分开来。有意味的是,我的这一反思,同样是得益于后现代理论。
后现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说:“真理不能存在那里,不能独立于人类心灵而存在,因为语句不能独立于人类心灵而存在,不能存在那里。世界存在那里,但对世界的描述则否。只有对世界的描述才可能有真或假,世界独自来看———不助以人类的描述活动———不可能有真或假。“”真理,和世界一样,存在那里———这个主意是一个旧时代的遗物。”
〔3〕(P13-14)罗蒂不是说,真理不存在,而是说真理不是一个“实体”,不能像客观世界一样“存在那里”,真理只能存在于“对世界的描述”之中。正是“对世界的描述”,存在着真理和谬误。
着述《语言学转向》的罗蒂对真理的看法,源自他的“语言的偶然”这一观点:“如果我们同意,实在界(reality)的大部分根本无关乎我们对它的描述,人类的自我是由语汇的使用所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被由语汇适切或不适切地表现出来,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相信浪漫主义‘真理是被造而不是被发现的’观念是正确的。这个主张的真实性,就在于语言是被创造的而非被发现到的,而真理乃是语言元目或语句的一个性质。”
〔3〕(P16)其实,后结构主义也揭示过“所指”的“不确定性”。用德里达的话说:“意义的意义是能指对所指的无限的暗示和不确定的指定……它的力量在于一种纯粹的、无限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一刻不息地赋予所指以意义……”〔4〕(P23)连批判后现代理论的伊格尔顿也持着相同的观点。他说:“任何相信文学研究是研究一种稳定的、范畴明确的实体的看法,亦即类似认为昆虫学是研究昆虫的看法,都可以作为一种幻想被抛弃。”“从一系列有确定不变价值的、由某些共同的内在特征决定的作品的意义来说,文学并不存在。”
〔5〕(P27)其实,伊格尔顿是说文学作为一个“实体”并不存在,文学只作为一种建构的观念存在。这一观点的哲学基础是语言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对现实的虚构。语言里没有现实的对应实物,只有对现实的概念反应。
虽然作为“实体”的儿童文学不存在,但是作为儿童文学的研究对象的文本却是存在的,尽管范围模糊并且变化不定。面对特定的文本,建构儿童文学的本质的时候,文本与研究者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吴其南说:“‘现实作者’和‘现实读者’是在文本之外的。而一篇(部)作品适合不适合儿童阅读,是不是儿童文学,主要是由文本自身决定的。”
〔1〕(P2)这仍然是把儿童文学当做是具有“自明性”的实体,是带有本质主义思维色彩的观点。本质论研究肯定不是脱离作为研究对象的文本的凭空随意的主观臆想,但一部作品“是不是儿童文学,主要是由文本自身决定的”这一说法,从反本质主义的建构主义观点来看,恐怕是难以成立的。文本无法“自身决定”自己“是不是儿童文学”,因为文本并不天生拥有儿童文学这一本质。
作品以什么性质和形式存在,是作家的文本预设与读者的接受和建构共同“对话”、商谈的结果,建构出的是超越“实体”文本的崭新文本。在这个崭新文本的建构中,读者的阅读阐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我读某位作家的一篇文章,将其视为描写作家真实生活的散文,可是,作家在创作谈中却说,是当作小说来写的。假设我永远读不到那篇创作谈(这极有可能),在我这里,那篇作品就会一直作为散文而存在。可见,这篇文章是什么文体,并不“主要是由文本自身决定的”。再比如,安徒生童话并不天生就是儿童文学。试想一个没有任何儿童文学知识和经验的成人读者,读安徒生的童话,阅读就不会产生互文效果,自然也不会将其作为儿童文学来看待。一部小说,在某些读者那里,可能被看作历史文本。一部历史着作,在某些读者那里,也可能被看作小说文本。本质并不是一个像石头一样的“实体”,可以被文本拿在手里。本质是一个假设的、可能的观念,需要由文本和读者来共同建构。在建构本质的过程中,特定的文本与研究者之间,肯定不是吴其南所说的“‘现实读者’是在文本之外”这种关系,而是在社会历史条件下,在文化制约中,研究者与文本进行“对话”、碰撞、交流,共同建构某种本质(比如儿童文学)的关系。
我相信,持上述建构主义的本质观,能够将很多从前悬而未决、甚至纠缠不清的重要学术问题的讨论发展、深化下去。比如,建构主义的本质论可以成为儿童文学史论的一种方法,有效处理在中国儿童文学史发生问题研究上出现的是否“古已有之”这一争论。到目前为止,主张中国的儿童文学“古已有之”的王泉根(观点见《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和方卫平(观点见《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与主张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的我本人(观点见《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讨论,可以说是彼此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本质主义思维的圈套,从而处于一种解不开套的困局的状态。但是,如果引入建构主义的本质理论,也许可以走出山穷水尽,步入柳暗花明。
二、观念的知识考古:“儿童文学”并非“古已有之”
王泉根认为:“中国的儿童文学确是‘古已有之’,有着悠久的传统”,并明确提出了“中国古代儿童文学”、“古代的口头儿童文学”、“古代文人专为孩子们编写的书面儿童文学”的说法。
〔6〕(P15-24)方卫平说:“中华民族已经拥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儿童文学及其理论批评作为一种具体的儿童文化现象,或隐或显,或消或长,一直是其中一个不可分离和忽视的组成部分。”
〔7〕(P28)我则不同意上述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的观点,指出:“儿童与儿童文学都是历史的概念。从有人类的那天起便有儿童,但是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儿童却并不能作为‘儿童’而存在。……在人类的历史上,儿童作为‘儿童’被发现,是在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才完成的划时代创举。而没有‘儿童’的发现作为前提,为儿童的儿童文学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儿童文学只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与一般文学不同,它没有古代而只有现代。如果说儿童文学有古代,就等于抹煞了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独特规律,这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8〕(P54)尽管我提出了儿童文学是“历史的概念”,却没有意识到,在方法论上,要用对古人如何建构儿童文学这个观念的探寻,来彻底取代对那个并不存在的儿童文学“实体”的指认。
陷入讨论的僵局状态,是因为双方都在拿“实体”(具体作品)作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王泉根说,晋人干宝的《搜神记》里的《李寄》是“中国古代儿童文学”中“最值得称道的着名童话”,“作品以不到 400 字的短小篇幅,生动刻画了一个智斩蛇妖、为民除害的少年女英雄形象,热情歌颂了她的聪颖、智慧、勇敢和善良的品质,令人难以忘怀”〔6〕(P24)。我则认为:“《李寄》在思想主题这一层面,与‘卧冰求鲤’、‘老莱娱亲’一类故事相比,其封建毒素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李寄斩蛇’这个故事,如果是给成人研究者阅读的话,原汁原味的文本正可以为研究、了解古代社会的儿童观和伦理观提供佐证,但是,把这个故事写给现代社会的儿童,却必须在思想主题方面进行根本的改造。”
〔8〕(P82-83)方卫平把明代吕得胜、吕坤父子的《小儿语》和《演小儿语》看作是儿童文学的“儿歌童谣”,我却赞同周作人的观点:“……如吕新吾作《演小儿语》,想改作儿歌以教‘义理身心之学’,道理固然讲不明白,而儿歌也就很可惜的白白的糟掉了。”
〔9〕(P548)“他们看不起儿童的歌谣,只因为‘固无害’而‘无谓’,———没有用处,这实在是绊倒许多古今人的一个石头。”
〔10〕(P112)涂明求的《论中国古代儿童文学的存在———以童谣为中心兼与朱自强先生商榷》一文,是一个典型的把儿童文学作品当作“实体”的存在来指证的研究。涂明求例举我的一些动情地赞美童谣的感性化文字,说这里面有一个“诗人朱自强”,然后将从文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立场出发,否定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的我,称之为“概念朱自强”,说“这个清辉遍洒、童心本真的朱自强”“驳倒了‘概念朱自强’”。
〔11〕在我内心中和研究中的确存在“诗人”(感性)和“概念”(理性)这两个“我”,但是,涂明求将我的不同语境的研究中出现的两者对立起来,是没能理清不同的学术维度。涂明求的论文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我对现代社会的“‘儿童’的发现”和“儿童文学只有‘现代’,没有‘古代’”的论述,的确是一种“概念”辨析。
如果我们在本质论上,不是把儿童文学当作一个“自在”(方卫平语)的存在,而是当作“自为”(朱自强语)的存在,①即不是把儿童文学看作是客观存在的、不证自明的“实体”,而是作为一个建构出来的“观念”来认识把握的话,再面对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的是否“古已有之”的争论,就可以另辟蹊径来展开讨论,使各自的理论言说得到拓展和深化乃至修正。
上述争论双方都是把所谓古代儿童文学的存在,当做一个“实体”来对待。可是,儿童文学偏偏又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不像面对一块石头,一方说这就是石头(儿童文学),另一方也得承认的确是石头(儿童文学)。判断一个文本是不是儿童文学,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标准。你拿你所持的儿童文学理念来衡量,说这是儿童文学作品,而我所持的儿童文学理念与你不同,拿来一衡量,却说这不是儿童文学作品。这样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讨论不光是很难有一个结果,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讨论学术含量、学术价值很低,也很难形成学术的增值。
依据建构主义的本质论观点,现在我认为,作为“实体”的儿童文学在中国古代(也包括现代)是否“古已有之”这一问题已经不能成立!剩下的能够成立的问题只是,在中国古代,作为一个建构的观念的儿童文学是否存在这一问题。对这一问题,方卫平似乎已经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虽然把古代称为儿童文学的“史前期”,把古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看作是“前科学形态”,但是,行文中还是出现了“……在明代以前……围绕着童谣起源、本质等问题所形成的种种解释,也就成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滥觞”〔7〕(P38)这样明确又肯定的观点。而在介绍了吕得胜的《小儿语序》和吕坤的《书小儿语后》两则短文之后,也有这样的评价:“吕氏父子的这两则短文,单从理论批评的角度看,自然还显得粗浅谫陋;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它们在中国古代儿童文学批评史上,却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页。”
〔7〕(P43)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方卫平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一书引用的古人文献里,都没有出现过“文学”和“儿童文学”这两个词语。不过,古代文献里,比如《南齐书·文学传论》、《南史·文学传序》出现过“文学”一词,有的解释与现代意义的“文学”有相通之处。但是,古代文献里从未出现过“儿童文学”一词,可见古人的意识里并没有“儿童文学”这一个概念。
在此,我想针对作为观念的儿童文学在中国古代是否“古已有之”这一问题,引入布尔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文学场”这一概念进行讨论。布尔迪厄认为,要理解和阐释“什么使在博物馆展出的一个小便池或一个瓶架成为艺术品”,“这需要描述一整套社会机制的逐步出现,这套社会机制使艺术家个人作为这个偶像即艺术品的生产者成为可能;也就是说,需要描述艺术场(分析家、艺术史家都被包括在当中)的构成,艺术场是对艺术价值和属于艺术家的价值创造权力的信仰不断得到生产和再生产的场所”〔12〕(P275)。“艺术作品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如同审美判断的特定性问题,只能在场的社会历史中找到它们的解决办法,这种历史是与关于特定的审美禀赋的构成条件的一种社会学相联系的,场在它的每种状况下都要求这些构成条件。”
〔12〕(P273)儿童文学的生产,也需要历史的、社会的构成条件,是以“一整套社会机制”来进行实践的。所以,对探讨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这一问题,我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中说,“面对中国儿童文学的产生这一重大文学史事件,我们不能采取对细部进行孤证的做法,即不能在这里找到了一两首适合儿童阅读,甚至儿童也许喜欢的诗,如骆宾王的《咏鹅》,在那里打到了一两篇适合儿童阅读,甚至儿童也许喜欢的小说,如蒲松龄的《促织》,就惊呼发现了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学绝不是在上述那些平平常常的日子里,零零碎碎地孤立而偶然地诞生出来的。古代封建社会的‘父为子纲’的儿童观对儿童的沉重压迫,使中国儿童文学这个胎儿的出生变得格外艰难,需要整个社会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来助产(正如欧洲关于‘人’的真理的发现,需要启蒙运动来帮助擦亮眼睛一样),因而中国儿童文学呱呱坠地的那一天,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节日。不过,我所说的这个节日并不是生活感觉中的某一天,而是历史感觉中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儿童文学诞生的证据在整个社会随处可见:在思想领域有旧儿童观的风化,新儿童观的出现;在教育领域有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革新;在文学领域有为儿童所喜闻乐见的新的表现方法的确立;在出版领域有成批的儿童文学作品问世等等。这样一个儿童文学的诞生已成瓜熟蒂落之必然趋势的时代,只能出现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之中。”
〔8〕(P57-58)日本也是同样情形。日本儿童文学诞生于明治时代,也是因为明治时代新的儿童观的出现为儿童文学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明治建立并普及了现代小学校这一教育制度,同时,印刷技术革命,资本主义经营和中产阶级为主的购买层的出现等等,这些条件结构在一起,成为日本儿童文学诞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
我认为,如果要论证儿童文学理念“古已有之”,同样像布尔迪厄所说的,“需要描述一整套社会机制的逐步出现”的状况,有这样“一整套社会机制”,才能形成布尔迪厄所说的那个“社会惯例”———“社会惯例帮助确定了一直不确定的并在简单的用品与艺术作品之间变动的界限”。
〔12〕(P271)如果对假设存在的古代的儿童文学“场”进行描述,将会出现什么情形呢?在思想领域,有占统治地位的朱熹那样的成人本位的儿童观;在教育领域,有对儒家经典盲诵枯记的封建私塾;在文学领域,有重抒情轻叙事、重诗文轻小说的文学传统;在出版、经济流通领域,印刷技术水平低下,文学作品难以作为商品流通。如果我的上述描述反映的是古代社会的普遍性,那么,它与我在前面描述的儿童文学得以产生的那个现代社会是完全异质的。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将在现代社会中产生的某些特定的文本称为“儿童文学”,那么,我们就不能将与现代社会性质相反的古代社会里的某些特定的文本称为“儿童文学”。
事实上,方卫平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里,对古代的“社会空间”作了这样的描述:“与传统文化对儿童特点和精神需求的扼杀比较起来,这些在传统儿童观顽石的夹缝中偶尔生长起来的理论小草终究还是难以为中国古代儿童文化领域带来哪怕是些微的春色,难以改变历代儿童不幸的生存地位与精神境遇。”
〔7〕(P35)在方卫平所指出的古代历史和社会条件下,说能孕育出儿童文学(这个儿童文学只能是一个现代人的概念),其间必然出现逻辑上的断裂。
针对儿童文学这一观念在中国古代(也包括现代)是否存在这一问题,我还想引入福柯提出的历史学研究的“事件化”方法。“在福柯看来,有总体化、普遍化癖好的历史学家常常热衷于发现普遍真理或绝对知识,而实际上,任何所谓普遍、绝对的知识或真理最初都必然是作为一个‘事件’(event)出现的,而‘事件’总是历史地(的)具体的。”“这样,事件化意味着把所谓的普遍‘理论’、‘真理’还原为一个特殊的‘事件’,它坚持任何理论或真理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期、出于特定的需要与目的从事的一个‘事件’,因此它必然与许多具体的条件存在内在的关系。”
〔13〕(P141)某一知识(比如儿童文学)作为一个“事件”的出现,都会具有一定的确定性,就如福柯所说:“不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的知识是不存在的,而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
〔14〕(P203)吉登斯也说道,“确实存在着历史变革的一些确定性事件,人们能够辨认其特性并对其加以概括。”
〔15〕(P5)我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儿童文学”这一观念的创造,就是福柯所说的“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的知识,就是吉登斯所说的“历史变革的一些确定性事件”之一,对其“特性”,“人们能够辨认”“并对其加以概括”。
如果我们把古代“儿童文学”观念(假设有)的生成“事件”化,会出现什么情况?结果显而易见:古人的文献里,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儿童文学”这一语汇,主张儿童文学“古已有之”的现代学者的相关研究,目前还无法将“儿童文学”在古代事件化,无法将“儿童文学”描述成“确定的话语实践”,无法梳理儿童文学这一知识(假设有)在古代的建构过程,更没有对其“特性”进行过“辨认”和“概括”。
一个概念,必有它自己的历史。在古代社会,我们找不到“儿童文学”这一概念的历史踪迹,那么,在哪个社会阶段可以找得到呢?如果对“儿童文学”这一词语进行知识考古,会发现在词语上,“儿童文学”是舶来品,其最初是先通过“童话”这一儿童文学的代名词,在清末由日本传入中国(商务印书馆 1908 年开始出版的《童话》丛书是一个确证。我曾以“‘童话’词源考”为题,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中作过考证),然后才由周作人在民初以“儿童之文学”(《童话研究》1913 年),在五四新文学革命时期,以“儿童文学”(《儿童的文学》1920 年)将儿童文学这一理念确立起来。也就是说,作为“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的儿童文学这一“知识”,是在从古代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清末民初这一历史时代产生、发展起来的。
有研究者拿周作人“中国虽古无童话之名,然实固有成文之童话”一语,作为中国古代已有儿童文学(童话)的依据,其实,这个例子恰恰是对古代已有儿童文学这一观点的驳斥。周作人是这样说的:“中国虽古无童话之名,然实固有成文之童话,见晋唐小说,特多归诸志怪之中,莫为辨别耳。”〔16〕(P340)在这段话里,“莫为辨别”一语特别重要。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没有接受者,作品将不会存在。因此,当《吴洞》这样的作品被古人“归诸志怪”来接受,而不是被当做由现代概念判定为“童话”的这种作品来接受,我们就不能说古代存在过“童话”,而只能说存在着“志怪”。
现代的“童话”概念里有着“给儿童的故事”这一含义,而古代的“志怪”,毫无疑问地没有“给儿童的故事”这一含义。
可见,“志怪”与“童话”这两个语词,无论是能指还是所指都是不同的。我认为,对古代的民间文学(包括童谣)也应该以此理论之。
古人“莫为辨别”的还有古代童谣。周作人说:“自来书史记录童谣者,率本此意,多列诸五行妖异之中。盖中国视童谣,不以为孺子之歌,而以为鬼神凭托,如乩卜之言,其来远矣。”〔17〕(P294-295)到了现代人周作人这里,方“视童谣”“为孺子之歌”:“儿歌之用,亦无非应儿童身心发达之度,以满足其喜音多语之性而已。”〔17〕(P300)中国古代尽管出现了“童谣”这一语汇,但是,这一语汇完全不能与作为“知识集”(佩里·诺德曼语)和“文学场”(布尔迪厄语)的“儿童文学”这一现代概念划等号。也就是说,即使能证明古代存在“童谣”理论,但是却不能由此而得出古代存在“儿童文学”理论这一结论。我想,我的这一观点也是对涂明求上述与我商榷的论文的一个回应。
需要辨析的还有“自觉”与“非自觉”这两个修饰语。主张儿童文学“古已有之”的学者(比如王泉根和方卫平),为了将所谓的古代儿童文学与现代儿童文学相区别,往往说古代儿童文学是“非自觉的儿童文学”,现代儿童文学是“自觉的儿童文学”(可见论者自己也知道两者不是一个东西)。但是如前所述,如果不是把儿童文学看做一个“实体”,而是当作一个理念,所谓现代儿童文学是“自觉的”,古代儿童文学是“非自觉”的这一观点就不能成立。因为古代如果存在儿童文学这一“理念”,作为理念,就不可能是“非自觉的”,而必然是“自觉的”。
另外,“现代意义的儿童文学”也不是科学的、逻辑一致的表述,因为这一表述是以存在“古代意义的儿童文学”为前提。古人从没有建构过任何意义的儿童文学观念。如果进行知识考古,很显然,“古代意义的儿童文学”这一概念产生于现代人这里,是他们在现代社会,拿着根据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现代作品建构起来的“儿童文学”观念,回到古代,代替不作一声的古代人来指认某些文本就是儿童文学。也就是说,“创造”了“古代儿童文学”的不是古代人,而是现代人,所以,还是只能说,儿童文学是现代人创造的现代文学,儿童文学只有“现代”,没有“古代”。
对作为观念的儿童文学的发生进行研究,要问的不是儿童文学这块“石头”(实体)是何时发生、存在的,而是应该问,儿童文学这个观念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语境)下,出于什么目的建构起来的,即把儿童文学概念的发生,作为一个“事件”放置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知识考古,发掘这一观念演化成“一整套社会机制”的历史过程。而且,如果如罗蒂所言,“只有对世界的描述才可能有真或假”,那么,我对儿童文学这一观念的现代发生的描述,和一些学者对儿童文学这一观念的古代发生的描述,两者就很可能一个是“真”的,另一个是“假”的。
[参考文献]
〔1〕吴其南.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陶东风.文学理论:建构主义还是本质主义?———兼答支宇、吴炫、张旭春先生〔J〕.文艺争鸣,2009(7).
〔3〕(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美)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5〕(英)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6〕王泉根.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M〕.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