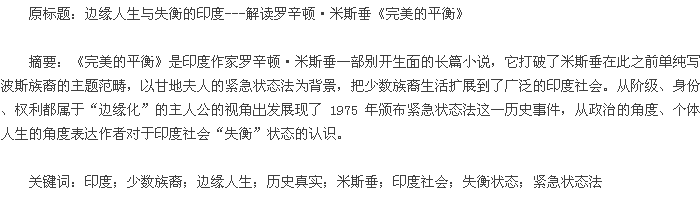
罗辛顿·米斯垂关注历史、关注历史浪潮对于个体人生巨大冲击力的创作范式,从《如此漫长的旅途》中形成之后,又延续到了下一部作品《完美的平衡》中。但与前一部作品不同的是,《完美的平衡》打破了米斯垂在此之前单纯写波斯族裔的主题范畴,以甘地夫人的紧急状态法为背景,把描述波斯这一少数族裔生活扩展到了广泛的印度社会。这一写作范畴的扩大,证明了米斯垂对于“边缘”的理解已经更加深入。
“边缘”不仅体现在人口数量的多寡,“边缘”既可以是地位的边缘,也可以是阶级、权利、身份的多重边缘化。正如评论者所言,“它较之前的作品而言,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详尽的对于性别、阶级、宗教等多方面的探索。”它提供了“一个相当大的社会谱系,关于穆斯林收账员、裁缝、锡克教出租车司机、狡诈的乞丐、清醒的律师、杀人的彪形大汉、腐败的贫民区房主、利欲熏心的警察、激进主义的学生,还有在一些片段中写到英迪尔·甘地的形象,和《午夜的孩子》《如此漫长的旅途》中一样真实。”[1]
实际上,米斯垂自己也意识到了在前两部作品中自己对于波斯族裔的集中描写忽略更广大的社会群体,因此在一次访谈中,他说:“我在这本书中有意识地包含了更多的东西,主要是因为在印度,75%的人居住在乡镇,我想要拥抱更多的印度社会现实。”[2]
小说把目光聚焦在一些低级种姓、穆斯林,当然还有波斯人这类边缘人身上,他们在种姓上是“不可接触者”,在宗教上边缘于印度教,在社会地位上又非精英阶级。
小说设置了四个主要的主人公:房东迪娜,迪娜雇佣的叔侄俩裁缝伊什尔和奥姆,还有迪娜的房客马奈克。迪娜是个寡妇,她拒绝了哥哥对她再婚的建议独立生活,在自己的眼睛不能再缝制衣服之后只能做服装加工买卖的中间人。伊什尔和奥姆是因为躲避追杀离开家乡,因为奥姆的父亲参加了种姓暴动运动,全家被屠杀,只有伊什尔和奥姆成为幸存者逃离家乡做裁缝以谋生计。马奈克,是迪娜同学的儿子,遵从父亲的意愿在孟买上大学,因为受到羞辱搬出了学校。在迪娜破旧的房子里,故事开始叙述,米斯垂把不同命运、不同经历的四个人物通过一个共同的生活地域进行关联,再把叙述沿着回忆和时间的延续两个相反的方向发散出去。迪娜的童年生活,丈夫的早逝,艰难的谋生经历;马奈克童年的喜玛拉雅山,在学校受到屈辱,迪拜的生活经历,最后卧轨自杀的结局;伊什尔和奥姆的家族,他们在逃亡中居住的贫民区,在阿什拉夫叔叔那里学习裁缝,为古帕塔夫人做廉价劳动力以及最后成为乞丐。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每讲述一段经历就是描述一个生存空间。同时,四个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又把他们所遇到的人、看到的事、听到的议论全部网罗其中,最后形成一个小人物生活圈。米斯垂试图尽可能地把印度社会底层生活境况全面地展示出来,在每一个故事中,我们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人物生存状态的不稳定性,这些人物所承受的是远离自己的土地、家庭、亲人,还要面对他人的谴责、失业、牢狱之灾、身体伤害甚至死亡。
米斯垂把小说的题目定名为《完美的平衡》,并借人物说出这样的感受:“你不能分隔界限,也不能拒绝让步……你只能在希望与绝望之间保持一种完美的平衡……最终,所有的问题就是平衡的问题。”[3]
这里的所谓“平衡”显然是一种讽刺。在米斯垂的描述中“,平衡”并不是那么仁慈而轻易地就能降临到一个普通人头上,平衡在印度人心里因为太抽象、太遥远最后只能成为内心的祷告。而在现实中,他们所要经受的却是无法逃避的“失衡”社会。如果说在《如此漫长的旅途》中米斯垂还是描写了一次非常态的人生经历,那么在《完美的平衡》中米斯垂就是完全着眼于最普通、最平常的人生,主人公在失衡状态下的受难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印度人的整体命运。
一、政治权利失衡
很多评论家把米斯垂与一些现实主义作家相提并论,原因就是在于米斯垂有类似于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视角:政治权利问题、社会的不平等问题,等等。在《完美的平衡》中,米斯垂并没有描述整个历史时代的野心,而是针对和围绕着甘地夫人在 1975 年颁布的紧急状态法这一特殊历史事件。紧急状态法在历史上一般被认为是甘地夫人在执政期间所做的错误决策之一。但紧急状态法所代表的铁腕政治、专制统治却非英·甘地政府所独有,而是带有印度政治权利失衡的普遍性特征。甘地夫人于 1971 年大选胜利后开始处于政治上空前的上升阶段,印巴战争的胜利更加巩固了她的权威性,在当时,有“英迪尔就是印度,印度就是英迪尔”的说法,内阁大臣无不对她俯首帖耳,人事任免完全取决于她的个人好恶。然而 1972 年印度旱灾之后,受到美国水门事件影响,与甘地夫人有关的舞弊案件被揭发出来。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件是关于在 1971 年大选中违法筹措选举资金的丑闻;一件是女总理利用职权纵容自己的儿子在新德里开设“风神之子”汽车厂。1975 年,北方邦的阿拉哈巴德市高等法院宣判甘地夫人在 1971 年选举中有舞弊行为,取消她的议员资格。反对党乘机逼英迪尔·甘地辞职。为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继续掌握政权,甘地夫人随即宣布紧急状态,取缔反对党,禁止罢工、示威和五人以上的集会,实行新闻检查,冻结职工工资和奖金,并下令逮捕了反对党大小头目和骨干十万多人。紧急状态法颁布之后,甘地政府局势稳定了,但这一强制性政策不仅不能解决印度当时的问题,反而给印度带来了更大的动荡和危机。天灾、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党派纷争日益严重,与此同时,紧急状态法的实施又给印度增添了一层恐怖气氛:
一些人莫名其妙地被逮捕、监禁,甚至“消失”.小说中写到马奈克在大学中唯一的一个朋友,善良、热情的阿维奈什就是因为参加学生政治活动而被秘密暗杀。阿维奈什的死是伊什尔和奥姆亲身经历的,小说一开始,在他们乘坐火车的途中,铁轨上发现了一具尸体。受到打扰但都感觉事不关己的旅客们只是议论着为什么人们现在都选择铁轨自杀,为什么不用毒药或是刀子这些话题,直到在后文中米斯垂交代出这种死亡方式是对反对者的警告,而死者就是阿维奈什的时候,这一事件才和强硬和残暴的印度政治联系起来。在作品中,米斯垂仍然是通过对“身体”的描述这一惯用视角,表现出掌权者的为所欲为和被统治者面对压迫、残害的无奈命运。迪娜在童年时因为剪了头发受到哥哥(统治者的象征)的惩罚,不得不把剪下的辫子每天再绑在头发上去上学;伊什尔和奥姆被阉割,成为残疾;马奈克在小说结束时选择了卧轨自杀。统治者权利的极端集中和被统治者的任人宰割,两者在权利上的强弱对比十分鲜明、强烈。
二、身份失衡
作品中的四个主要人物虽原因各不相同,但或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或被迫离开自己的亲人和自己所熟悉的生存地,或被迫离开了自己所依赖的某种感情寄托。尽管,每个人物都或多或少地在与命运进行着抗争,试图创造新生活,试图与新环境相互融合。但结局总是悲惨的失败。迪娜表现出的是人在命运的捉弄下不断丧失的过程;伊什尔叔侄表现出的是卑贱的身份所遭受的歧视、迫害和不公;马奈克表现出的是一个离根者在寻根过程中无法回归的困境。
1. 孤独的游魂。迪娜的人生变故是从父亲的去世开始的,先是失去了受宠的家庭地位,委曲求全地在兄嫂照顾下生活。丈夫在车祸中死去之后,她又失去了感情寄托无奈地回到哥哥家中。不久,因为哥哥坚持让她再嫁与之产生矛盾不得不离开家做裁缝独立生活,随后因为眼睛问题不能亲自缝制衣服只能为服装公司做中间人。迪娜在一生当中似乎永远也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所在,永远是形只影单,父亲去世她失去了女儿的身份,丈夫去世她失去了妻子的身份,与哥哥的矛盾使她完全断绝了亲情,眼睛问题又让她失去了谋生手段。在与伊什尔和奥姆相处的过程中,因为伊什尔和奥姆和自己是雇佣关系,带着波斯人在印度社会经济地位上的自豪感,她又无法真正与其相融。因此,迪娜在作品中的身份就是一个孤独的,边缘于家庭、亲情的游魂。
2. 永远的被统治者。伊什尔和奥姆在四个主人公中是地位最低下的,最受鄙视的,因此也是遭受磨难最多的。他们的家族最初是皮革工人,伊什尔的父亲为了改变身份,让自己的儿子去学习裁缝。然而,在印度,身份是无法改变的。奥姆的父亲因为对自己受歧视的身份不满,参加种姓暴动导致全家被屠杀。伊什尔和奥姆以为离开乡村来到城市会有新的生活,但迎接他们的仍然是贫民区、被雇佣、想要得到粮食补给就要被阉割的命运。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他们都只能是也永远是劳力者,是被统治者,他们所要面临的总是不稳定、不安全的生活。他们做第一份裁缝工作时住在竹竿搭成的阁楼,阁楼的意象象征着悬空、脆弱,街道的角落、店铺的门口、火车站、贫民窟被拆除以至流离失所、废墟上的临时帐篷等也都象征着动荡、边缘的生存空间。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无论他们是裁缝还是皮革工人,他们的身份都是惟一的,都是“toiler”.
3. 绝望的离根者。马奈克这个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米斯垂的代言人,一个被迫离开了自己眷恋的家乡,在现实中左冲右撞试图寻找某种感情寄托但却屡遭挫折,最后在精神上成为完全崩溃的悲剧人物。通过马奈克的短暂人生,米斯垂抒发了一个离根者在去留两难间遭受的精神折磨。对于“根”,马奈克经历了从怀念-清醒-绝望的心理过程。在小说的前半部分,马奈克在言谈之中总是充满了回家的渴望,对新生活越是失望情绪就越是低落;这一情绪的变化发生在他与伊什尔和奥姆的交往之后,在小说 311 页有一段他们的对话,“有些东西很复杂,是很难用剪刀分开的,马奈克说,好的和坏的就像这样连在一起。马奈克把他的手指并拢。比如,我的山脉。他们很美,但是经常会制造雪崩。”这个时候的马奈克已经可以比较清醒地去看待自己的家乡,不再是盲目地夸赞;在作品的最后,马奈克在迪拜生活工作了八年之后回到了孟买,这无疑是一次蓄谋已久的回归,带着热切的寻根的愿望和期待。然而孟买的混乱政局、迪娜的悲惨处境和冷漠、伊什尔和奥姆沦为乞丐甚至让马奈克不敢上前相认,一切现实恰如一场雪崩,淹没了马奈克的所有希望。可以说,米斯垂在创作《完美的平衡》时是相当悲观而绝望的,紧急状态法之后的印度在他心目中如同一个巨大的丑陋的怪物,印度之“根”已经败落、腐烂,完全失去了母国的意义和感情联系,正是这种联系的断裂导致了马奈克的精神毁灭和他的死亡。作为一个离根者,其身份的悲哀就在于他们对“根”极度渴望,却又总是让自己落入处处无根的困境之中。
在文本叙述中,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米斯垂一次一次在精神上回归印度,在意念中亲近故土,就如同他笔下的主人公对回忆的特殊癖好一样。但是,米斯垂又不得不承认,充满着政治腐化、种姓压迫、贫穷和动荡的印度就像拉什迪所说,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这是让米斯垂不能回避却又无比痛心的事实。于是,历史的勾勒之笔停驻在边缘地带,和拉什迪、奈保尔一样关注并揭示出被忽视、被掩盖、被隐藏的印度。
在印裔流散作家笔下,历史视角既是本土意味的内在挖掘,又具备了外来眼光的苛刻审视,他们对于历史的叙述既是一种寻根,一次对母国文化的回归,又是一次撕扯,试图把母国文化带离固守传统的窠臼。因此,在他们笔下关于民族历史的叙述不仅意味着对民族历史的探求、解构和重述,同时也是对民族形象的文本化模仿。正像我们不能把他们的历史叙述看成是虚构和篡改,他们笔下的印度也不能被视为虚假、他者化和扭曲的形象。印度在他们笔下和印度历史本身一样,多元、混杂、充满矛盾,这种认识恐怕是任何持有对立和一元文化立场的作家所难以达到的高度和深度。
参考文献:
[1][2]Peter Morey.Rohinton Mistry[M].Manchester UniversityPress,2004:95.
[3]Rohinton Mistry.A Fine Balance[M].faber and faber,1995: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