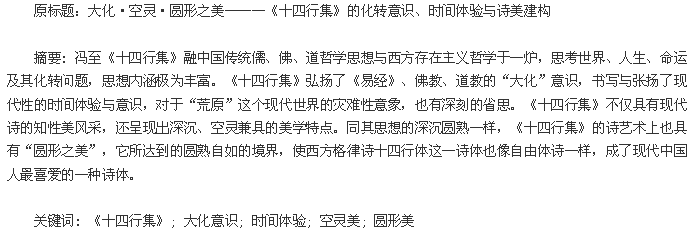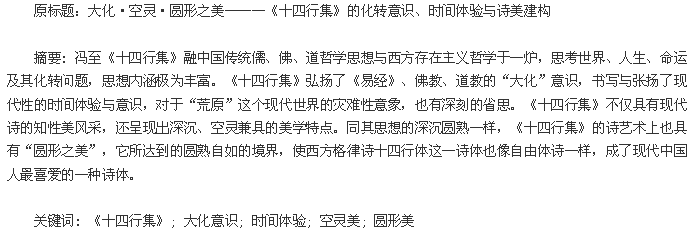
“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我们准备着》)。《十四行集》是冯至留学归来,经历了种种人生的磨难,从北向南逃难数千里,在“西南联大”教书时思考与书写“悲欢”人生的生命存在经验的一部现代经典诗集。它也是冯至在“诗是经验的传达而非单纯的情感的宣泄”的诗学观念影响下书写成的一部“凝结”着悲欢人生漫长岁月“瞬间”体悟的哲理诗集。“人有人命,虫有虫生”,人超越虫的地方在于人能够超越,懂得化转———“像蜕化的蝉蛾//把残壳都丢在泥里土里”;“像一段歌曲,//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终归剩下了音乐的身躯/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十四行集》这部在深刻的生命哲学观照下融中国传统儒道禅哲学思想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于一炉,思考人生、命运及其“化转”的极终性问题,书写与张扬现代性时间体验与意识的诗集,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
《十四行集》还呈现出现代诗所特有的知性美。“我们空空听过一夜风声,/空看了一天的草黄叶红,/向何处安排我们的思、想?/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冯至借山川万物、自然原野,以及草黄叶红、树凋虫亡的秋天之景,隐喻人生及其转化,从而创造出美的意象:《十四行集》美学个性鲜明,既呈现出深沉静穆的博大美学境界,又呈现出空灵、淡远的美学风格。从诗美艺术的建构角度来审视,冯至十四行诗的创作已经把西方严格的格律诗中国化了。《十四行集》娴熟自如地运用十四行体这一西方格律体诗歌艺术形式,既显示出其诗体特有的“圆形之美”,又显示出这种外来诗体的诗语言及其方式在转化成汉语后所具有的洗练、娴熟和畅达自如美。《十四行集》的这种诗美追求,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诗体建设的新进程,在现代汉语诗歌及其诗美建构史上具有巨大的意义。
一、大化意识、现代性时间体验
《十四行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沉思”,它是“沉思的诗”。《十四行集》里既有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人生观:“作者最关心的是人的生命态度或生存态度的问题。这一问题成为《十四行集》以及为数不少的散文的思想焦点。在这些作品中,冯至反复强调,作为自觉的生命个体,人应力求正当的生死,坚持认真地为人。”
又有浓厚的东方哲学智慧:“另一方面与传统的思想的联系也是明显的,例如,诗人关于自我与万物的沟通的体验与思考,就明显有‘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体验与思考;诗人自己还说,这样的经验,就像是佛家弟子,化身万物,尝遍众生的苦恼一般,冯至的诗也由此获得了某种东方哲学的底蕴。”
但是,总体而言,《十四行集》的时空意识及时间经验与体验是中国化的,它把个体及其人类的生命、命运放到一个特定时空里考察,表现的是中国文化中的《易经》、佛教、道教的人生哲学思想。
世变缘常,变即是常;生死相依,生生不息;天人合一,“天地之大德曰生”,是典型的传统中国《易经》、佛教、道教的人生哲学思想,也是《十四行集》的基本构思起点。《十四行集》前半部分,书写灾难岁月中的人生感受及体验,首先从这种世变缘常的理论依据出发,从转化、化解开始写起。
如其第一首《我们准备着》和第二首《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两首诗便是如此: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它们经过了一次交媾/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便结束它们美妙的一生。/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像秋日的树木,一棵棵//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伸入严冬;我们安排我们/在自然里,像蜕化的蝉蛾//把残壳都丢在泥里土里;/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
这两首诗,前一首写诗人及那些逃难的现代知识分子当下的生命境况和体验感受———“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后一首直接探讨化解、转化问题———把那些从我们身上脱落的“化作尘埃”,“像蜕化的蝉蛾//把残壳都丢在泥里土里”,像歌声“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有了这种转化、化解,生命才能够生生不息,是这首诗所传达的基本思想。所以,该诗集从生死这个终极问题出发,思考人生、社会,中国文化中的“化解”、转化、超越意识极其明显。
《十四行集》27首诗分为两部分:前14首为一部分,后13首为一部分。《十四行集》的前半部分,充分地展现出了上述思想。像前14首诗就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1、2首是第一个层次,是总题,从生死转化出发,思考化解和转化问题;第3、4首《有加利树》和《鼠曲草》是第二层次,举证了积极的化解、超越之例:把自己化解成崇高的一部分,把自己化解在平凡里;第三个层次,第5到第8首,列举一般尘世人(孤独者、绝望者、没有反省意识者、梦想者)的消极的处事之道,从反面举证化解;第四层次,第9到第14首,列举英雄、“圣者”走向永恒者的化解之道,像《给一个战士》、像《鲁迅》,像《杜甫》,像《歌德》,像《画家梵高》等诗,都是如此。这些英雄、“圣者”的化解之道,颇类佛教的化解方法,如鲁迅的“觉”、梵高的“引渡”、蔡元培的“宁静”法,以及杜甫“烂衣裳”的圣光、歌德飞蛾似的投身火焰或脱皮而生法,就是典型。
《十四行集》后半部分的13首,同样在演绎中国文化的“大化”转化意识,佛道教的化解、缘分、空无、实在的思想显得十分突出。如第15首《看这一队队的驮马》,它是对于实在的追问,从“有”与“无”、色与空的佛教式追问开始。第19首《别离》里又具有浓厚的轮回意识、前世今生的观念和生命短长的形上体验:“为了再见,好像初次相逢,/怀着感谢的情怀想过去,/象初晤面时忽然感到前生。//一生里有几回春几回冬,/我们只感受时序的轮替,/感受不到人间规定的年龄。”在第22首《深夜又是深山》诗里,尘世和“深夜”、“深山”的对举,也使我们想到深山老林里宗教修行的事情。同样在第15首《看这一队队的驮马》、第16首《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第17首《原野的小路》、第18首《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和第19首《别离》诗里,佛教、道教的“缘”、“缘分”、“有”、“无”意识,都涉及转化。这些诗整体上都在思考转化问题,体现的是中国文化的化转智慧。
《十四行集》里,《易经》思想也占了很大比重,《易传》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思想,在这里得到集中展现。我们知道,《易经》这部中国文化的经典,它与四书五经、道经和佛经一样,十分关心人类的生存和命运:认为人类的生存、命运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人与自然,是一个生态链,相互依赖;所谓生,就是生命、生成、创化,生生不息乃生之本质,生是生命自身内在的要求。《十四行集》的第16首《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第20首《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语声》、第21首《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第24首《这里几千年前》、第25首《案头摆设着用具》等传达的就是这种思想:我们的存在是与宇宙万物相互关联的,万物中有我们,我们自身里藏着万物,我们最终是万物的一部分,尤其是第25首,还传达出转化是生命自身的呼唤,是生命内在的要求的思想。所以,不管是在《十四行集》的前半部分的诗里,还是在后半部分的诗中,这种东方生命哲学的思想都溢于言表。
对于冯至来说,他似乎从这些东方文化思想里悟到了人在“苦难人间”存在下去的策略、存在的意义以及积极的人生追求的价值。其基本逻辑是这样的:因为万物一体,相互转化,所以,化我们在自然里,化成另外一个生命,世界、宇宙、人生就生生不息了;事物相互关情,相互关联,过去、未来和现在总有内在联系,所以,我们应该相互感念、关爱:“你说,你最爱看这原野里/一条条充满生命的小路,/是多少无名行人的步履/踏出来这些活泼的道路。//在我们心灵的原野里/也有几条宛转的小路,/但曾经在路上走过的/行人多半已不知去处://寂寞的儿童、白发的夫妇,/还有些年纪青青的男女,/还有死去的朋友,他们都/给我们踏出来这些道路;/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原野的小路》)这似乎是冯至所找到的存在逻辑和现实依据。知道化解、转化的内在逻辑及其现实依据,也许我们会发现怎样化解人生苦难的策略。而且,这种化解、转化,根本上说,还不是走向宗教的空,而是走向日常生活的深处。因此,后13首诗歌,《易经》的“化”的思想,最终变成了冯至对于世界、人生的感念,对人生的热爱以及对生存态度和生存策略的思考上了。这大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1)在“暴风雨”的世界里,如果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策略,尤其是佛教道教的“大化”意识,那么我们“暂住的生命”、“微弱的灯红”是最终能够找到“新生”路径的:
这里几千年前/处处好像已经/有我们的生命;/我们未降生前//一个歌声已经/从变幻的天空,/从绿草和青松/唱我们的运命。//我们忧患重重,/这里怎么竟会/听到这样歌声?//看那小的飞虫,/在它的飞翔内/时时都是新生。(《这里几千年前》)。
(2)在我们熟悉的日常用度中发现“振翼凌空”的奥妙;在小狗的存在里,发现感恩,温暖。因为日常用度里,包含我们生命本身的要求,天海自然的呼唤;个体生命与自然早已融为一体,空气、海盐已经在我们血中:
案头摆设着用具,/架上陈列着书籍,/终日在些静物里/我们不住地思虑。//言语里没有歌声,/举动里没有舞蹈,/空空问窗外飞鸟/为什么振翼凌空。//只有睡着的身体,/夜静时起了韵律:/空气在身内游戏,//海盐在血里游戏———/睡梦里好象听得到/天和海向我们呼叫。(《案头摆设着用具》)。
(3)在我们的熟悉的人物身上,发现他们的化解之道。你不见那些战士吗?你不见鲁迅、蔡元培、杜甫、歌德和梵高们吗?他们的化解,他们的人生,给了我们无限的启示。所以,《十四行集》27首,从前到后,主题是相当一贯的。前14首总体谈化解、转化思想,后13首谈论化解的依据及其人生化解、转化和超越的种种策略。得着了这种化解之道与策略,便会对于人生有新的领悟:
啊,一次别离,一次降生,/我们担负着工作的辛苦,/把冷的变成暖,生的变成熟,/各自把个人的世界耕耘。(《别离》)阅读《十四行集》,我们自始至终会领略到道家那些“贵己重生”的人生观、观行坐忘和性命双修的意识,也会时时嗅到佛教的“四谛”、“五蕴”、因缘、涅槃、轮回、“诸行无常”和靠自身解救自身的浓厚气息以及《周易》的“天人合一”、万物转化的思想。《十四行集》张扬的这种文化思想意义重大。这种思想让我们找到了生命安顿的智慧,得着了存在的经验。
时间经验和体验也是人类最基本的精神性存在经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语汇、诗句表达这种经验与体验,如恍若隔世、度日如年、朝思暮想、白驹过隙、一眨眼间、“天上一时人间三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悠悠千古等等,不胜枚举。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和陶渊明的“今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等等诗句也是如此。
在“诗不徒是情感,还是经验”的现代性诗学理念引领下,《十四行集》充分地展现了这种人类存在的体验。如《我们准备着》有“漫长的岁月”与“瞬间”比照的时间意识;在《这里几千年前》包含过去包容现在的时间意识;《别离》具有过去、前生和时序轮转的时间意识;《歌德》包含80年漫长人生与分秒不停地时间追索情怀;《一个旧日的梦想》里千年与如今对举等,都展现了这种现代性时间意识,书写了这种时间性体验。这种书写的代表作是《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
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在一间生疏的房里,它白昼时/是什么模样,我们都无从认识,/更不必说它的过去未来。原野———//一望无边地在我们窗前展开,/我们只依稀地记得在黄昏时/来的道路,便算是对它的认识,/明天走后,我们也不再回来。//闭上眼吧!让那些亲密的夜/和生疏的地方织在我们心里:/我们的生命像那窗外的原野,//我们在朦胧的原野上认出来/一颗树,一闪湖光,它一望无际/藏着忘却的过去、隐约的未来。这首以空间性经历写时间性体验的诗篇,充分地展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会通的现代时间意识。
从《十四行集》的整体结构来看,这首诗似乎又是整个《十四行集》的一个缩影。因为整个《十四行集》都以空间性经历写人类及其个体的时间性体验。从南到北,从平原、高山到林间小屋,从星空到大地,诗人冯至在这种大空间的长途跋涉中体验着时间,体验着生命及其存在,体验到生命、自然、时间的相互关情、相互建构。这委实是《十四行集》的独特内涵。
事实上,《十四行集》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它不仅表达了传统中国式的安顿生命的策略和智慧,还把时间意识与个体生命的体验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内涵上,超越了那种面对时间不可逆转性的生命短暂、时光易逝的感叹(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也超越了面对时间无限而产生的个人渺小孤独的喟叹(“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而力图张扬着把定现在,明了时间的短暂与生存的永恒这一辩证性体验,具有了在整体的时间长河里转化、化解、超越的现代性时间意识、时间策略。具体而言,这种时间意识的现代性意义体现在:。
(1)否定了宗教的、传统的循环、轮回的时间意识,而代之以进化论的发展演进的时间观;(2)规避了进化论的直线的机械性时间意识,而张扬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建构的思想。能够体会时间,具有了这种现代性时间经验,懂得了时间的这种建构性思想,我们的生命便有了有待开拓的无限的丰富空间。因为人因懂得时间及其内在的机理而懂得人生,因建构了时间意识和时间经验而成熟起来。这种经验的拥有,是我们人类精神与心灵丰富与富有的表现。因此,阅读《十四行集》,我们会在其中得着丰富的人生启迪和生存智慧:在狂风、暴雨不断打击,战争、冲突不断升级的灾难下,在漫长岁月中,不幸突然来临时,死亡又不可避免,我们应该明白,世界万事万物,宇宙、社会和个体总是相互有关联的,我们应该在这种关联处发现我们自身,辨认出我们自身;过去、现在和未来也并非毫不相干,在忘却的过去,隐约的未来中,我们要认出“现在”;既然万物相通,互相影响,互相转化,转化中包含着生机,世界与生命由此生生不息,那么,我们应该也去解化、创化自己;纷杂、喧嚣的尘世,绝望与希望并存,堕落与升华同在,我们应当追求后者,在短暂中去追求永恒,把住当下,自我主宰自己的命运,开拓自己存在的“大宇宙”空间;我们拥有的东西,可能会瞬间即无,我们的生命能带走什么,留下什么呢?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实在?像小飞虫取得新生,像蝉蛾化成泥与土,像飞翔的鸟,不倦地飞,那才是我们的真正实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十四行集》字字是禅语,句句是人生,在其中,我们会得着丰富的生命的启迪与人生智慧。
《十四行集》的思想相当丰富。它还包含西方近现代现代派诗歌具有的“荒原”意识,如第5首《威尼斯》和第6首《原野的哭声》,就清晰地表现了这种意识,一些诗的意象如“荒村”、“原野的哭声”、“威尼斯”、“狂风”、“暴雨”、“彗星”和“阡陌纵横的路上”等,就雷同艾略特的《荒原》的意象。
然而,《十四行集》并不消极。如第21首《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是冯至《十四行集》里最悲苦的一首诗,也是冯至内心世界最深重的叹息:狂风暴雨中,破旧茅屋里,微弱孤灯下,与一切分离,与一切都有千里万里的距离,人像风雨中的飞鸟随时会被吹入高空,淋入泥土,不能自主,但是,冯至在诗中书写的“向死而生”的存在智慧、传统中国文化的生生不息的大化、转化意识与积极的现代性时间意识,却使诗的思想明显明亮了起来。因为经验而懂得,因为深悟世变缘常,所以豁达而从容面对。这使《十四行集》思想境界骤然腾升。
二、美学形态:空灵与深沉兼具
《十四行集》这部表现灾难岁月中的人生感受与体验的经典现代诗集,没有虚无,消极的成分,而有一种空灵深沉兼具的格调。这是《十四行集》最可宝贵的美学品格。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文本中,这样的存在为数极少。
何谓空灵?
美学家叶朗认为,空灵相当于美学境界上的禅悟禅悦。“禅宗主张在普通的、日常的、富有生命的感性现象中,特别是在大自然的美景中,去领悟那永恒的空寂的本体。这就是禅宗的悟。一旦有了这种领悟和体验,就会得着一种喜悦。这种禅悟和禅悦,形成一种特殊的审美形态,就是空灵,‘万古长空’,象征着天地的悠悠和万化的寂静,这是本体的静,本体的空。
‘一朝风月’,则显示宇宙的生机,大化的流行,这是现实世界的动。禅宗就是要人们从宇宙的生机去悟那本体的静,从现实世界的‘有’去悟那本体的‘空’。所以禅宗并不主张抛弃现实生活,并不否定宇宙生机。因为只有通过‘一朝风月’,才能悟到‘万古长空’。反过来,领悟到‘万古长空’,才能真正珍惜和享受‘一朝风月’的美。这就是禅宗的超越,不离此岸,又超越此岸。这种超越,形成了一种诗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审美形态,就是空灵”。在这个美学定义下考辨,《十四行集》就具有美学范畴意义上的空灵美。如《十四行集》第1首《我们准备着》关于“奇迹”的隐喻,结尾第27首《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关于“风旗”的象征以及首节的“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取水人取来椭圆的一瓶,/这点水就得到一个定型;/看,在秋风里飘扬的风旗”的说明,就反映了这部诗集的禅语———生命与人生的宗教般的沉思及其瞬间永恒的体验性书写,就具空灵之美的形态。冯至借山川万物、自然原野,以及草黄叶红、树凋虫亡的秋天之景,隐喻人生及其转化,从而创造出具有空灵美的意象。《十四行集》的空灵美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万古长空”去体悟“一朝风月”的诗歌创作构思所呈现的思维品格,使诗歌具有了空灵之美的美学形态特征。在第27首诗《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里,“泛滥无形的水”和“秋风”意象即是本文所说的“万古长空”、鸿蒙宇宙;“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即是“一朝风月”,即是对于当下存在的体悟,也就是禅宗的“悟”。“禅宗启示人们一种觉悟,就是超越有限和无限、瞬间和永恒的对立,把永恒引到当下、瞬间,要人们从当下、瞬间去体验永恒”,“空灵的美感,就是使人们在‘万古长空’的氛围中欣赏、体验眼前的‘一朝风月’之美。永恒就在当下。这时人们的心境不再是忧伤,而是平静、恬淡,有一种解脱感和自由感,‘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了悟生命的意义,获得一种形而上的愉悦”。《十四行集》的27首诗都具有这样的美学品格,它的从瞬间去体验永恒的思想,即为其有空灵美的重要表现。
第二,“天人合一”及其《易经》的转化、化成意识,本身就是空灵美的基本品格。具体而言,《十四行集》的诗作中展现的那种超越实用性的体验,在灾难中得以升华的转化思想,既是从外界转到更为开阔的精神世界,也是从功利、实用转向非功利、非实用。这种从物质世界向精神务虚层面的超越,就是空灵美最主要的体现。因为唯有这样,才能达到畅达、自由之境。所谓化身万物,不是化为虚空,而是化为更高远的宇宙自然。
第三,抒情主人公具有的豁达、从容、淡定的人生态度与人生境界,向更高自由追求的高远情致,他的飞翔性体验,从死、“脱落”里达致生的境界,像歌声“终归剩下了音乐的身躯/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的超验性升华思想,也是《十四行集》空灵美的具体体现。因为在灾难岁月中,主体能够从容面对涌来的彗星、狂风和死亡,从而呈现出来的这种豁达、豁然,就是悟,就是禅悦。
可以说,整部《十四行集》最能凸显上述三个方面的诗作就是第16首《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一诗:
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化身为一望无边的远景,/化成面前的广漠的平原,/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长、我们的忧愁/是某某山坡的一棵松树,/是某某城上的一片浓雾;//我们随着风吹,随着水流,/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化成蹊径上行人的生命。
这首诗传达的是佛教“化身万物”和《易经》“天人合一”的思想。它传达的化成意识,转化思想,充满诗意,能给人一种精神的愉悦。这个“化”,并非堕落,而是人类向上、向远的根本性本质。
同时,这首诗借山巅、原野、山川、松树和风、水、云、雾等意象,传达万事万物相互关联、相互关情的思维特征,是典型的从“万古长空”体悟“一朝风月”的禅宗方法。山巅、原野、山川、松树意象是“静”,按照禅语,静乃空寂,是宇宙之本;风、水、云雾等意象是“动”,这动乃灵动,有飘逸之状。最后,由于化解、转化,抒情主人公呈现出的情感是淡定从容的。总之,冯至诗歌的空灵之美,即指这种“万古长空”的悠悠千古的崇高追求及其超越体验的化解、转化之美。
新诗史上,冯至诗歌的这种特征与美学个性,其他的一些诗人,如废名、林庚等诗人不同。他们的诗,如林庚的《蝴蝶》等,能够“落想天外”,并且有从“万古长空”体悟“一朝风月”的特性:
如其春天只有一次的相遇/那该是怎样的不舍得失去/为什么我们又是说不定/要抓住一只正飞的蝴蝶呢/它只有这一次的生命//苇叶的笛声吹动了满山满村/象征那五月来了/不美吗?这时的黄昏/把青春卖于希望的人/因青春而失望了//快乐是这样的时候/当我醒来天如水一般的清/那像你的眼睛!/说我消瘦了,我的心/轻轻地落出天外//听惯了来复枪声/会想到命长是一件可笑的事吧/不是吗?/五月里的杜鹃,野有鹿鸣。(《蝴蝶》)但相比较而言,冯至的诗,没有《蝴蝶》诗中所展现出的这种超越常人的菩萨拈花微笑般的超脱,而多了些深沉与执着,现实性品格比较明显。
进一步来说,冯至《十四行集》的空灵美并非王维、韦应物、苏轼等的一些寄情山水之作,同样不是谈禅说佛的宗教教义宣示,因此,与废名、林庚的“禅”趣内质上一定的差异,冯至的诗侧重于对处于困境中的现代人的生存及其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它的现实性品格是非常浓厚的。它包含着对于生命存在及其人类命运的积极深沉的思考;它那在战争、黑暗中探求光明的鲜明的时代性、历史性因素;它有关于在日常生活里寻找生命意义的深刻的存在因素;它吸收了传统中国宗教中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成果,比如说万物一体的思想、化成意识、现代性时间意识等,用以阐释现代人生及其命运的新生路径等。这是冯至诗的超越性与时代性的重要特征。冯至的诗,不是废名、林庚的“晚唐的美丽”,而是现代现实的认真与执着。因此,《十四行集》既具有空灵美———个体生命及其人类向高、向上、向远、向美的情趣和人生境界追求的美学样态,也具有“正当的生死,认真的为人”的现实性品格。这在新诗美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三、十四行诗体及其“圆形之美”
十四行诗是西方的的一种格律诗体,也是新文学产生以来被介绍、移植到中国的一种诗体。
这种诗体的格律主要从音步、诗行、段式、韵式等四个方面构建起来。在现代诗歌史上,冯至的《十四行集》是最有特色的十四行诗的实验性诗集之一。它以意体十四行诗的审美原则书写。然而,它的十四行诗却达到了圆熟自如的境界,标志着这种诗体已经中国化。这也是冯至《十四行集》诗美建构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现代汉诗发展史上,十四行诗的翻译和实践,有四个时期。20世纪20年代,是十四行体在中国的输入期,郑伯奇及其新月的一些诗人在此阶段成就最大。20世纪30、40年代,是十四行体在中国的发展期。《诗刊》、《现代》及冯至是主要的探索者。20世纪50、70年代,是十四行诗在中国的蛰伏期,20世纪80、90年代是繁荣期①。新诗史上,新月诗人启动了这种诗体诗美建构的首创性实践,他们以“体制的输入和实验”为契机①,把十四行体这种西方诗体当作他们诗美建构的重要内容与参照,做到了“洋为中用”,为他们的新格律诗实践找到依据。如20世纪20年代中期,闻一多翻译了十四行诗《白朗宁夫人的情诗》,徐志摩做了解读,并就这种诗体的沿革做了介绍:“因为商籁体(一多译)那诗格是抒情诗体例中最美最庄严,最严格亦最有弹性的一格,在英国文学史上从汤麦士槐哀德爵士到阿寨沙孟士这四百年间经过不少名手的应用还不曾穷尽它变化的可能。
这本是意大利的诗体,彼屈阿克的情诗多是商籁体。在英国槐哀德与石磊伯爵最初试用时是完全仿效彼屈阿克的体裁与音韵的组织……白朗宁夫人当然是最显著的一名。她的地位在莎士比亚与罗刹蒂中间。初学诗的很多起首就试写商籁体,正如我们学做诗先学律诗,但很少人写得出色……商籁体是西洋诗式中格律最严谨的,最适宜于表现深沉的盘旋的情绪。像是山风,像是海潮,它的是有圆浑的回响的声音。在能手中它是一只完全的琴弦,它有最激昂的高音,也有最呜咽的幽声……当初槐哀德与石磊伯爵既然能把这原种从意大利移植到英国,后来果然开结成异样的花朵,我们现在,在解放与建设我们文字运动中,为什么就没有希望再把它从英国移植到我们这里来?”
经过新月诗人的提倡、实践,到了20世纪30、40年代,十四行诗在现代中国诗人们笔下,已经和古典格律诗一样,被继承借鉴发展下来,成了现代新诗美学建构的重要参考资源之一。如朱湘《石门集》第三编中的十四行诗有71首,其中英体17首,意体54首。朱湘的英体第一首如《看,看远方的那个峰燧》的开头:
看,看远方的那个峰燧/在边关百尺上扬起光华/它曾经照过胡兵结队,/悄无声的骏马驰走平沙。
采用的是英体的交韵ABAB式;他的意体第一首如《一个一个的人就中蕴藏》:“一个一个的人,就中蕴藏/有无限的情与无限的力。/冲突着,他们掺和在一起,/再没有相谐,成美的时光。”采用意体的抱韵ABBA式。冯至的《十四行集》写成于20世纪40年代初。这部晚出朱湘《石门集》近10年的诗集,在朱湘基础上又有许多的新探索。所以有人认为,“冯至的《十四行集》成为中国十四行诗的成熟之作。诗集做到了情理交融、内容和形式、思想和艺术、使用格律和语调自然的统一。这正是中国诗人移植十四行诗所追求的境界。”
冯至的十四行体诗写作,比之朱湘,是达到了圆熟自如的审美境界的。
十四行诗的格律之美,主要体现在它的音步(音组)、节奏之美;诗行的均齐与变化之美;段式之美(“最佳的十四行,应该是个360度的圆形,其内在结构是书写一个单纯意念或情绪的自然完整过程;十四行的段式和韵式同内在结构的进展相契合,呈现内在和外在美的统一;力求在音韵乐段上体现出浑然美、整体美、回环美和协和美”)和韵式美四个方面。冯至的《十四行集》也从这四个方面入手写成,并达到了“圆形之美”的美学效果。第一,它整体上具有了整体美、回环美。
《十四行集》有27首诗构成。这27首诗,计378行,整体上做到了对称美和回环照应美。如它的第1首和第27首,揭示这27首诗整体性的构思、运思模式,具有照应、绾结的功能性特征。第2首到第14首,在生命及其转化意义上,抒发人生的深刻的感受与情思;第15首到第26首诗,也在生命及其转化以及生活智慧的基点上抒发人生哲思,两部分具有对称美。前14首为“起承”结构功能,后13首具有“转合”结构功能,整体上达到了“圆形之美”。第二,《十四行集》的每一首诗,也具有起承转合有度的“圆形之美”。如第1首《我们准备着》,起承转合的抒情结构理路相当明晰。第1节为“起”,第2节为“承”,第3节为“转”,第4节为“合”。“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两行又巧妙照应,诗的“圆形之美”特征相当突出。所以有人认为它“把全诗十四行划分成若干乐段,并在诗中关上粘下,把全诗的每一句、每一意象都网在一起给人以整体美。十四行体用双交韵和抱韵,变体还用随韵,再加上频繁换韵,使诗韵交错穿插具有回环美”。这与它的韵式的交韵和抱韵构成的回环美共同形成了《十四行集》形式上的圆形美。
冯至《十四行集》的诗美建构,还体现它的诗行建构上。这主要从表1的“音数和音组”、“诗行字数”这两个诗行建构的最基本层面可以发见这种探索实践的清晰轨迹(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到,冯至为汉语十四行诗美探索做的另一个重要实验,是把西体十四行的以音为主的方式转化为以“言”(五言的五字、现代汉语的字)为主,从而来建行、探索新诗诗美建构的形式规律。仔细分析起来,冯至《十四行集》的27首诗十四行诗对于意体十四行的改造,最主要的在音组和诗行两个方面。它的6到12字一行,3到5个音组一行的诗行建构的实践,是以音与字数的变化显示着这种建构变化的,其中基本的规律是10言(字)4音尺的诗行建构。这在27首诗里占有10首之多。依赖于这种变化,《十四行集》的27首诗就有近20种变体。所以,从“十四行”的意体1种体式到近20种变体,从每一行的音组和字数的排列到27首诗的总计378行诗的实践,《十四行集》实际上为十四行格律体的诗体和建行创造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验。它的行有定数(14行),行字、音组基本固定(10言、4音组)又变化无限的建行探索,为十四行诗的汉语化探索了新路径。当我们用数学和统计学方法对于这部新诗经典的典律构成做探究的时候,会发现《十四行集》诗美建构的很多规律及其转化的痕迹。这是颇有创造的实验行为,对于新诗格律形式创造以相当深刻的启发。所以林庚说:“我是从两方面开始这种探索的。一方面致力于把握现代生活语言中全新的节奏,因为它正是构成新诗的物质基础;一方面追溯中国民族诗歌形式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半个世纪以来,我在新诗创作方面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对新诗的格律也逐渐形成了一些个人的意见……要求寻求生活发展中含有的新音组……要服从于中国民族语言在诗歌形式上普遍遵循的‘半逗律’也就是将诗行划分为相对平衡的上下两个半段,从而在半行上形成一个类似‘逗’的节奏点。三、要求这个节奏点保持在稳定的位置上。”林庚诗的理论与创造,受到过新月派诸诗人,尤其是冯至等人的深刻影响。
因此,从诗美艺术建构角度来审视,《十四行集》运用“十四行”这一西方格律体诗歌艺术形式,已经娴熟自如。它既显示出其诗体特有的“圆形之美”,又显示出英转汉语后汉诗语言所具有的畅达自如美。《十四行集》的诗,既有律诗的秩序感,又时有变化;既有外形的格律,又有内在的错落美,达到了整饬而舒展自然的美学效果。冯至十四行诗将西方严格的格律诗中国化了。《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等就是典型,可以说,十四行诗体经徐志摩、朱湘、孙大雨,再到冯至的实践,已经与自由体一样,成了现代中国读者喜爱的一种现代诗体。这其中,冯至及其《十四行集》的影响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