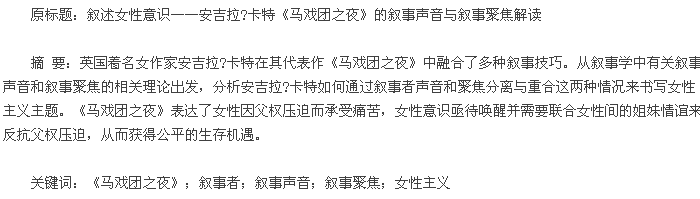
一、引言
安吉拉·卡特(1940—1992)以独特的写作风格驰名英语文坛,其写作风格混杂了魔幻写实、哥特式与女性主义。2006 年众多女性读者在英国掀起一股卡特作品回顾热潮。在两年后的《泰晤士报》“战后 50 位英国最伟大作家”评选中,安吉拉·卡特位居第十。《马戏团之夜》是卡特的倒数第二部小说,发表于 1984 年,次年获詹姆斯·泰特·布雷克奖。小说一经出版便赢得学者的众多关注,但是我国对卡特的研究起步较晚。纵观国内外对该小说的研究,多从女性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狂欢化、互文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角度入手。虽然国内外研究关注《马戏团之夜》的女性主义主题,但是目前并没有学者从叙事学角度对该文本进行分析,其小说独特的叙事声音和叙事视角长期遭到忽视。本文以叙事学为基础,从叙事者的叙事声音和叙事聚焦入手解读《马戏团之夜》的女性主义思想, 表明女性因父权压迫而承受痛苦,女性意识亟待唤醒并需要联合女性间的姐妹情谊来反抗父权压迫,从而获得公平的生存机遇。
二、理论框架
叙事声音和叙事视角是叙事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对这两个概念都未进行区分,理所当然地认为叙事声音和叙事视角是重合的。直到法国叙述学家热奈特在《叙述话语》一书中才廓清了这两个概念,即谁说和谁看的问题。叙事声音是叙述者的声音,但是叙事视角可以是叙述者的视角也可以是人物角色的视角。也就是说谁说和谁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说的人不一定是看的人。自 20 世纪初以来,在第三人称小说中,叙述者常常放弃自己的视角转而用故事中人物的视角来叙事。
在热奈特的《叙事话语》中,他将叙事视角分为三类,并用抽象的“聚焦(focalization)来替代视角一词”。
三种聚焦分别为:(1)零聚焦,相当于传统的全知视角,可用公式“叙述者>人物”。(2)内聚焦,叙述者所知道的仅限于人物所知道的,可用公式“叙述者=人物”。其中内聚焦又可细分为三类:固定式内聚焦,不定式内聚焦和多重式内聚焦。(3)外聚焦,叙述者所知道的比人物少,可用公式“叙述者<人物”。
本文主要应用叙事学中的叙事声音和热奈特的叙事聚焦来分析卡特是如何巧妙应用叙事技巧在“谁说”和“谁看”、重合与不重合这两种状态下书写女性意识。
三、叙事者叙事声音与叙事聚焦分离:新女性形象
《马戏团之夜》由 3 个部分组成,分别以地名命名:伦敦、匹兹堡和西伯利亚。飞飞所在的柯尼尔上校的帝国马戏团以伦敦为起点,亦以伦敦为终点。在伦敦部分,小说以采访的形式展开,男主人公华尔斯是一名美国记者,飞飞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羽翼全丰的“鸟女”。 在这一部分作者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事方式,用“他/她”或其名字指涉故事中的人物。虽然叙事声音来自于第三人称叙述者,但是这一章采用的聚焦却是华尔斯的固定式内聚焦,读者所了解的基本限制在华尔斯的所知所感之中。在这一章,第三人称叙述者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全知视角,采用华尔斯固定式内视角来呈现故事,但偶尔全知叙述者会出现,以证明他的在场,也就是说在这一章中存在着零聚焦与内聚焦的变换:
一条宽大的绉边衬裤,显然是掉落在当初被随手扔掷的地方。它覆盖着某件物品,也许是座时钟,也许是大理石半身像,也可能是骨灰坛,由于完全被覆盖着,所以可能是任何东西。……总之,这个房间称得上是一项女性的杰作,展示出细腻精致的女人邋遢相,毫不做作掩饰,足以恫吓任何一位比眼前这位记者见识过更多世面的年轻男子。
上述这段的叙事声音与叙事聚焦看似出自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但仔细阅读之后我们便会发现,在“总之”之前的聚焦者并不是全知叙述者而是华尔斯,如果聚焦者是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他就应该知道在衬裤底下的就是时钟而不需多加猜测,而之所以会猜测是因为这里的聚焦者并不是全知叙述者而是华尔斯,因此叙事声音与叙事聚焦分离,声音来自全知叙述者,聚焦者则是男主人公华尔斯。在此,说的人和看的人并未统一。而“总之”之后的评论则出自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也就是说“总之”之后的聚焦属于零聚焦其叙事声音和叙事聚焦则完全重合,此时 全知叙述者不再限制自己的视角对飞飞的房间做了评论称之为“女性杰作”。
小说所展示的飞飞形象是通过华尔斯的固定式内视角展现出来的,全知叙述者只是偶尔出来进行评论然后又巧妙滑入华尔斯的聚焦。在华尔斯的眼中飞飞完全不具备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特点,她的笑太大声、太自由,“金发女人放声狂笑”,“她赞赏地咯咯笑着”;她太过粗犷,“靠近点儿看她,不得不说,她长得实在不像个天使,反而比较像匹用来拉货车的母马。……她那张椭圆形的宽脸,看起来就像用来盛肉的大盘子一样,是用粗粘土在普通陶轮上拉成的坯”;她的饮食太过粗野,“她狼吞虎咽,她拼命把食物填进肚子里,她把酱汁泼溅在自己身上,她吮吸刀子的豌豆泥,她有个与身材尺寸颇成比例的大喉咙,以及伊丽莎白时代的餐桌礼仪”。这一系列描述出自华尔斯的感知,但是叙事声音则来自全知叙述者,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华尔斯对飞飞厌恶之情,这与他最后与飞飞坠入爱河颇成对比。这一厌恶之情却恰能说明聚焦者是男主角华尔斯而不是全知叙述者。一般而言,后者要求客观真实地呈现故事。而对于采访期间的华尔斯来说,飞飞丝毫不具备女性的优雅,她的笑太放肆,她的举动太男性化,她完全跳出了维多利亚时代男性对女性的期待。而卡特正是利用华尔斯的固定式内视角将男性对飞飞的偏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讽刺男性所持有的女性期待,从而反衬出飞飞表现出来的男性气质以及女性的自信和优越感。
四、叙述者叙事声音与叙事聚焦的重合:蕾丝边和蕾丝边社团
在小说的另外两章匹兹堡和西伯利亚中,作者运用了较多的零聚焦,就是说叙述者的叙事声音和叙事聚焦完全重合。零聚焦叙述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全知叙述,其特点是叙述者没有固定的观察位置,拥有上帝般的视角,既能够通古知今,也能够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
在匹兹堡这一章中,有两个特殊的人物米娘和阿比西尼亚公主。在马戏团,没有人懂得米娘的语言,而阿比西尼亚公主从未讲过一句话。这两个角色象征着那些被男权社会剥夺声音的女性。由于她们的沉默,她们的故事无人知晓,但是零聚焦者通过他的特权向读者讲述了她们的故事尤其是米娘的悲惨际遇。
在米娘遇到飞飞之前,她的人生令人唏嘘不已。她是杀人犯的女儿。她的父亲因为怀疑妻子与驻扎在他家附近的士兵有染而将面包刀刺向了他的妻子而非那个士兵。而她的父亲为了寻找丢失在池塘的面包刀也溺水而亡。一夜之间,米娘和她的妹妹成了孤儿。显然米娘家的三个女性是男性嫉妒与懦弱的受害者。
失去了父母的保护,为了生存米娘沦为乞丐也做过小偷。之后她遇到了 M 先生,M 先生是一个虚伪的骗子,他为自己的骗局冠以道德的假名。他为米娘提供食物、住宿并提供给她一份所谓的“工作”——假扮年轻女孩的幽灵,以此向死去女孩的父母骗取钱财。M 先生为了防止米娘逃跑将她软禁在自己的住处并每日从她那获取他的性满足。然而无是非观念的米娘“以为自己身在天堂”,而零聚焦者则一语点破“但那其实是个傻子的天堂”。
之后 M 先生的骗局被揭穿受到了法律的制裁,米娘则被裁定是 M 先生的受害者而无罪释放。虽然米娘是 M 先生的受害者,但是米娘的无知与软弱也是造成她悲剧人生的原因之一。
米娘与猿佬儿的结合亦是一个悲剧。在这段婚姻中,米娘受尽了家庭暴力的折磨。而米娘最惨的遭遇是在跟猿佬儿到马戏团的第 7 天,三个摩洛哥杂技演员在给她吸了点印度大麻后轮番强暴了她。
大力士是米娘的情人,而他对她只有性欲,且是他将米娘陷于虎掌之下而几近丧命。
米娘从男性那获得的是无尽的痛苦,而她的沉默与顺从加深了她的悲剧。卡特笔下的米娘实际上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典型代表——家中的天使,完全顺从家中的男人,毫无女性意识。幸运的是男主角将她从虎掌之下解救下来,而飞飞则帮她转变为一个新女性。飞飞发现米娘唱歌的天赋并为她在阿比西尼亚公主那找到了一份工作。之后米娘与公主相恋,从此远离男性所给予的痛苦。
小说的第三章运用了零聚焦与人物固定式内聚焦交替叙述的叙述技巧。在结束彼得堡的最后一场演出后,飞飞以及马戏团的所有成员登上了穿越西伯利亚驶向日本的火车。途中火车被一群政治犯所引爆,飞飞以及马戏团的其他成员被俘虏而华尔斯因被埋在桌布和餐巾纸下而被单独留下,之后被一圆形监狱的女囚欧嘉·亚历珊卓芙娜唤醒。在这一章中零聚焦暂时中断飞飞的故事,而将聚焦伸向西伯利亚深处的圆形监狱,而监狱中只囚禁着一种罪犯——犯了杀夫罪的女性。
在伯爵夫人的圆形监狱里,女囚们被禁止与外界有任何形式的联系,就连女看守们也需要带着头套。她们唯一能够做的就只有关在自己的牢房冥想她们所犯下的罪。欧嘉·亚历珊卓芙娜一遍又一遍地冥想自己所犯的罪,最后认定自己无罪,而且她还得出一个结论,“这些守卫就跟她一样,也是这个地方的受害者”。于是她决定联合同样被囚禁在此的女看守逃离伯爵夫人的凝视,推翻这一父权统治的代言人。她暗中与其中的一个守卫薇拉·安缀耶芙娜联系,监狱里没有笔,她们便用女性特有的经血联系。女性的经血通常与不洁联系在一起,“经血被认为对于恶魔和不洁的精灵具有吸引力,一个经期妇女的出现可以使牛奶酸腐,可以使她走过的草坪枯死。”
而正是这令男性所恐惧的经血帮助欧嘉以及监狱里的其他女性获得同性之爱,并最终逃离了伯爵夫人的凝视重获得自由,并决定在西伯利亚荒野建立一个原始乌托邦。
女同性恋乌托邦世界可以视作对父权社会最为激进的反抗,完全将男性排除在女性社区之外。从米娘和阿比西尼亚公主的同性之爱以及西伯利亚荒野的同性恋社区可知,在父权社会,传统女性遭受着莫大的痛苦,难逃被物化的命运。同性之爱、姐妹之情则能够武装女性,从而反抗父权压迫,继而颠覆父权。
五、小结
安吉拉·卡特将自己定义为女性主义作家,伊莱恩·肖瓦尔特称卡特“在英国女性文学的开端以及转型期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毫无疑问,《马戏团之夜》带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特点。同时,卡特在创作《马戏团之夜》时运用了繁复的叙事技巧,叙事者的叙事声音与叙事聚焦巧妙地分离与重合。迈克·伍德曾说过:“卡特的文字看上去(通常也是)缺乏控制。”
其实不然,繁复的叙事技巧正是卡特的特色之一,她的叙事技巧并没有扰乱她的叙事,相反这些技巧恰到好处地服务于故事情节。卡特通过华尔斯固定式内视角为我们展现了独立自信的新女性形象飞飞;通过全知叙述者的特权描绘了米娘的悲惨际遇以及和阿比西尼亚公主的同性之爱;在第三章中全知叙事者中断叙述时间向我们展示了西伯利亚圆形监狱的女囚与女看守为爱冲破枷锁颠覆父权凝视奔向自由。
参考文献:
[1]Genette G. Narrative Discourse [M].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2]安吉拉·卡特.马戏团之夜[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