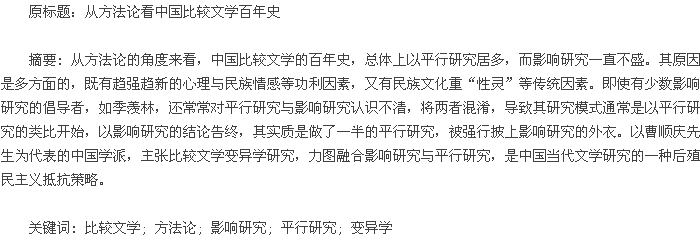
一、中国比较文学的分期及研究方法
第一,20 世纪初到 40 年代,是中国比较文学初期阶段。这一时期,比较文学学者大多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这一现象非常显着。胡适、陈独秀等“五四”时期激进的学者,大都持这样一种论调: 西方文化远胜东方( 中国) 文化。因此,他们怀着一种匡世济民的热忱,提倡学习西方文化,抛弃中国旧文化。而以刘师培、吴宓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却主张发扬“国粹”,在现代社会延续中国文化道统。但有意无意,这些保守主义者也是以西方文化作为衡量中国文化价值的标准,实际上也暗含了中国不如西方的判断。这种文学之间的比较,包含鲜明的价值判断因素,是尚未摆脱“比较”一词在美学意义上的全部含义,是法国学派所不支持的一种原生态的比较,在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毕竟,比较文学并不是文学的比较。
“五四”前后的这种文学比较,即使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政治、经济、军事、哲学、语言学、社会学等方面单纯的优劣评判,能称得上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也大多属于平行研究范畴,如梁启超的《丽韩十家文钞序》、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人间词话》、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鲜见影响研究论着。
这种平行研究的方法一直被初期的比较文学学者所沿袭。如郑振铎的《民间故事巧合与转变》和《中山狼故事之变异》、梁宗岱的《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钱锺书的《谈艺录》、闻一多的《诗与格律》和《文学的历史动向》、朱光潜的《诗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杨宪益的《零墨新笺》、李健吾的《咀华集》和《咀华二集》、李广田的《诗的艺术》等一大批论着,皆为平行研究的成果,其中不乏经典之作。钱钟书的《谈艺录》秉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理念,对中西文论进行了相互阐发比较,就是平行研究的典范。这一时期,大概只有郑振铎与沈雁冰合着的《法国文学对于欧洲文学的影响》和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是典型的影响研究,算是难得的例外了。
第二,1950 年到 1977 年,属于中国比较文学衰滞期。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比较文学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伪科学,因此,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受阻,其发展一度陷入停滞。但仍有少数学者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冯雪峰的《鲁迅与果戈理》和《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和其他欧洲国家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曹未风的《莎士比亚在中国》和《鲁迅先生与外国文学》、阿英的《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范存忠的《< 赵氏孤儿 > 在启蒙的英国》、钱钟书的《林纾的翻译》等。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仅有的这些着述中,几乎全部是采用影响研究的方式。这种情形在中国比较文学史上绝无仅有,实在是值得注意的奇特现象。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使得比较文学研究本身就成为一个危险的领域,而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的危险尤甚于影响研究。因为平行研究的主旨是追求具有普世价值的理论,这种普世价值自然与主张文学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相违背,因此,学者们不敢贸然踏脚,是为情理之事。而影响研究相对安全,这也就解释了此时期仅有的比较文学研究几乎全部采用影响研究方法的原因了。
第三,1978 年到 20 世纪末,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期,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快速发展期。这一时期的比较文学成果,大部分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如标志着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研究复兴的巨着———1979 年钱钟书的《管锥编》,据赵毅衡先生考证,里面涉及中西文学互相参照比较的条目有二百多条,基本上都是平行研究。“在前四卷一千二百多个条目中,包括有中西文学互相参照比较的条目共二百多条。我们把这二百多条略事整理,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情况: 涉及中西文学实际影响的条目实际上只有六七条。……以钱先生阅读之广、记忆力之强,在中西文学交流的长期历史中,完全可多找出一些实际影响的例子,但钱先生宁愿把注意力集中在另一方面———平行研究方面。”[1]又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金克木的《比较文化论集》、杨周翰的《攻玉集》、范存忠的《英国问讯论集》、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黄药眠与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卢善庆的《近代中西美学比较》、狄兆俊的《中英比较诗学》、周来祥与陈炎合着的《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等,主要使用的方法还是对中西文学与文论进行平行研究。这一时期,只有茅盾的《外国戏剧在中国》、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史论文集》、李明滨的《中国文学在苏联》、赵毅衡的《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等少数的比较文学学术专着运用影响研究方法。这些少数派,几乎被数量上居绝对优势的平行研究所淹没。
第四,从 21 世纪开始,中国比较文学进入了反思与探索并存的转型期。新时期的比较文学,依然是平行研究居多,但是由于季羡林等老一辈学者对平行研究的批判与反思,有向影响研究路数回归的趋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运用影响研究手法的比较文学着作,如 2004 年出版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文库”,包括孟华的《他者的镜像: 中国与法兰西》和《中法文学关系史》、张哲俊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刘建辉的《东亚近代化黎明: 中日文化互动的轨迹》、车槿山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等。
二、平行研究占主导地位的原因
中国比较文学前三个时期,从方法论看,平行研究占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影响研究一直不盛,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四个原因。
( 一) 趋强趋新的心理
崇拜强者的心理在此多少也有一定的影响。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已跃居世界强国,超越法国,并逐步成为世界第一霸主。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模式,是其在文学研究领域对欧洲的挑战与超越。其奉行的路数,与 20 世纪中期一度盛行的新批评有内在的关联,都是主张抛弃传统的历史背景研究,而代之以关注文本本身的美学价值。只不过比较文学将新批评的这种关注扩大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之间的文本之上,甚至引进到学科的跨越之上。这种在文学研究上的开放心态,一方面与美国的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相契,另一方面,也是对日趋保留的欧洲大陆的厌烦与挑战。中国学者在面临外部政治或文化势力入侵时期,或有感于民族文化的危机,或有感于国运的衰微,出于借外国先进科学文化振兴中华民族之梦想,出于对强者的崇拜,借鉴学习美国是情理之中的。在科学技术上学习美国,在比较文学上像美国学派一样主张平行研究,似乎不值得大惊小怪。此外,中国人在五四之后,抛弃了传统的精神,抛弃了经典之学,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表现为普遍地好新好奇,追求时尚之学。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在时间上后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因此给人的感觉是更时尚更新鲜,而法国学派自然显得更老旧、已过时。在趋新的心态之下,中国人更愿意进行平行研究,自然是毫不奇怪了。
( 二) 民族情感
中华民族是爱面子的民族,或者说是有自尊心的民族。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最能给国家或民族挣面子的事,莫过于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学影响了他国或他民族的文学。这也是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最热衷的研究领域。法国学派的研究往往显示欧洲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如何影响了其他国家,如何引领了世界文学的潮流,其他国家受到法国文学的多少恩惠,欠了法国文学的多少债。因此,影响研究被美国学派指责为“文学的外贸”。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出于民族本性与爱国自尊心,本能的反应应该是选择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但中国现当代文学多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而鲜有输出影响者,因此,学者们无奈之下,只能求助于中国古典文学。然而,年代久远,烟波浩渺,要考证其流传至西方的路径,拿出中国古典文学影响西方文学的确凿证据,实属不易。这也是影响研究难做与成果少的客观原因。于是,中国大多数的比较文学学者们只好拿本国的古典文学来与西方文学类比,以平行研究为法宝,凸显出“你们西方有的我们中国也有,你们西方没有的我们中国还有”的心态。
非常吊诡的是,中华民族又是个非常自卑的民族,有时极易堕入妄自菲薄这种与强烈的自尊心相背离的一端。然而,无论是自尊还是自卑,中国比较文学的学者最终都走向选择平行研究的方式。前面已讲了,自尊心如何使学者们以平行类比的方式挣得“我们祖上也阔过”的面子,现在看看自卑心为何也让学者们选择了平行研究这一看似奇怪的现象。“五四”前后,因为看到中国与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差距,出于自卑心,或者是出于爱国心———这两种心理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惊人的相似,都表现出对本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批判其处处不如西方———许多学者不好意思去研究中国如何影响了西方,或认为没有必要去研究中国受到了西方的多少影响。不好意思是因为自卑———中国都这样落后挨打了,怎么还好意思去吹嘘自己过去的 辉 煌 呢? 认 为 没 有 必 要 也 是 因 为 自卑———中国如果早点接受西方的影响,如何会落到今日如此受列强凌辱的境地? 这种心态,使比较文学学者大多摒弃影响研究而选择平行研究。当然,这种平行比较大多是前面我们说过的中西方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对比,其或明显或暗含的价值判断也是相似的,即中国不如西方。
如朱光潜写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诗论》,属于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着作,但里面其实也隐含着中国诗学不发西方诗学的价值判断。他在1942 年抗战版序中说: “诗学在中国不甚发达……中国人的心理偏向重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谨严的分析与逻辑的归纳恰是治诗学者所需要的方法。诗学的忽略总是一种不幸。”[2]( 抗战版序)因此,他认为中国诗学应该向西方学习。1984 年三联版《后记》中,朱光潜又写道: “在我过去的写作中,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独到见解的,还是这本《诗论》。我在这里试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2]( P345)阐发学本应该是中西诗学相互阐释、相互印证的一种学术行为。但是,从朱光潜的“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这貌似公允的话中,还是可以发现其着重点和立足点在于西方诗论。为什么说这句话“貌似公允”呢?
首先,前半句“用西方诗论来……中国古典诗歌”,接着的后半句是“用中国诗论来……西方诗论”,乍一看,这是非常完美的并列结构,表示对西方诗论和中国诗论同等待之,一视同仁。但是,这句话真正的关键却在于其使用的两个动词———“解释”和“印证”。“解释”的行为是主动的、积极的,“印证”的态度是被动的、消极的。当然,如果要进一步发挥,扯上文化批评,还可以说前者是阳性的、主宰的、中心的,后者是阴性的、驯顺的、边缘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这句话虽然使用了并列结构,但是前半句话和后半句话的态度却都倾向于将西方诗论作为中心。这一点,从《诗论》的整体内容来看,也可以得到印证。这其实反映了朱光潜潜意识里很自然地将西方诗论置于优越地位,认为中国诗论只是辅证西方诗论正确性的材料而已。
( 三) 平行研究与中国民族传统特性相契合
中国古人就喜欢平行研究,如对于南北方等地域文学异同的比较,作家作品优劣、异同的评论,诗画乐禅的跨学科比较等。当然,里面也有些是讲不同地域的风格或作家彼此间的影响,但这一类的讨论非常少,更多的是平行比较。
例如,《世说新语·文学篇》说: 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 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月。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说: 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 山东风俗,不通击难。令狐德棻等撰《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说: ( 南方) 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邺卫; ( 北方) 建言务存质朴,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说: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义贞刚,重乎气质。南北文学的比较,在中国文化与文学中一直长盛不衰,并扩展到书画、禅学、戏曲等领域。
作家作品的比较,也早已有之。汉初刘安认为: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 班固《离骚序》) 扬雄在《法言》中也对众作家进行过点评: 屈原过以浮,司马相如过以虚; 司马迁之说,圣人将有取,刘安之说,鲜取焉尔; 孔子爱义,司马迁爱奇。至于曹丕《典论·论文》对七子的评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历代作家作品的研究与点评,更是脍炙人口,为人熟知。中国历代诗话、词话、曲话对作家作品的风格技巧等方面的比较不胜枚举。
诗画乐禅的跨学科比较,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也是历史久远。关于诗与音乐的关系,最早出自《尚书·尧典》: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又如,《毛诗序》云: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 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里面已初具诗与乐的比较了。《文心雕龙·乐府》云: “诗为乐心,声为乐体。”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云: “诗是乐之心,乐为诗之声,故诗乐同其功也。”诗画比较也极为常见,如苏轼《东坡题跋·书摩诘 <蓝田烟雨 > 》云: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清人叶燮在《赤霞楼诗集序》说: “画者,天地无声之诗; 诗者,天地无色之画。”
“画者形也,形依情则深; 诗者情也,情附形则显。”类似言论,比比皆是。至于以禅喻诗,亦早已有之。李之仪《与李去言书》云: “说禅作诗本无差别。”刘克庄在《题何秀才诗禅方丈》中说:“诗家以少陵为祖,其说曰: ‘语不惊人死不休。’
禅家以达摩为祖,其说曰: ‘不立文字。’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也。……夫至言妙之固不在于言语文字,然舍真实而求虚幻,厌切近而慕阔远,久而忘返,愚恐君之禅进而诗退矣。”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更是显例。[3]( P577 ~613)虽然这种平行研究可能还不是比较文学学科意义上的研究方式,但这种爱平行比较和跨学科比较的天性和传统,有助于中国学者更倾向接受比较文学平行研究。
( 四) 中国人重“性灵”的传统
中国学者讲究灵性、灵气,反对僵直、死板;讲究顿悟,而以渐悟为劣; 在义理、考据之间,更倾向于义理之学,而厌烦考据之风。渐悟类似于一步一个脚印,实在地摸索着迂回前进,最终登上峰顶,得见佛光。顿悟要求是电光火石一刹那的灵光附体,醍醐灌顶。影响研究埋首于地下,挖掘历史的遗迹,爬梳相隔两地者的交通往来之证据,这种踏实而略显烦琐的学术气质,确实更近于渐悟。而从平行研究的特点来看,天马行空,高蹈而鹏举,凭丰富的想象力找到不同事物之间的类似点,其学术气质确实类似于顿悟。考据之学,讲究源流实证,近于影响研究; 义理之学,讲究一般规律,近于平行研究。因此,这种学术精神的传承,也是影响中国比较文学学者选择平行研究的一个原因。
三、影响研究的呼吁与迷误
季羡林早年基本上只认同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而排斥平行研究。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混淆了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导致其实践与理论常相背离。他声称自己做的是影响研究,然而实际上却是做了一半的平行研究。他既不能像平行研究一样最后抽绎出一般的理论,又不能像影响研究一样给出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之间的文学影响的路线或关系。季羡林的比较文学研究模式可以归纳为: 以平行研究式的类比开始,以影响研究式的结论告终; 其实质是做了一半的平行研究,被强行披上了一件影响研究的外衣。这模式是不可取的。这种错误部分原因在于对资料搜集性质的误判,使他混淆了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界限。这种混乱对比较文学学科,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季羡林曾毫不掩饰对平行研究的轻视,而呼吁影响研究方式。如在《民间文学与比较文学》一书的序言中,他说: “简言之,我赞成比较文学研究直接影响的一派。这一点我是无法否认的。限于自己的气质,做学问,我喜欢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对那些高高在上玄之又玄的东西,我不擅长,也不喜欢。”[4]( P2)他反对平行研究,是因为不相信两个类似的文学现象能各自独立地在不同的地方产生。在《一个流传欧亚的笑话》一文中,他先找到两个分别在欧洲和亚洲流传的类似的笑话,然后就断定它们是同一个来源,理由是“创造一个笑话同在自然科学或精神科学上发见一个定律同样地难”,因此不可能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产生相同的笑语; 而且“在中国同欧洲流行的许多寓言和童话都不是在中国或欧洲产生的,而是来自印度”,因此他进一步断定这两个笑语源自印度。[4]( P34)1947 年在《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看寓言和童话》一文中,季羡林从印度找到类似曹冲以船称象的故事,又找到类似于古希腊伊索寓言中的鹳帮狼从喉咙里取骨刺的故事,然后就断定这两个故事都源自印度。他的理由同样是: “创造一个真正动人的故事,同在自然科学上发现一条定律一样的困难。两个隔着几万里的民族哪能竟会创造出同样一个故事来呢?”[4]( P45)可以看出,这种研究充满了主观臆测,丝毫谈不上什么考据,也没有什么逻辑性。稍微懂得一点逻辑学知识的人都能看出,这种因果逻辑关系是错误的。而且,“创造一个真正动人的故事”,是否真的“同在自然科学上发现一条定律一样的困难”? 这是颇值得怀疑的。退一步讲,承认两者的难度相同,也不能说就没有两位科学家发现同一条定律的可能性。如牛顿和莱布尼茨二人没有交换过意见,但几乎同时建立了微积分理论; 克劳修斯和开尔文二人各自独立发现热力学第二定律; 费尔和克鲁伯格同时各自独立发现巨磁电阻效应而分享了 2007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蒙塔格尼尔和盖洛分别独立发现了 HIV 病毒。在文学上,各自独立产生的各种类似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人心相通的信念并非毫无根据,甚至从一些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的相类似的比喻中也可以一窥其斑。如东西方都用家畜比喻“不重要,可牺牲”,用大型野兽比喻“强权”,用狼和狐狸等小型野兽比喻“狡猾凶残”。在各个文化中,用上下左右的位置来比喻,意义都相近,上下是社会地位,左右是政治立场。[5]又如二十世纪初出现的形式论“星座效应”,也充分证明产生类似文学现象的可能性。“艾略特和瑞恰慈,没有听说过什克洛夫斯基或雅克布森,索绪尔与皮尔斯也没有听说过对方名字; ……正在英国开始叙述形式研究的詹姆斯、福斯特、勒博克等人完全不知道在德国或俄国出现的叙述形式研究。
形式主义文论各流派,自发同时出现在欧美各国: 从莫斯科、彼得堡、布拉格、日内瓦,到大洋两岸的两个剑桥,他们不了解别人也在思考类似的问题。”[6]( P5 ~6)当然,呼吁影响研究方式,并没有什么对错之分,但是混淆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的概念,问题就严重了。1946 年,季羡林在《一个故事的演变》中认为,中国关于乞丐从一罐子残羹剩饭中幻想出鸡出蛋、蛋生鸡,终成富翁娶妻生子的美梦,最终把罐子打碎而梦碎的故事源自于印度。
他的依据是梵文中早就有类似的故事。[4]( P23)至于这个故事是如何从印度传到中国,中国的传播路径如何,是什么时候传过来的,由何人传过来,一概未加论证。甚至提都未提,仿佛只要找到印度中有这个相似的故事就算结束了,成功了。这种做法,并非说不可以,但却不是脚踏实地的、扎实的、令人信服的功夫,不是影响研究的那种套路,而有点类似于寻找相似性的平行研究了。季羡林口口声声说自己更愿意做脚踏实地的考据工作,也确信自己所做的是影响研究,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反倒做的正是他自己所反感的平行研究。更糟糕的是,他这种平行研究还只是做了一半,即只是找出相似点,而没有继续从中归纳出什么义理或抽绎出什么理论。他的研究套路与之相类似的文章还有《柳宗元 < 黔之驴 > 取材来源考》《“猫名”寓言的演变》《< 西游记 > 与< 罗摩衍那 >》《一个流传欧亚的笑话》《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看寓言和童话》等,都是以平行研究式的类比开始,然后下了一个影响研究式的结论告终。
在 1985 年《资料工作是影响研究的基础》一文中,季羡林写道: “你如果对一个故事发生了兴趣,想到别的国家的文学中去找相同或者相类的故事,那真如大海捞针。结果总是捞不到的。有时候,‘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样的偶然性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喜悦,一篇短短的不起眼的短文,往往产生于这样的偶然性。其中滋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实不足为外人道也。”[4]( P195 ~196)从其所描述的搜集资料的过程来看,不像是影响研究,而更像是平行研究的第一步———寻找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文学现象的类同。在寻找类同性的过程中,充满了偶然性,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或者说是灵感,也即季羡林所提及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所以说,季羡林所说的搜集资料的过程,其实并不是他所认为的是影响研究的开始,而是平行研究的开端。这也是造成他对自己一些名为“影响研究的论文”的误认与误判的原因。那些论文实际上是做了一半的平行研究的论文。
当然,其他学者典型的影响研究,也可能存在问题。如戈宝权的《中外文学因缘》,其研究路数无疑属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作者在该书的前言中颇为自豪地提到,《< 阿 Q 正传 > 在国外》一书出版后,黄源写信说: “读兄书,其中很多第一手材料,不知花多少时间精力调查、探索而得,深为感佩! 这里虽则没有什么深奥的哲理,但这种实事求是的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的精神,正是我们做学问的基本基础。”紧接着又提及日本大阪外国语学院相浦杲教授的赞誉,他认为中国写的文章,多偏重于空论,而戈宝权的论文则以丰富的史实来说明问题。[7]( 前言,P11)可以看出,戈宝权对自己重史实的研究特色颇为得意。然而,该书存在的问题倒不是混淆了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而是其选编了作者建国以来在比较文学方面的 40 余篇论文,大部分是讲外国作家作品对中国的影响,真正讲到中国文学对外国的影响的很少,只有《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谈阿 Q 正传的世界意义》和《谈茅盾对世界文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等寥寥几篇,明显折射出中国现代文学与理论的弱势处境。
四、方法论的困境与变异学的突破
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在方法论上常常充满疑惑。一方面,以季羡林为代表的学者对 X + Y 式比附的批判,让初学者不敢轻易运用平行研究,以免贻笑大方。另一方面,有些所谓的影响研究,看起来却不那么纯粹,常常与平行研究混淆,难以区分。即使是在季羡林的比较文学论述中,也存在这种迷误。而且采用影响研究,又容易陷入民族自尊心受挫的境地。这种方法论上的困境,制约着中国比较文学的进一步深入发展。直到2005 年,曹顺庆先生提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变异学理论,才打开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在专着《比较文学学》中,曹顺庆先生首先提出“变异性”: “从‘变异’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从以前比较文学文类学研究的‘求同’思维中走出来,从而拓宽文类学的研究视野,为比较文学文类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开拓一片新的园地。”[8]( P269)2006 年初,他为变异学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 “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9]接着,他进一步完善了变异学的理论体系,将变异学定位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其研究从语言、跨国与跨文明形象、文学文本、文化、文学的他国化五个层面进行,具体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10]( P97 ~98)此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系统阐释变异学的理论背景、理论核心、价值意义等,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变异学的理论逻辑,首先是分析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本身的缺憾。影响研究面临的困惑是:
实证性的文学关系也同时包含变异的问题。因为当一国文学传到另一国时,它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变异。实际上,国际文学关系的两大支柱应当是实证与变异,也就是实证性的国际文学关系与变异性的国际文学关系。在法国学派的研究中,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只突出了实证性的一面,即只注重研究存在着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文学,而忽略了变异性的一面。法国学派不但回避谈论审美判断与平行比较的问题,也没有认识到在影响研究中存在着的变异。这是法国学派学科理论的两大缺憾。
平行研究面临的困惑是: 有人提倡比较文学无边论,又有人提倡比较文学应该有边界。然而,无论是提倡比较文学无边论,还是有边论,都是在比较文学的“求同”之上进行研究的,这证明了美国学派倡导的比较文学的根本立足点是建立在“求同”的基础之上的,都没有认识到比较文学的变异性实质。美国比较文学界两种对立的观点揭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面临的一个危机,而这种危机美国学者却恰恰没有看到: 那就是只注重求同,韦勒克是主张“大同”,即全人类都可以“同”,而韦斯坦因只承认“小同”,即西方文化的“同”。他们都没有认识到异质与变异性。美国学者在运用平行研究看待问题时,往往会忽略异质性的问题,这使得比较文学面临着危机。
变异学的理论核心是差异性与变异性的可比性。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同源性”“类同性”是“可比性”的基本立足点,而变异学探讨的是完全差异的对象是否存在可比性的问题。变异学的根本理论认识是: 异质性也是可以比较的。同源中包含了变异,因为同源的文学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在语言翻译层面、文学形象层面、文学文本层面和文化层面都会产生变异,这就是异质性的体现。
在通常情况下所讲的变异是影响研究中的变异。但是,当进行平行研究时,两个毫不相关的对象在研究者的视野中相会了,双方的变异因子从交汇处产生了,这就是平行研究中的变异问题。平行研究中的变异,最根本之处是体现在双方的交汇中,是文明的异质性交汇导致了不同文明文学的变异。平行研究中的变异,最突出之处体现在话语变异上。对文学作品而言,“理论”就是一个“话语”,文学理论就是文学作品的话语。
西方的理论话语到了中国以后,产生了两方面的话语变异: 一方面,在知识谱系上,西方文论几乎整个地取代了中国文论。现当代的中国学术与文学研究几乎都是照搬西方的文学和理论,导致我们的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都是西方式的。另一方面,西方理论自身也产生了变异,即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另外一种话语变异是中国文学理论在与西方文论的碰撞中出现的“激活”问题。
也就是说话语在变异中被“激活”后,会产生新的东西,这是一个生产性的过程。这种“激活”是在西方文化与文论的启发下对中国传统价值的再发现,也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回归和承续。比较文学话语变异最典型的个案,就是中国学者提倡的“阐发法”。在整个当代中国,学者们都形成了一个基本思路,即用西方文学理论( 或是西方话语言说方式) 来解读中国文学作品,这使得中国文学作品与西方理论都产生了变异。
变异学研究正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新方法和新理论,弥补了法国学派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重大缺憾,开启了一个注重异质性和变异性的新阶段,最终打破了中国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困境。采用变异学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再也不用担心落入民族xuwuzhuyi或被指责“拉郎配”式的比附了。变异学既开拓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变异学实质上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比较文学试图抵抗西方强势文化的策略,与后民殖民主义理论思潮有关,尤其是与霍米·巴巴的文化杂交理论有内在的共通性。
文化杂交理论以解构主义的姿态,主张东方人对西方文化入侵的抵制和反抗。霍米·巴巴认为,殖民主义的权力并不是完全被殖民者所占有。[11]处于弱势地位的被殖民者可以利用种族、性别、文化和气候上的差异的力量扰乱殖民话语的权威性,以模仿、嘲笑等诡计来威胁权威,以混乱和分裂的杂交文本出现于殖民话语之中。通过提出这些跨文化的、混杂的要求时,本地人既挑战了话语的边界,又巧妙地通过设置与文化权威进行协商的其他特定的殖民空间而改变了其术语,最终解构了殖民话语的权威性。[12]文化杂交实际上是一种抵抗的策略。变异学采取的正是这种文化杂交策略,通过改写法国的影响研究,改写美国的平行研究,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摆脱长期处于西方中心主义的阴影,获得自己的合法性。这种改写和杂交,具体体现在: 先是默认来自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权威性,但是又以实证性的文学关系也同时包含变异的问题来动摇影响研究的稳定性,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与跨文明的异质性来动摇平行研究的稳定性; 在动摇了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稳定性之后,用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等变异学的术语来混合和改写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状态,进而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赢得一定的话语权。
结 语
中国比较文学的百余年发展史,从方法论上来看,经历了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 当然是以平行研究居多) ,最终到中国学派的变异学研究的变迁。影响研究是历史实证的研究,其哲学上的依据远可追溯到实证主义,近可依恃科学主义,操作层面上是考据之学。
平行研究是审美的研究,哲学上的依据是理一分殊,道的普遍性,近可引英美新批评为据,操作层面上是义理之学。变异学研究实质是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融合,其背后的学理基础是后殖民主义,操作层面上是考据与义理同行,严谨与想象并举。影响研究是法国的文学外贸主义,体现了法国人的自傲与欧洲中心主义。而平行研究是美国人为了与法国人、欧洲人抗衡———因为美国人历史不长,文学传统没有欧洲丰富悠久,在影响研究方面不占优势,不能体现美国人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真正实力,所以他们拈出不用考虑影响关系的平行研究来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但有意无意又落入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中心主义。中国人进行影响研究时,大多数是靠老祖宗的遗产来充面子,靠古典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来宣示文化的影响力。中国学者的平行研究也多是拿老祖宗的遗产来与西方文化类比,很少有拿现当代的作家作品与西方作家作品类比的。
新世纪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实力都大为增强,但文化软实力还远远不够,比较文学研究的话语权仍把持在西方学者手中。中国学者采用文化话语杂交的战略,以变异学研究解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权威,其深层的心理诉求是重塑民族自尊与自信,因此常常被人称为民族中心主义。总之,变异学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双重努力,是新世纪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突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赵毅衡.《管锥编》中的比较文学平行研究[J]. 读书,1981,( 2) .
[2]朱光潜. 诗论[M]. 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5.
[3]曹顺庆. 比较文学学科史[M]. 成都: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
[4]季羡林.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