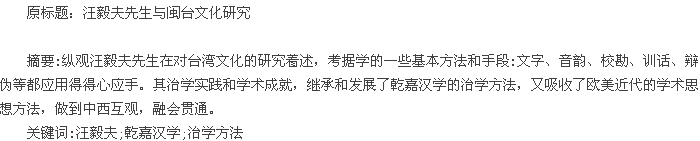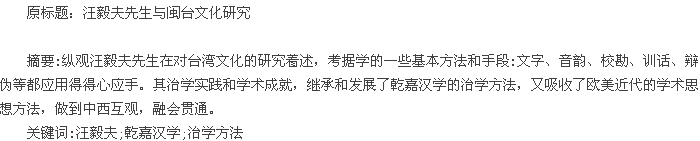
因为要转向研究台湾文化的缘故,暑假里我搜集了一些有关台湾文化方面的论文、着作。我发现汪毅夫先生在闽台文化的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并且造诣很深,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不仅反映在他的治学内容上,还反映在他的治学方法上。汪毅夫先生对台湾文化情有独钟,先后出版有:《台湾近代文学丛稿》(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台湾文学史·近代文学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台湾社会与文化》(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文化与闽台社会》(海峡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台湾近代诗人在福建》(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1998年版)、《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闽台区域社会研究》(鹭江出版社2004年版)等专着。这与其家学渊源有一定关系。汪毅夫先生 1950年出生于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台湾名门望族,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第一人、台湾进士汪春源的四世孙。十九世纪末,晚清政府腐败,国势日渐衰落,1895年4月17日清廷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孔4月28日在京参加举人会试的台湾举人汪春源、罗秀蕙、黄宗鼎(此三人中,只有汪春源后来成为进士)挺身而出,到督察院上书,表示“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的决心。5月2日汪春源等人又参加了由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再次“垂涕而请命”,要求清廷“拒和、变法、迁都。”表现出知识分子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现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福建省台盟主委的汪毅夫先生曾说:“这段历史在我心中留下极深印迹。在我的生活中、工作中和研究中,思乡怀土之情贯穿始终,我的许多研究凝结了我对先人,对故土的悠悠思念之情”。
一
在这样一个传统的书香门第中,汪毅夫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不仅使他在国学方面根抵深厚,对其思想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虚怀若谷的学风洋溢在他学术文章的字里行间。他在《中国文化与闽台社会》一书中的后记中写道:“作为政协委员,我还以‘学者的认真’自勉。先师俞元桂教授生前以‘学者的社会责任’相训迪,也令我不敢稍忘也。”他的学术研究贯穿着一个主题,即为推进祖国统一服务。正如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刘登翰教授所言:“在台湾文学的研究中,有一个领域、有一个角度是属于汪毅夫的。或者说在台湾文学研究者中,恐怕没有谁比汪毅夫更适合以这种角度来进行这个领域的研究了。’
汪毅夫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师从于俞元桂教授,考证鲁迅的生平事迹。俞元桂教授的治学严谨踏实、一丝不苟,直接影响着汪毅夫的学术个性。因此,他强调认真读书,重视实证,力戒空谈,主张无一事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花力气,下功夫,长年累月地搜集资料,再将搜集的材料排比归纳,核其始末,究其异同,每一结论,必有论据,据必可信,反对盲目蹈袭前人旧说。这样使得汪毅夫的论着往往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熟知汪毅夫的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博导汪征鲁教授曾说:“毅夫兄在学问上深受乾嘉考据学派的影响,每每以材料见长,以考据取胜学习确实如此。汪毅夫的《魏建功等“语文学术专家”与光复初期台湾的国语运动》一文计一万八千多字,引文注释达71处;《明清乡约制度与闽台乡土社会》一文计一万三千多字,引文注释有59处;《语言的转换与文学的进程》一文近万字,引文注释有48处;《北京大学学人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兼谈鲁迅在厦门的若干史实》一文一万一千多字,引文注释也达46处。其所征引的,有正史、地方史,还有野史、档案资料、诗文集、笔记小说、碑刻、庙宇签诗、口碑史料、田野调查报告等,其治学范围广及文学与文学史、史学与史学史、政治学与制度史、教育学、学术史等,在人文学科中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近年,急功近利的思想使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了浮躁、媚俗的现象。特别是对台湾文化的研究,海峡两岸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宏观研究,在台湾学界被认为是空泛的。有的大陆学者向台湾的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被评讲人认为过于空洞,根本无法算是一篇学术论文。而汪毅夫的研究成果资料多、注释详尽,又有鲜明的观点和精辟的论证。其治学实践和学术成就,既继承和发展了乾嘉汉学的治学方法,又吸收了欧美近代的学术思想方法,做到中西互观,融会贯通。诚如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导孙绍振教授所说:“我读毅夫的文章,往往有大开眼界之感,除了他论述时有警策之处外,主要就是他的材料都是第一手的,原汁原味,好象上帝才创造出来,还冒着热气似的,其充分和丰富常常令我仔细揣摩。
二
纵观汪毅夫先生在对台湾文化的研究着述,可以看到考据学的一些基本方法和手段:文字、音韵、校勘、训沽、辩伪等都应用自如。《语言的转换与文学的进程—关于台湾文学的一种解说》(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4年第一期)从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来考量台湾现代文学的分野、台湾现代文学史的分期、台湾现代文学作品的分类,以及台湾现代作家创、译用语问题的分析,经过大量的考据,提出令人信服的台湾现代文学史的三个阶段,其间作品略可分为文言作品、国语(白话)作品和日语作品。与此相应,台湾现代作家的创造用语可以称为创、译用语,他涉及文言、国语(白话)、日语和方言。《闽南民间文献考释举隅》介绍了作者近年收集的闽南地区的齿录(同榜举人或同榜进士各具姓名、生年、籍贯、三代等情况的履历汇编)、寿言、哀启、自传、书信和家训等各类民间文献,并就其涉及的文化、历史和闽台关系诸方面的问题加以考释。《闽南碑刻札记》从实物和出版物抄录部分闽南碑刻并加以考释,从而发掘出该部分碑刻在民间信仰、宗法制度、地方外事、社会问题、华侨历史等方面的史料价值。《<漳郡会馆录>发微》就《漳郡会馆录》一书涉及的版本、人物、职官、科举以及闽台会馆文化等方面的问题,逐一考证索隐,从中发掘史料,再现清代历史社会的若干情况。《地域历史人群研究:台湾进士》,就台湾进士这一地域历史人群的总数、名录、佳话、义举、轶事等钩沉索隐、取证考据,并就清代科举制度和科举文化进行介绍和评估。他认为:台湾进士是一个于今不在、于今不再的人群,宜以“地域历史人群视之,台湾幕友、台湾班兵、台湾熟师、台湾教谕等亦各是一地域历史人群。”《闽台文化史札记》较为集中体现了汪毅夫的学术个性。该文结合作者在研究工作中的得失来谈论闽台文化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古人生平的考定与名字的辨异、工具书的使用和史料的收集、实地取证与推理校勘,并由此说明了闽台文化史上的若干问题:刘家谋、黄宗鼎、施士洁的生年,丘逢甲、许淡的名、字、号,杨浚的籍贯等等。
三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乾嘉考据学的学风特色从十个方面进行概括,正与汪毅夫的学风哈恰相合。
其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陈孔立先生在评论汪毅夫的《中国文化与闽台社会》一书时曾指出:“作者以广泛搜集资料见长,言必有据,几乎每篇论文都发掘、应用了新资料。他特别善于从文学作品中发掘出可以说明历史、文化、社会方面的资料,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此外还广泛应用家乘族谱、碑刻、方志、档案、律令、俗谚理语,乃致庙宇和古膺的沿革简介等等都在搜罗之列。研究的课题有的是相当细小、冷僻的,研究的功夫却是十分精细的,见微知着,得出的结论则是很有意义的。孙绍振教授也说:‘他的治学精神并不完全是老学究、老夫子式的。”“他不仅长于占有资料,而且理论的阐发也有相当精致之处。’如对闽台乡约制度的考证,就旁征博引,罗列排比,去伪存真,由此及彼,从而厘清了迷误。
其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论。”汪毅夫的《<畅所欲言>与 18971928年间泉州的市井文化》就施舟人教授的藏本及其他藏本,龙彼得教授提及的版本、文体、作者和俗语诸问题,索隐发微,考据取证。此文通过内容和字迹上的比对,可以看出施藏本与汪毅夫自己在闽南某地访得的藏本一样,都是属于应用石印技术、摄底本之字迹而成的翻印本,属于名为“改良”,实则是不改不良的盗印本,并由此而推出《畅所欲言》开始写作的年代应为 1897年。
其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汪毅夫的《林树梅作品里的闽台地方史料》一文中应用得炉火纯青。此文对林树梅的生卒年重新进行了考证,汪毅夫曾在《林树梅作品札记》中考证其生卒年为“1808一1851”,此说已被闽台两地学界采用。但由于过去对林树梅生卒年的考证举证不足,不合“孤证不为定说”规则,所以在《林树梅作品里的闽台地方史料》一文中,重新加以检讨。他先从林树梅《先姚陈淑人行述》中考知其生年为1808年,又从林树梅《亡弟扩志》中得佐证。先从《金门县志》引“旧志”证明林树梅的卒年当在 185。年以后,又从刘家谋《观海集》有《为啸删诗毕未寄去讣音至矣》之诗,作年为1851年。据此推知,林树梅的卒年为 1851年。又如在《闽台文化史札记》一中对黄宗鼎的生年考证,先引黄宗鼎的科举齿录,又在黄氏后人处得见黄宗鼎的亲笔题画为佐证,考其生年为 1864年,同时也印证了“应试时少填一岁在旧时是一项俗例”的说法,有了佐证,才出此断言,严格遵守了“孤证不为定说”的规则。
其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得。”汪毅夫在《闽台文化史札记》一文中,对自己研究中出现的错、漏、误决不隐匿、躲避,而是坦然地加以更正。如在《清代台湾教育科举若干史实考》一文中,错引了《词林辑略》(朱汝珍辑)中误将福州侯官名人陈梦雷作为泉州同安人陈梦球的胞兄。在((福建科举人物丛谈(三题)》一文中指出自己所引《清代馆选分韵汇编》(严愚功编)在列举“父子翰林”时漏列“福州闽县陈海梅、陈培馄父子”一例。在写作《台湾文学史·近代文学编》时参阅获奖的某词典中关于“刘家谋”的词条,从中误接受了“台湾府学教谕”的常识性错误,应更正为“台湾府学训导”。此三次错、漏、误本来不属于汪毅夫的失误,是因为工具书的疏漏,但汪毅夫自己却认为是自己读书不审,心中感愧。汪毅夫先生的治学严谨,由此可见一斑。
其五“最喜罗列事项的同类证,为比较研究,而求得其公则。”汪毅夫的《清代台湾的幕友》,从《清实录》和部分清人着作、民间文件举出清代台湾从二品大员到九品小官,从巡抚、道员、知府、同知、知县、县承、千总到把总各级官员延请幕友的事例,说明清代台湾各级官员普遍辟置幕府、延请幕友的情况,以及清代台湾幕友在台湾公共事务和文学活动方面的表现,从幕府制度的角度证明闽、台两地历史社会在制度文明上的共同性。
在比较研究中,汪毅夫还大胆地应用新掌握的知识、自己的观点推出合理的假设、推断,即所谓的“理较”之法。如在《闽台文化史札记》中对金门历史文化名人许淡的名字,到底是“淡”还是“炎”,进行大胆假设。在《金门志》(1882)、((金门县志》(1992)等书中均记为“许炎”,而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上海古籍出版,1992年版)及记载翰林姓名、籍贯、科年、甲第等情况的专书《词林辑略》(朱汝珍辑)则记为“许淡”。炎、淡,音义皆不同,孰是孰非?作者根据古人有名有字,或又有号,名、字、号一般应有意义上的关联,由此着手进行考辨。
《金门志》记:“许炎,字保生,号瑶州”,《词林辑略》(朱汝珍辑)则记为“许淡,字保生,号瑶州”。淡、瑶均为美玉。作者以渊博的学识和大胆的推测,认为古书《礼记·玉藻》谓“古之君主必佩玉。”又谓: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佩玉除装饰的功用外,还被认为有护身的作用,以此视之,淡、保生、瑶州即名、字、号之间有意义上的联系。“理较”之法,是古籍校勘方法之一,陈垣先生在《校法四例》中云:“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由于理较法“最为高妙”,且带有一定的冒险性,不如其它校法稳妥,故前人虽也运用理校之法,但总不如用别法为多。汪毅夫先生在研究论着中,运用理校之法时,不仅据文理校,还据义理校。他在同一篇论着中,对台湾文化名人丘逢甲的名字有自己的新解。丘逢甲生于甲子之年(清同治三年甲子, 1864年),从字面上看,生逢甲子之年故名“逢甲是顺理成章的”,于是有“公初讳逢甲,以逢甲子年生也”(丘琼:《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之说。其实此说尚可斟酌。丘逢甲的长兄名先甲,先甲以及逢甲弟辈源甲、树甲、瑞甲、兆甲、崇甲、同甲、世甲也名用“甲”字。
在汪毅夫看来,“逢甲”之名与其生年有关的似不在“甲”字而在“逢”字。他还进一步推判出:按照太岁记年之法,丘逢甲的生年甲子为“阔逢困敦之年”,“逢甲”之名以及逢甲后来改用的字“仲阔”均与“阔逢困敦之年”有关。
其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在关于自己的曾祖父汪春源的刹晰问题,原在1998年由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的《台湾近代诗人在福建》中曾记:“曾祖父在同辈兄弟中排行第六。”但在后来台湾学界友人在台南吴氏家族旧藏的图书资料里发现汪春源的书信8封,并用电脑扫描复印后邮寄给汪毅夫。汪毅夫从信件中考证出汪春源在兄弟里的排行应为第九。他在《闽南民间文献考释举隅》一文中,一一明引。
其七“所见不合,则相辩洁,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J件。”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文风。这一点在汪毅夫的着作中也表现得很充分。如在《隔世之念与隔岸之想—<文艺春秋>、范泉、欧坦生及其他》(《世界文学论坛》2001年第四期)提及自己的着作《台湾近代诗人在福建》出版后,台湾静宜大学副教授黄美娥博士在((东海大学文学院学报》第41期上撰文,指出书中的若干错误。汪毅夫欣欣然地接受,并说:“诚哉是言也!在本世纪的曙光里,愿两岸的交流和合作深人至于亲密无间的境地。”汪毅夫还在《北京大学学人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兼谈鲁迅在厦门的若干史实》中对历来受人推崇的鲁迅先生有关顾领刚的看法,提出疑问,认为鲁迅先生看问题也有偏颇。如‘,((现代评论》派色彩将弥漫厦大”就是一个错觉;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几个史实》(载《鲁迅研究月刊》 2003年第12期)中关于陈万里的摄影作品的评价也是公允的,不因鲁迅的反感而厌恶。鲁迅因陈万里是顾领刚推荐到厦门大学工作的,所以对陈万里有看法。1926年10月10日,陈万里的摄影作品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陈列室展出,而陈列室里在10月4日起先有“碑褐拓片”(包括鲁迅收藏的)一类展品展出。鲁迅认为陈万里的摄影作品加人后显得不伦不类。汪毅夫公正地说:如果从摄影角度看,是很好的作品。
其八“辩洁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的意见,有盛气凌人,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谈台湾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注释中,作者写到:“癸未之秋、开学伊始,我同研究生张宁、游小波、李诊林诸君商定,他们各以‘台湾古代文学史’、‘台湾近代文学史’、和‘台湾现代文学史’作为博士论文学位的选题,我则担负指导之责。”身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福建省台盟主委、福建师范大学博导的汪毅夫教授对后学弟子皆待之以诚,蔼然有古人之风。他在论着中,诚实、坦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有不明之处,坦然地请教于人。在((漳州会馆录发微》中考证陈登元的史料时,有文人进士陈登元、有武人贵州安笼镇标守备陈登元,都是漳浦人氏。作者弄不清在《漳州会馆录》卷末所收《捐金重修西馆记》文中“陈登元,漳浦人,捐洋银捌员”的记载到底是文人陈登元,抑或是武人陈登元。知者奉告。《(畅所欲言)与 1897一1928年间泉州的市井文化》一文中,对属国际汉学界顶级人物龙彼得 (Pietvanderloon)教授对《畅所欲言》的补充说明有疑问,但仍尊称龙彼得是治学严谨的,并不因他的补充说明漏了说明此书还收有五言、压韵的内容而讥笑他。
此外,“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与“文体贵朴素简洁,最忌‘言有枝叶”’也很符合汪毅夫的文风。钟情于台湾文学史研究的汪毅夫先生从1987年初涉此领域,至今有近20个年头。他兢兢业业,孜孜以求,勤奋地在这一领域耕耘着。他一再诚恳而虚心地表示“吾愿以治学之得失,报告于同道诸君。”(汪毅夫《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谈台湾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他坦荡地以自己治学之得失奉告同行“文学的外部制度同文学的关系乃是中文(国文)院(所)出身的学者如我辈宜多加注意的关节。”“在‘台湾幕府与台湾文学’的课题之下,宜深人进行个案研究和综合研究,相关的文学史实亦当在台湾史着里论述及之。”
汪毅夫对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同台湾文学史研究的关系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他听台湾学者李亦园教授说,这种研究方法有从周边看文学的倾向,很像台湾学者王裕兴教授“周边文化关系”的理论。汪毅夫不掠人之美,他虚怀若谷,坦陈自己从王裕兴教授“周边文化关系”的论点受到启发。
四
梁启超在归纳乾嘉考据学的学风特色后,对乾嘉学派的学术活动所产生的文化效应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其直接效果有三:一是吾辈先向觉难读难解之古书,自此可以读可以解。二是许多伪书及书中窜乱芜秽者,吾辈可以知所别择,不复虚糜精力。三是有久坠之哲学,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学,自此皆卓然成一专门学科,使吾辈学问之内容,日益丰富。其间接效果有二:“一是见其‘为学问而学问’,治一业终身以之,蛛积寸累,先难后获,无形中受一种人格观感,使吾辈奋兴向学。二是用此种研究法治学,能使吾辈心细,读书得间,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使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十三)梁启超先生的这些真知灼见和我阅读汪毅夫先生的论着所感受到的十分相似,大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
参考文献:
【1】方友德、丁晓峰:《愿为祖国统一大业竭尽绵力—福建省副省长、台胞汪毅夫访谈录》,载《台声杂志》, 1998年5月。
【2】转引自黄新宪:《汪毅夫与台湾文化研究》,载《教育评论》, 1997年第3期。
【3】汪征鲁:《独具慧眼,厚积薄发—江毅夫(闽台区域社会研究>读后》,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盛年第1期。
【4】转引自刘大可:《汪毅夫与闽台文化研究》,载《东南学术》,1999年第i期。
【5】陈孔立:《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序”》,转引自邓孔昭《闽台历史文化研究的一本好书—评汪毅夫的<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载《台湾研究集刊》, 2001第2期。
【6】管宁:《汪毅夫:台湾文化研究的辛勤耕耘者》,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