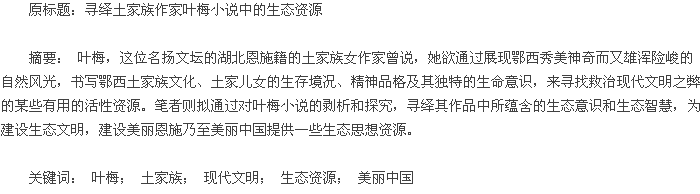
叶梅,这位湖北恩施籍的土家族女作家,以执着自信地展现鄂西秀美神奇而又雄浑险峻的自然风光和书写鄂西土家族儿女的生存境况、精神品格及其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人生命运的作品名扬文坛。研究者则称其作品为“土家族文化小说”[1],极力挖掘其作品中所蕴涵的土家族优秀的民族文化品格和女性意识。而笔者由于一直关注或者说研究的是生态文学,因此在阅读叶梅小说的时候,着眼点则是叶梅小说中的生态书写和潜隐其中的生态意识,期望从中发掘和寻绎出有益于救治现代人精神生态失衡的活性资源,发掘和寻绎出有益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恩施乃至美丽中国的思想资源。
一
叶梅从小生长在鄂西,成年后她又在鄂西生活和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鄂西是她成长的摇篮,鄂西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是她心灵的伙伴。自然,鄂西的自然山水也就早已化作血液流淌在她身体里,成了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成了她的生命之魂、艺术之魄。因此,不论是身在恩施的初期练笔,还是身在武汉、京华的中后期创作,鄂西神奇美丽、雄浑粗野的自然山水都是她创作灵感的活水源头,是她一直书写的对象。正如张守仁评价其小说时说的那样: “那山、那水,一根竹管,一朵山花,一泓泉水,都化作了一种情绪。”[2]
这种情绪几乎弥漫在她所有的作品中。在《撒忧的龙船河》中,龙船河在她笔下是蜿蜒狂躁、变幻莫测的,但同时又雄浑壮美、充溢着原始的野性和生命活力: “那河看是纤细实际奇险刁钻,河上礁石如水怪獠牙狰狞参差不齐,水流变幻莫测,时而深沉回旋织出串串漩涡,时而奔腾狂躁如一束束雪青的箭簇。”龙船河两岸的青山则相对而出,“间或有血红点点,三两猴儿于茂林中嬉戏”1,一派生机。在《青云衣》中,鄂西境内的三峡黄昏则充满了诗情画意,一片盎然生机: “残红晚霞,一江碧水泛散粼粼金光,倦鸟泼剌剌归林,峡谷峭壁深沉了颜色,如墨如黛。”[3]202鄂西恩施的自然生态在叶梅笔下是如此神奇美妙,如此令人向往。难怪叶梅自己也禁不住发出这样的感叹: “她( 鄂西恩施) 所具有的灵秀与纯真显然别具一格,足以与世界上最优美的风景相媲美。
中国恩施,无疑会是人类后工业时代最迷恋的去处之一。”因为我们“透过目不暇接的绚烂宝藏和多姿风情,可以穿越时空去触摸大自然的深处和我们民族的祖先,从而清醒当代人类应站立的位置”,而“恩施人正是从这里出发,去努力寻求人与自然,人与 社 会,人 与 人 之 间 及 人 的 内 心 的 最 大 和谐”[4]169-170.的确,在当今这个科学技术已然成为全球惟一宗教的后工业时代,全球生态危机、生态灾难频频发生,人类有点无处躲藏的时代,像鄂西恩施这样还拥有美好自然生态环境的区域确实是令人向往和迷恋的地方。难怪鄂西恩施不仅被誉为“国家三大后花园( 大兴安岭、西双版纳、鄂西恩施) 之一”,而且还被联合国评为“全球最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然而,随着现代化步伐的无往不至,鄂西恩施也不可能真正与世隔绝,成为生态独立王国。就像叶梅在《青云衣》中书写的那样,随着三峡大坝的建设,像向怀田老人居所那样美丽的地方将全部消失。
在其散文《有条河的名字叫龙船河》中,叶梅则以怅惘、伤感、忧思的笔调这样写道: “由于三峡工程的进行,大坝蓄水的时候,回水将进入这条小溪,旅游中引以为特色的乘坐‘碗豆角’漂流将不可能在下游进行,而沿途的峡谷景点也会相应消失或者变矮,悬棺、栈道,将会没入水底,觅食的猴子也将会搬到更高的山上……”[4]19这就是说,鄂西神奇美丽的自然生态其实也在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在加速度变化着,而这种变化,引起了作家叶梅深沉地忧思和焦虑。
如何让鄂西恩施真正成为我们未来的“后花园”和“全球最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到的也许就是在发展地方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应该首先考虑的是 GDP 和政绩,而是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和谐。就像***指出的,“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因为自然生态环境一旦破坏到不可扭转的地步,不论我们最终在经济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我们都是失败者。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适宜于居住家园,更不用说实现诗意的栖居了。毕竟我们人类不可能真的去火星或其他星球上生活的。
二
土家族人长期生活于巫山山脉和武陵山脉交汇之处的恩施,曾经实行了 400 多年的土司制度,直至清雍正十三年才改土归流,实行流官制,才逐渐与外界有了沟通和交流。而在此之前,他们一直生存在山高沟深的大山里,独立于世,几乎不与外界相往来。在这样的生存环境和生命状态下,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领悟到了人与自然、人与神灵的某种神秘关系,同时也就学会了如何与天地交流、与鬼神对话。因此在神灵信仰上,他们信奉多神教,相信万物有灵,平常重巫敬鬼。这种对生活和天地万物的理解,深蕴着浓郁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为土家族作家,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就像民族的生命基因一样潜藏在叶梅灵魂深处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在她构筑其鄂西世界的时候,这一思想便自觉不自觉地流注在她对土家族人的民俗和生活的叙述中。
在《花树花树》中,我们看到,在龙船寨,凡遇妇女生育,则必请巫师覃老二上天去请“七仙女”.在请“七仙女”的时候,原本“核桃壳”似的覃老二就会瞬间幻化成“婀娜多姿”的七仙女,在云蒸霞蔚的“拗花山”上找寻和将要出生的孩子对应的“花树”,从而预测孩子未来的吉凶祸福。因为人们相信,天上有一座灵魂聚居的拗花山,山中的千万种花儿和地上的千万个人儿的命运息息相关。一花一生命,一花一命运,谁也躲不掉。只有“七仙女”才能找到代表人们命相的花树。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是巫术或者可能还有人说这是迷信,但这种巫术或者迷信背后隐含的则是土家族人对生命和自然的理解和敬畏,是他们“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种体现。正如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说的那样: “对巫术的信仰乃是深深地植根于生命一体化的信念之中的。”
在《青云衣》中,叶梅则写出了土家人信仰山鬼的情感。向怀田眼看着父母和一明两暗的三间瓦房及门前的橘树和屋后的翠竹瞬间消失在江水中,只留下一阵阵呛鼻的土腥味儿。当向怀田为失去父母而悲痛欲绝时,周围的邻人却认为这“土腥味儿”是“山鬼的气息”.因为他们始终相信,山鬼是藏在大山深处的任何一个角落的,他一般不发作,可当他要发作的时候,任谁也无法预测,更不用说能够制止他的发作了,因此要对其安然处之,不能有丝毫的不满和怨恨。因为“山是不能没有山鬼的。山鬼是山的魂魄”.这就是说,在峡江人看来,峡江自古以来的滑坡就是山鬼在作怪,可山鬼是山的魂魄,山不能没有山鬼。因此面对滑坡,他们在悲伤无奈之余,又能坦然面对,对山鬼始终存有敬畏之心,就像人们劝慰向怀田时说的那样: “天作孽,人有什么办法?”
这种无奈而又坦然面对自然灾难的生活态度,深受现代文明教育的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土家人的迷信与愚昧。但在我看来,这种生活态度其实隐含了土家族人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情怀?
在《最后的土司》中,叶梅一开篇就写到了土家族的舍巴日。土家舍巴日,在每年的春分时节。这一天,土家人要祭祀上天祖先,祈求粮食和平安。就像叶梅小说中写的这样,龙船河的人舀取最清洁干净的泉水,用最好的松杉和柏木,给上天神灵和祖先预备上三牲供品,由沐浴洁净过的童男和童女供奉到他们的牌位前,对其不敢有丝毫的脏污。之后人们便开始跳祭祀舞蹈---茅古斯和摆手舞。舍巴日的祭祀体现的是土家人对祖先和神灵的崇拜,通过祭祀活动与祖先和上天对话,祈求祖先和神灵护佑族人,降福于族人。而带有明显巫术性质的舞蹈则将土家人崇拜生殖、热爱生命、敬畏天地自然的情感和天人合一的思想展现得淋漓尽致。因为“在这样的庆祝活动中的、跳着巫术舞蹈的人们,是彼此溶为一体并且与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溶为一体的。他们不是孤立的; 他们的欢乐是被整个自然感觉到并且被他们的祖先分享的。空间与时间突然消失了; 过去变为现在,人类的黄金时代回来了”.
然而,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科学家们早已证明天地间是不存在任何神灵的。既然天地间无任何神灵的存在,人类也就根本不信仰万物有灵了,自然也就谈不上敬天畏地了,“天人合一”思想在他们眼里也成了不合时宜的远古神话,甚至被认为是愚昧落后的观念。于是人类便开始心安理得而又毫无畏惧地手执科技利器,傲慢地向大自然进军,大有一副将征服自然的革命进行到底的姿态和架势。可令人类万万想不到的是,当我们在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同时,我们却不得不承担大自然向我们讨还的连本带息的我们完全担负不起的生态债务。
最近几年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种越来越可怕的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简直就是血淋淋的明证,可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便有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可他们更坚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都是完全可以通过科学技术解决的,从而丝毫未停下伸向自然的罪恶之手。这也许就是人类的自高自大! 若从救治人类对待自然的骄傲自大的病态心理的角度来看,叶梅笔下的土家族人敬畏自然、敬畏天地、崇拜生命和祖先上天的“天人合一”的生命意识和人生姿态则显得格外有意义和有价值。
三
在我看来,叶梅作品中有关土家族人的生死观和爱情观中也深蕴着“天人合一”的生态内涵。在《撒忧的龙船河》中,覃老大活着的时候,爱说这两句粗话,“该死的卵朝天,不该死的万万年。”“要死卵朝天,不死好过年。”这两句话看似消极宿命而又粗俗鄙陋,但仔细一思索,就会发现,它其实表现了土家人坦然面对生死的达观态度。土家族人长期生活在自然环境虽优美雄奇但又险峻恶劣的鄂西高山密林中,生与死往往一线之隔,这自然就培养出了他们对待生死的从容态度,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不珍惜生命,相反,从前一节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他们热爱生命、敬畏生命,从不轻言放弃生命。可当生命真正完结之时,他们又显得泰然从容,尊重生命的自然规律,不哭不悲,以欢天喜地的跳丧的仪式高高兴兴地送死者上路。同样在《撒忧的龙船河》中,当年过六十的覃老大无病而寿终的时候,乡民们就是笑逐颜开气势非凡地为他送行的。对此,叶梅阐释道:“土家人对知天命而善终的亡灵从不用悲伤的眼泪,……只有热烈欢乐的歌舞才适于送行,尤其重要的是在亡人上路之前抚平他生前的伤痛,驱赶开几十年里的忧愁,让他焕然一新轻松无比地上路,这是一桩极大的乐事。”
生老病死,本就是自然规律,也是人生常识。有生有死,生命才能保持平衡与和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土家族人的生死观中确实包蕴着参透自然规律、遵循并尊重自然规律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和当今的生态思想无不契合之处,完全能给当代那些耽溺于不死神话的人以启发和警醒。
男女爱情的书写,在叶梅小说中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容,但最能反映土家儿女独特爱情思想的当属《撒忧的龙船河》中的巴茶对覃老大的爱情和覃老大对客家妹子张莲玉的爱情。巴茶在祖祖丧事上看中了癫狂跳丧的桡夫子覃老大,于是她既不要媒人,也不要聘礼,而是在“女儿会”上,将自己一针一线纳成的饱含着浓情厚爱的千层鞋底送给覃老大,之后便果断地锁了自己的三间小屋,背着背篓跋涉到龙船河,全心全意地和家无余财且性情粗野的覃老大一起生活,风里来雨里去,一生无怨无悔。这种只尊重自己感情而不在乎身外之物的爱情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最干净最纯粹最自然也最健康的爱情。相对于那些建立在各种欲利基础上的爱情,这种爱情可以称作绿色爱情或者生态爱情。
《山上有个洞》中的田昆和杏儿之间的爱情也是这种最自然最干净最纯粹的绿色爱情,与金钱、权势、地位均无关,为了爱情,即便跨越千山万崖也要相亲相爱,不离不弃。
覃老大在山洞中之所以和客家妹子张莲玉发生关系是因为自己喜欢客家妹子,当然他也认为客家妹子喜欢他。就像他后来面对张莲玉逼婚时说的那样: “我姓覃的不偷不抢光明正大,原以为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才做了这件事。”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只要相互喜欢,你情我愿,两情相悦,就可以成为相好,就可以发生性爱关系,中间不能掺杂任何功利和物质的色彩。这种情爱观就像沈从文先生曾说的那样,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其实这也不仅表现出了土家儿女间的爱情观,而且更表现出了人类最本真最自然的情爱状态,是一种和天地自然相和谐相一致的生命状态,也是最健康最自然最自在的生命状态。所以后来,当张莲玉出于现实利益而两次投怀送抱的时候,覃老大都拒绝了。特别是第一次,覃老大原本想着自己苦苦思念的人儿也在想念着自己,所以“想疯狂地揉碎那女子”,可当他发觉女人已对他没有任何情分的时候,身上蠢蠢的胀动便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就像他自言自语的那样: “你覃老大是人,不是发情的野猪。”由此可见,在山洞中,他和张莲玉发生关系与情欲并没有多大关系。
在当今这个情欲泛滥、爱情可以买卖、爱情总是和各种利欲联系在一起的时代,叶梅笔下巴茶和覃老大的这种人类最原初也最本真的绿色爱情,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它可以提醒我们这些完全被物欲吞噬掉本真心性的今人,人类曾经这样美好的生活过。在情爱生活中,他们活的自然、自由、健康和快乐; 它也可以给当代那些游戏爱情不知真爱为何物的青年男女以精神启示,引导他们思考什么样的爱情才是人类最应该拥有和享受的。
通过以上的寻绎和探究,可以说,叶梅之所以构建她的鄂西世界,最大可能是因为她有感于现代文明之弊对当下中国优秀文化的侵损而为之的。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叶梅才给我们构筑了一个无比淳朴、神秘、美丽、自在、神话般的鄂西世界,以此来抗衡现代文明之弊,拯救现代人业已远离自然的灵魂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生态的失衡。因为在她的鄂西世界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己内心都是那么的和谐与自在。
参考文献:
[1] 吴道毅。叶梅和她的土家族文化小说[N].文学报,2003-05-29.
[2] 张守仁。鄂西无处不是情---关于叶梅的小说[M]/ /最后的土司。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247.
[3] 叶梅。妹娃要过河[M].北京: 作家出版社,2009.
[4] 叶梅。我的西兰卡普[M].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5] ( 德)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6]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M]/ /沈从文选集( 第 5 卷)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