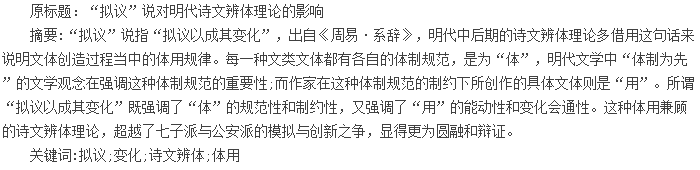
“拟议以成其变化”是《周易·系辞》里的一句话,这句话对明代诗学影响至深,可以说是贯穿明代诗学的一条主线。前后七子以它为理论纲领,在流派内部展开了有关是侧重“拟议”还是侧重“变化”的论争;而公安派则站在七子派的对立面,反对这个命题。到了后期诗文辨体理论家徐师曾、赵梦麟、顾尔行等人那里,他们又纷纷用这句话来阐释自己的文体学观念。关于“拟议以成其变化”与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理论的关系,学界同仁已经有所论述,而对于“拟议以成其变化”所包含的文体学内涵,学界尚无专门研究文章,本文即着眼于此,主要论述“拟议”、“变化”与明代后期辨体理论的关系,进而揭示其背后所隐藏的文体学观念。
一、“拟议”说的提出
“拟议以成其变化”作为一个易学命题,被借用到文学领域中来,在明代由前后七子首先发端,他们主要是用这句话来说明文学创作模拟与创新的关系。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首次提出这一命题,他针对李梦阳的“刻意古范,铸形塑模,而独守尺寸”提出批判,认为作诗应该“领会”古人之“神情”,而不是模仿其形迹。所谓:体物杂撰,言辞各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其善焉已尔。故曹、刘、阮、陆,下及李、杜,异曲同工,各擅其时,并称能言。何也?辞有高下,皆能拟议以成其变化也。
以为曹植、刘桢、阮籍、陆机、李白、杜甫之所以能各擅其时,皆因为其能“拟议以成其变化”。李梦阳则在《驳何氏论文书》中反驳曰:“规矩者,法也。仆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规矩者,方圆之自也,即欲舍之,乌乎舍?……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质顺势,融熔而不自知。”
他认为作诗应该守其规矩,不舍其法,久而久之,自能融会贯通而出新。二人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偏重拟议还是偏重创新:李偏重摹仿,即模仿古人以求创造;但要求虽有变化,却不得背弃古法,主张“法常由不求异”。而何偏重创造,也是模仿古人以求创造;但要求虽有拟议,却不得拘守古法,主张要“千载独步”。
后来李攀龙将这一命题上升为复古派的理论纲领,他在《拟古乐府序》中说:“《易》曰:‘拟议以成其变化’,‘日新之谓盛德’。不可与言诗乎哉!”
并且举了两个例子说明模拟方式之不同:一则为“胡宽营新丰”,使犬羊鸡鸭各识其家,这是能得其原貌的善拟者;一则是“伯乐论天下之马”,得精忘粗,得内忘外,这是“有以当其无有拟之用”者,是识透了天机不着痕迹的善拟者。他还在《古诗后十九首并引》中说:“辔策出大御,绳墨出巧工。”
可见,李攀龙是非常看重拟议一端的。王世贞《李于麟先生传》以“不以规矩,不能方圆;拟议成变,日新富有”来概括李梦阳的文学主张,同时更加强调变化的重要性:“于鳞居恒谓‘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拟议以成其变化’为文章之极则。余则以‘日新’之与‘变化’,皆所以融其‘富有’‘拟议’者也。”
围绕着拟议和变化,七子派内部展开了论争,有人侧重于模拟,如李梦阳和李攀龙;有人侧重于变化,如何景明和王世贞;也有人一直在试图调和二者,如徐祯卿和谢榛。这些论争一直持续着,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到了明代中后期,辨体理论家则用这句话来阐释文体创作过程当中的体用规律。如万历年间的赵梦麟《文体明辨序》说:“《易》不云乎:‘拟议以成其变化。’变化者用也。所以为之拟议者体也,体植则用神,体之时义大矣哉,而胡可以弗辨也!”
顾尔行《刻文体明辨序》亦云:“文有体,亦有用。体欲其辨,师心而匠意,则逸辔之御也。用欲其神,拘挛而执泥,则胶柱之瑟也。《易》曰:‘拟议以成其变化’。得其变化,则神而明之,会而通之,体不诡用,而用不离体。”
这两段话分别出自赵梦麟和顾尔行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一书所作的序言。他们不约而同地引用《周易·系辞》当中的“拟议以成其变化”一句来说明文体的创造过程,毫无疑问是受到了明代中期前后七子的影响。文学创造的模拟与创新跟文体创造的模拟与创新有相似之处,前后七子可以用这句话来说明问题,赵梦麟和顾尔行自然也可以;但是他们并不偏于模拟或者创新,而是另辟蹊径,从“体用”的角度来具体阐释“拟议以成其变化”所具有的文体学内涵。
二、“拟议”说与明代诗文辨体中的“体用”论
明代文体学家所论文体,实际上是三个层次的文体。第一层,文章自身存在一个先验的文章本体,即文章的共同之“体”,这是所有文体的基本范型;第二层,各种更相迭换的文类文体(如诗、赋、词、曲等等)其实也各自拥有其体制规范,这是文类文体;第三层面,不同诗人、流派等所造就的直观的具体的个别文体。相应而言,他们所涉及的体用关系也就在这三个层次之间展开,而着重于文类文体与个别文体之间的体用关系。
文类文体指的是拥有自身体制规范的体裁,而在体制规范下所创造的具体的个别文体则是文类文体的表现。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在论述《文心雕龙·体性》篇时曾云:“‘体’这个概念强调固有的标准或规范,它先于各种特殊表现,它携带一种参与到特殊表现之中的力量,你可以在特殊表现中把它认出来,但它本身不是那个表现的特殊所在。”
这里虽然没有明言“体用”,但却蕴含了“一与多”、“一般规范与特殊表现”的体用思想。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篇云:“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所谓“文之体有常”,即可理解为某一种文类文体的规范性和统一性,而“变文之数无方”,则可理解为在文类文体规范下创造出来的个别文体的多样性和变异性。
一方面文类文体以具体文体为存在的方式,人们只能通过具体文体来认识某种文类文体;另一方面人们创作和批评具体文体又要以文类文体的体制规范为根据,如明代李东阳所说:“古诗与律不同体,必各用其体乃为合格。”这就是文类文体与个别文体之间“体一用殊”与“体用不二”的关系。这种体用关系与上述第一种体用关系不同,主要是就创作领域来讲的。赵梦麟、顾尔行、谢廷授、许学夷等人均是从这个角度来谈的。
赵梦麟在《文体明辨序》中说:说者有以文之为用也,纵发横决,游矫腾踔,方其骋思而极巧也,固驰驭无方而神运莫测,何以体为哉?虽然,《易》不云乎:“拟议以成其变化。”变化者用也,所以为之拟议者体也。体植则用神,体之时义大矣哉,而胡可以弗辨也!
赵梦麟在这里引用“拟议以成其变化”一语来说明文体创作过程中的“体用”规律,明确指出“变化者用也,所以为之拟议者体也”,此处之“体”即是指作为一种规范的文类文体,而所谓“用”,则是指在体制规范下各种个别文体的变化。他认为这种变化具有“纵发横决,游矫腾踔”,“驰驭无方而神运莫测”的特点,也即是承认具体文体的创造在表现形式和表现对象上是灵活多变的;但另一方面他更强调体制规范的作用,所谓“体植则用神”,意为只有确立了文类文体的规范,具体文体的创造才能出神入化。
顾尔行在《刻文体明辨序》中进一步发挥赵梦麟的说法,他以为:文有体,亦有用。体欲其辨,师心而匠意,则逸辔之御也。用欲其神,拘挛而执泥,则胶柱之瑟也。易曰:“拟议以成其变化。”得其变化,将神而明之,会而通之,体不诡用,用不离体,作者之意在我,而先生是编为不孤矣。这段话以“体用”对举的方式指出“文有体,亦有用”这一观点,并且同样引用“拟议以成其变化”来说明这个道理。
所谓“体欲其辨”,是指创造具体文体之前要先辨明各种文类文体的基本特征和规范,这是个别文体创造的依据,如果不辨体制规范,过分“师心而匠意”,就会像御马脱了缰绳,无法控制。所谓“用欲其神”,则是指在创造具体文本时又不能拘泥陈规、胶柱鼓瑟,而应善于变化以至“出神入化”。
二者合起来既强调了“体”的规范性和制约性,又强调了“用”的能动性和变化会通性。“体欲其辨、用欲其神”体现了文体创造过程中“体一用殊”的一面;同时文类文体又要在具体文体的创造中才能实现,此所谓“体不诡用,用不离体”,体现了文体创造过程中“体用不二”的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赵梦麟和顾尔行两人所探讨的仅是就单个文体的生成规律来看的,这是先有文类文体的基本规范,而后才有根据这规范而创作出来的个别文体;但是从文体生成的整个历史来看,究竟是先有文类文体还是先有个别文体,却是一个难以解答的文体史难题。明人谢廷授在《续文章缘起序》中说:文有万变,有万体,变为常极,体为变极。变不极则体亦不工。工者,起之归而绝之会也。夫三才何日不常,任其所趋而变生,变以日异,任其所就而体成,体成而后工,工太甚则复拙,故工者,起之归而绝之会也。伏羲极古今三才之变而易以工,尧舜极天下人文之变而典谟以工,故书起于易者也,诗起于书者也,春秋起于诗者也。春秋体极而春秋绝,诗体极而诗绝,书体极而书绝,易体极而易绝。易难绝而如线之脉,犹寄于书诗之文,书读诗咏,理跃神传。玩易者有遐思焉,书诗绝而易绝。
易既绝而秦汉唐宋之文起,其体又万变矣。极其变而其体始备,体既备而其文始工。谢廷授在这里讨论的便是文类文体的历史生成问题。
他一方面认为文类文体体制规范的生成,从其萌芽到定型,是个别文体变化的结果,此所谓“极其变而其体始备”;另一方面又认为文类文体体制规范的建立是单个个别文体生成的根据,此所谓“体既备而其文始工”。但同时,他又强调“工太甚则复拙”,也就是说个别文体的创造变化达到极致又会产生新的文类文体,此所谓“工者,起之归而绝之会也”。这样,从文体生成的整个历史来看,文类文体与个别文体孰先孰后就是个无法解答的难题。
赵、顾二人关于文体创造过程当中的“体用”规律是在为徐师曾的辨体著作《文体明辨》作序时提出的。而《文体明辨》一书旨在辨析各种文类文体的体制规范及其源流正变。在明代,这种以“辨体”为主要目的的书有很多,如吴讷的《文章辨体》、贺复徵的《文章辨体汇选》、许学夷的《诗源辨体》、杨慎的《绝句辨体》、符观的《唐宋元明诗正体》等书均直接在书名中就透露了这一消息;还有一些虽未冠以辨体之名却行辨体之实的书,如王世贞的《艺苑卮言》、胡应麟的《诗薮》、胡震亨的《唐音癸签》等。
与此种现象相关联的是受宋人如倪思“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文矣”,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的影响,整个明代文坛流行着一种“体制为先”的文学观念。如李东阳的《麓堂诗话》曰“予辈留心体制”,陈洪谟曰:“文莫先于辨体,体正而后意以经之,气以贯之,辞以饰之。体者,文之干也;意者,文之帅也;气者,文之翼也;辞也,文之华也。”
吴讷一再强调“文辞以体制为先”。徐师曾指出:“夫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为堂必敞,为室心奥,为台必四方而高……夫固各有当也。苟舍制度法式,而率意为之,其不见笑于识者鲜矣,况文章乎?”又曰:“文章必先体裁,而后可论工拙。”胡应麟《诗薮》曰:“文章自有体裁,凡为某体,务须寻其本色,庶几当行。”许学夷曰:“诗文俱以体制为主。”
凡此种种,都是在强调文类文体的体制规范对于作家创作具体文本的重要性和决定性。这正是顾尔行所谓的“体欲其辨”。与“体欲其辨”相对而言的是“用欲其神”。顾尔行说:“用欲其神,拘挛而执泥,则胶柱之瑟也。易曰:‘拟议以成其变化。’得其变化,将神而明之,会而通之。”
这是指作家在创作具体文体时要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能拘泥于陈规,而应善于变化以入神。顾尔行将“变化”与“神而明之”联系起来说,许学夷则在《诗源辨体》自序中进一步指出“神而明之”的原因在于“存乎其人”:近袁氏、钟氏出,欲背古师心,诡诞相尚,于道为离。
予《辩体》之作也,实有所惩云。……魏六朝,体有未备,而境有未臻,于法宜广;自唐而后,体无弗备,而境无弗臻,于法宜守。……《易》曰:“拟议以成其变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夫体制、声调,诗之矩也;曰词与意,贵作者自运焉。窃词与意,斯谓之袭;法其体制,仿其声调,未可谓之袭也。今凡体制、声调类古者谓非真诗,将必俚语童言、纤思诡调而反为真耳。
许学夷此处意在抨击公安、竟陵派的一味求变。他认为“自唐而后,体无弗备,而境无弗臻,于法宜守”,因而当“法其体制,仿其声调”,“拟议以成其变化”。在许学夷眼中,拟议是体,而变化只是用,脱离了拟议的一味求变、“师心自用”是不可行的。但同时,他也强调“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强调“曰词与意,贵作者自运焉”,这就涉及到作家个人的创作才能了。陈洪谟所谓“体正而后意以经之,气以贯之,辞以饰之”所涉及的“意”“气”“辞”也都是主体的创造。按照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所说,影响文体形成的有四个因素,即“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每个人的“才、气、学、习”有所不同,所创造的具体文本也就会各不相同,而这些具体的个别文体正是某一文类文体的特殊表现(用)。
三、“拟议”与“神”
在涉及“拟议以成其变化”的命题时,顾尔行讲“用欲其神”,许学夷讲“神而明之”重点都在一个“神”字上。而“神”又是《周易》本身所特别强调的一个观念。《易·系辞》讲“变化”,是与“神”紧密联系起来的。如: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智。故神无方而易无体。(《系辞上》)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系辞上》)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系辞上》)《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系辞上》)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系辞上》《周易》用“神”这一概念来说明阴阳、天地变化的微妙性和不可预测性,这一概念既与鬼神观念有关,又与天地、阴阳变化本身的神秘性和规律性相连。《周易》认为变化具有“神”的特性,同时只有“天下之至神”,才能体察道“无思、无为”的《易》之本体。那么学《易》者对于《易》之本体的把握就要靠主体的能动性去“神而明之”了。孔颖达疏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言人能神此易道而显明之者,存在于其人:若其人圣,则能神而明之;若其人愚,则不能神而明之,故存于其人,不在易象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若能顺理足于内,默然而成就之,暗与理会,不须言而自信也。
‘存乎德行’者,若有德行,则得默而成就之,不言而信也;若无德行,则不能然。”意为易道弘深自存,需要用易解易之人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去神会之、显明之,而人是否有德行,又是能否“神而明之”的关键。学易之人的主体性在这里被强调突出了。其实,“拟议以成其变化”这个命题,本身就包含了“拟议”和“变化”这两个侧面的矛盾,如何处理这个矛盾,就要靠个人的“心神涵泳”。明清之际的张次仲《周易玩辞困学记》说:变化无端,拟议有迹,拟议之于变化,相去远矣。而曰“拟议以成其变化”,何也?吴因之曰:拟议不是迹象摹拟。心神涵泳,独会于意,言象数之表,时然后言,即是拟之后言;时然后动,即是议之后动。语默动静、随处咸宜,即是成变化。
这里张次仲明确指出“拟议”和“变化”之间的矛盾,认为拟议有迹,变化无端,二者相去甚远,接着他引晚明吴默的话,解决了这个问题,并特别强调“心神涵泳”也即是学易者个人对于易理的领受。明代来知德也说:“《易》之变化不在其《易》,而成于吾身矣。”联系到作诗为文,某一文类文体的体制规范是一定的,但是作诗为文之人的才、情却是不同的,人们尽可以在具体的创作中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去拟议而成变化,并最终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
与许学夷大致同时的“末五子”之一李维桢在论述诗文创作的模拟和创新时就说:“故为诗文取古人所已言而袭,非也;必欲得古人所未言而用之,亦非也。臭腐可为神奇,神奇亦可为腐朽,存乎其人何如耳。”他还在《太函集序》中具体论述了法与才的关系:文章之道,有才有法。无法何文?无才何法?法者,前人作之,后人述焉。犹射之彀率,工之规矩、准绳也。知巧则存乎才矣,拙工拙射,按法而无救于拙,非法之过,才不足也。将舍彀率、规矩、准绳而第以知巧从事乎,才如羿轮,与拙奚异?所贵乎才者,作于法之前,法必可述;述于法之后,法若始作;游于法之中,法不病我;轶于法之外,我不病法。拟议以成其变化,若有法若无法,而后无遗憾。
认为在创作时,才与法缺一不可,没有法就没有文章,而没有才思则不能对法度运用自如。法的合理选择与运用,以至达到若有若无的境地,都取决于作者个人的才思。只要运用得当,法度不会束缚才思,才思也不会损坏法度,所谓“法不累才,才不伤法”、“用欲其神”是也。
由以上分析可知,明代辨体理论家引用“拟议以成其变化”一句来说明他们的文体观念,主要的还是在创作领域,也就是在文类文体与具体的个别文体之间的“体用”关系这个层面上展开。这是因为整个明代诗坛乃至文坛都在纠结一个问题:模拟与创新。前后七子以“格调”理论为中心,打出“文学复古”的旗帜,强调模拟;公安派、竟陵派则师心自用,强调创新。即使在七子派内部,也有侧重“拟议”还是侧重“变化”的分歧,而在“拟议”的一端,也存在着“拟形”还是“拟神”的纷争。他们各执一端,互相攻击,在气象上难免显出狭促不足的一面。而赵梦麟、顾尔行、许学夷等这些处于明代中后期的辨体理论家,他们运用“体用”论来看这个问题,就比较辩证和圆融。
参考文献:
[1]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M].//大复集卷三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M].//空同集卷六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李攀龙.拟古乐府序[M].//沧溟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李攀龙.古诗后十九首并引[M].//沧溟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八三[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王世贞.屠长卿[M]//弇州续稿卷二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M].罗根则,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8](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M],王伯华,陶庆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9]李东阳.麓堂诗话[M].//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Z].北京:中华书局,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