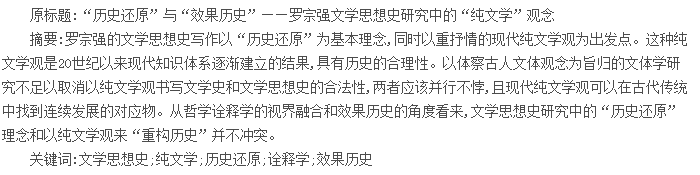
一
在罗宗强的文学思想史研究中,“历史还原”是他反复提及的核心理念。这个理念是针对当今古代文学思想史和古代文论研究中某些对古人的过度阐释和不当转化而发的。他反对用现代的理论任意附会、装扮古人,把古人文学思想不当地现代化。在1999年发表于《文艺研究》的《古文论研究杂识》一文中,罗宗强对古代文论话语的“现代转换”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对于古文论的研究,不能急于“古为今用”,要怀着一颗平常心,以求真为目的,庶几可以达到“无用之用”:“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弄清古文论的本来面目,也可以说是研究目的……求真的研究,看似于当前未有直接的用处,其实却是今天的文化建设非有不可的方面……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只要我们以一种严谨的学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扎扎实实地研究,我们就有可能更快地前进,更快地接近新理论创造的境界。”
所以他把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第一位工作称之为“历史还原”。罗宗强在为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作序言时说:“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第一位的工作,应该是古代文学思想的尽可能的复原。复原古代文学思想的原貌,才有可能进一步对它做出评价,论略是非。这一步如果做不好,那么一切议论都是毫无意义的。我把这一步的工作称之为历史还原……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我以为,不论用何种的方法,都必须极重视历史的真实面貌。”[2]5“所谓历史的还原,就是弄清一种文学思想从萌生到发展的种种表现形态,弄清它产生和发展的前因后果。”
罗宗强的文学思想史研究采用了很多新的范式,如通过士人心态来链接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想,兼顾考察作品中的文学思想等,都是他“历史还原”理念的具体落实。但也有论者提出了质疑,认为罗先生在写作中是用后设的“纯文学”观念来框架古人:“他在考察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时,首先有一个理论预设,那就是认为文学是重抒情、重形式、重美,并把这作为文学与非文学区分的标准……尽管他声称历史还原,但是自己又不知不觉地拿着现代人的纯文学标尺去衡量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凡和这一标尺相符的,罗先生就认为是重艺术特质,回到了文学本身……如果和这一标尺不符,罗先生就认为是重功利,远离了文学本质。”
因此该文作者认为罗先生的文学思想史写作在“历史还原”这个理念上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尴尬”。这涉及当今的一种思潮,即对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写作中“纯文学”观合法性的质疑。本文试结合学术实践和理论对这个问题阐述自己的知见。
二
罗宗强关于文学思想史的文学观的确是一种纯文学观,他认为:“从总趋势看,从主要倾向看,我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重功利文学思想与非功利、重文学特征、重抒情的文学思想不断交替的过程。”[5]299因此他认为汉人的思想是“前文学思想”,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思想的总趋势是“沿着文学的艺术特质展开的,重抒情,重形式的美的探讨,重表现手段、表现方法”[3]4,是“淡化文学与政教之关系,而回归他自身”[3]337。可见,非功利、远离政教、重抒情、重表现手段、重表现方法,是罗先生文学思想史写作中隐含的文学观念。
这种文学观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作者们鉴于新中国成立后30年过于政治化的文学史书写所共同采取的立场。更远一些来说,这也是20世纪以来逐渐形成并为国人认同的一种文学观。中国古代的“文学”多指“文章”“学术”,和现代的“文学”有所关联和交叉的是“文”这个内涵十分宽广的概念。20世纪以来,在欧风美雨的吹袭下,国人逐渐建立了新的知识体系,文学从史学、哲学中独立出来。而且在对中西方文学史的考察中,国人注意到,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学,都大致可以分为杂文学和纯文学两种,如童行白《中国文学史纲》所说:“文学有纯杂之别,纯文学即美术文学,杂文学即实用文学也。”
而着五四运动以来对欧洲浪漫主义文学重抒情性的纯文学的介绍,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纯文学观逐渐为文学史写作者们所认同。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30年以阶级意识形态为标准的阶段后,人们又继续认同这种作为“人学”的纯文学观。
在这种纯文学观逐渐成为优势话语的复杂过程中,杂文学观虽然由于其局限性而被抛弃,但人们也一直在反思这种新的纯文学观是否和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情况相符。在当今的学术界中,这种反思仍在继续,上文提到的对罗宗强的质疑就是一例。
又比如,基于对古人的文学观念的同情理解,现在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应该注意古人的文体观念,因此对于古代文体学的探讨越来越多了。吴承学在《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绪论中说:“本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主要是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对中国古代原来非常重要的一些文体形态相当忽视。
因为从现在的眼光看,古代许多重要的文体形态是‘非文学’的文体形态,但是在中国古代实用文体形态与文学文体形态是浑成一体的。因此,我们的古代文体史研究,一定要从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的实际情况出发,避免以西方的文体形态分类学的框框来套用,削足以适履。”
[6]2如此看来,似乎纯文学的文学史观的合法性处于危险的边缘了,似乎还原古人的杂文学观念和文体分类是“历史还原”的更具有合理性的诉求。但如果以古人的杂文学观来进行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写作,就辜负了20世纪以来辛勤建立纯文学史观先驱者们的苦心了。纯文学史观是现代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拒绝纯文学观实际就是拒绝文史哲分立的现代知识体系,这和文化走向的大势是相背的。试问按此逻辑,哲学史、心理学史、伦理学史的观念也要抛弃吗?如果不能,为何文学史独然?冯友兰在编写《中国哲学史》时曾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
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7]1中国文学史为何不能如此呢?
而且这种新的纯文学观可以在古代文学传统中找到对应物,从而形成由古至今连续不断的一条脉络。
在政教和载道的正统文学观外,古代文学一直存在着重抒情、重自我的“文学性”传统,如陈伯海认为,昭明太子《文选》“沉思翰藻”的遴选标准以及陆机《文赋》中所说的“缘情绮靡”,都可以成为和现代纯文学观链接的“文学性”观念。20世纪以来新文学观建立的过程,其实也是对这种传统重新发现的过程。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书写,受古人的各种话语影响甚大。东海西海,心理攸同,重抒情重自我是普遍的人性,中国古人又何尝没有抒情性的传统呢?港台古典文学界所提出的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论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所以“纯文学”观不能说完全是舶来的。
其实文体学研究者的初衷也并不是反对以纯文学观来书写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吴承学在《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的绪论中区分了文体学研究和传统的文学史研究的不同使命,他说:“在文学史研究中,文体史是有一定独立性的研究领域。文体史研究在价值取向以及理论、方法等方面,不仅应该有别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也应该与一般文学史研究有所区别……文体史与文学史的视角有所不同,其价值判断也有所不同,有些作品在艺术方面水平并不高,在文学史上地位不高,但也许在文体形态方面有独到之处,在文体史上就有独特的地位。”所以,文体学研究诚然很必要,但并不妨碍传统的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以及理论、方法,也不妨碍当代研究者有自己的文学观念。
三
从诠释学上来说,当代的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研究从当代人的文学观念出发是必然的。海德格尔认为“解释”必然具有一种“先行掌握”,“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
[9]176所以当代人在试图还原历史时,必然会带有自己的历史性所带来的“偏见”。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的看法,而且认为“前见”是理解的条件,“偏见”不能被视作一种阻碍,而完全可以是合法的,是此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赋予解释者的生产性的积极因素。伽达默尔认为:“时间距离并不是某种必须被克服的东西。这种看法其实是历史主义的幼稚假定,即我们必须置身于时代的精神中,我们应当以它的概念和观念,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概念和观念来思考,并从而能够确保历史的客观性。
事实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的可能性。”[10]384时间距离所造成的“前见”其实恰恰为解释者提供了一种特定的“视界”,解释的意义就在于将自己的视界与前人的视界融合,这就是“视界融合”。伽达默尔还认为:“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10]387。每一代解释者面对历史流传物时都通过这种视界融合达到新的效果历史,而这随即又变成下一代解释者面对的历史流传物,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阐释学循环,这样流传物即解释对象的意义在历史的流转中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正如童庆炳所说:“由于不同时代解释者观念的不同,对同一部历史文本意义的构设和解说也就不同,那么这个历史文本的意义就不断增加,最终成为一个永远不断增加的意义链。”[11]330这才是诠释的真谛。
罗宗强注意到了历史还原的复杂性,充分认识到现代阐释学和新历史主义对于历史和文本难以完全还原的理论对于古代文史研究的启示。他认为,历史还原的困难,一是史料方面的问题,另外是主观因素不可避免的介入。在2005年的《我们如何进入历史》的讲座中,罗宗强对史料的庞杂、真实性和缺乏情况进行了充分估计,提出要小心面对史料,这是还原历史困难的一方面。另外他也认为在研究中主观因素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研究者要有自己的主见:“很多历史学家都说,研究历史,切忌主观因素的介入。说主观因素的介入,是史学家之大忌。
我对于这个说法颇不以为然。“”我们必须回到原典,但我们又不可能完全回到原典籍。我们不可能用古人的思维方法。思维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的思维,是现代社会培养起来的。”“我们用我们的思维方法,去理解历史,去对历史作出我们的解读,去再现,去重构,这就是我们的主观,是我们的主观介入。”[12]322纯文学观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思维方法,我们不可能回到古人的思维中去。可见,罗宗强也认识到哲学诠释学中所说的作为效果历史的合理前见的积极意义,他提出要用现代的思维去“重构历史”:“历史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此“任何对于古代的研究,都存在一个重构历史的问题”[12]317。
罗宗强在这里所说的“重构历史”和他一向主张的“历史还原”的研究理念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因为“前见”的本体性存在,所以“历史还原”必然是“重构历史”。而“重构历史”如果建立在合理“前见”的基础上,就是“历史还原”。所以“历史还原”和“重构历史”辩证统一的关键在于诠释者的“前见”是否具有合理性。伽达默尔区分了“使理解得以可能的生产性的前见”与“阻碍理解并导致误解的前见”[10]382。从上文的论述来看,“纯文学”观念显然是无法抛弃也不需抛弃的生产性的前见。那些在中西方比较中运用不当从而歪曲了古代文学原貌的理论运用,才是“阻碍理解并导致误解的前见”。罗宗强的“历史还原”所反对的只是歪曲历史,而不是合理地重构历史,关于这一点上文已有论述。而罗宗强也在反复强调“重构历史”不等于主观臆断,而是要在史料的基础上尽力还原历史的原貌:“我们重构历史,不是以我们想当然去重构,不是用我们今天的理论,我们今天的理论框架去任意地重构。我们必须根据历史提供的条件,去进入历史。”[12]321文学思想史的诠释就在“历史还原”和“重构历史”的张力中展开。同样道理,近些年来古代文论研究界提出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的主张和“还原历史”的研究理念也并不矛盾。童庆炳在论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时也一直将“历史优先原则”作为古代文论研究三个策略中的第一位,他强调古今对话要“把古人作为一个主体并十分尊重他们,不要用今人的思想随意曲解他们”[11]3。
综上,从哲学诠释学“效果历史”的角度来看,以当代的文学观念来梳理古代的文学流传物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应然的。历史写作的观念应该以当今时代所需要的观念为出发点。所以,不论是从实践还是理论角度来说,对古人文体观念的体察是必需的,但这主要是文体学研究的任务,不应以之束缚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的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