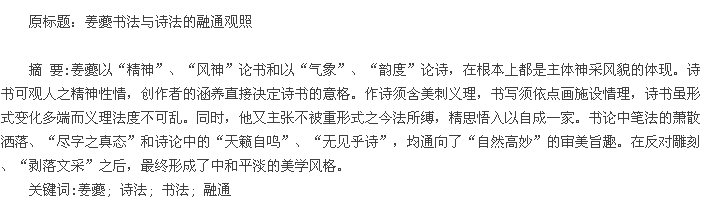
诗以语言造境,书以笔墨传情,二者的艺术形式与体制本为相隔; 然就其共同的“精神内核”而言,可谓二艺同道,相融相通。姜夔历经高宗至宁宗四朝,他虽终生未仕,却因其“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 211),与萧、杨、范、陆等中兴诗人名士多有往来。①其诗论集中体现在《白石道人诗说》与两篇《诗集自叙》中,书论主要结集于《续书谱》,均受到后人推崇并产生深远影响。如清人潘德舆云: “宋人诗话,《沧浪》及《岁寒堂》两种外,足以鼎立者,殆惟《白石诗说》乎? 其说极简极精,极平极远,此道中金绳宝筏也。”宋人谢采伯为《续书谱》作的序中称其: “议论精到,三读三叹,真擎书学之蒙者也。”对于在诗学与书法领域均产生重大影响的姜夔,后人在研究中却绝少注意其文艺思想的融通现象。本文即欲对其诗学思想与书法理论进行比较观照,以期深入把握其文艺观念。
一、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通
姜夔认为,无论是诗歌还是书法均是创作者人格精神的体现,这在诗论与书论中表现为对“意”的祈尚。从诗歌和书法作品中便可见出作者的人格修养,这又促成了他以德论艺的批评倾向。诗书与精神通,故接受者可用“以心会心”的方法读诗观书; 创作主体则必须积学以致涵养,尚雅而去俗。
姜夔在《续书谱·情性》中提出: “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通,其说见于 昌 黎《送 高 闲 上 人序》。”此说虽出于韩愈,却也是姜夔的主要文艺观念。韩愈在其文中云: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可见,张旭的草书非徒然而作,其精神意绪、万物之变均在书中有所寄寓,可以说,书法就是他某个时段内心世界的外化,这样书法也即具有诗歌般抒情言志的功能,故其草书之迹易学而其书写之心难得。姜夔的书论与诗论中处处表现出对精神之意的祈尚与对工拙之形的贬黜。《续书谱》云: “‘心正则笔正’,‘意在笔先,字居心后’皆名言也。”( 《用笔》) 可见他迎合了宋代以来的尚意书风,主张胸有成竹而字随意遣。论临摹时他提出: “临书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笔意。临书易进,摹书易忘,经意与不经意也。”( 《临摹》) 姜夔可谓深谙临书与摹书之道,摹书以纸覆于真本之上,随其大小、长短、位置而机械运笔,非精神所发也,写成之后与真迹貌合而神离; 而临书以帖置于侧,参其笔中之意与字之神采,以意运笔,发乎心性,故而虽失其形而多得其神,这与岳珂所云“临贴出于游艺,必有以观笔意”之意略同。姜夔在《诗说》中也贯彻了尚意精神,如论景与意的关系: “意中有景,景中有意。”又说: “意格欲高,句法欲响,只求工于句、字,亦末矣。故始于意格,成于句、字。”可见,姜夔认为,精神为本而艺之形式为末也。
姜夔将诗书均看做鲜活的生命体,它们非仅具文艺形态,且贯通着主体的神采风貌。他常以生命精神谈书论诗,在论及观书感受时说: “予尝历观古之名书,无不点画振动,如见其挥运之时。”( 《血脉》) 观书之点画如见书法名家挥毫自如之神态,“振动”一词极尽鲜活跳跃之精神。关于“点画振动”,姜夔进一步论道: “撇捺者,字之手足,伸缩异度,变化多端,要如鱼翼鸟翅,有翩翩自得之状。”( 《真书》) 如此之书自然给人以生命跃动之感。姜夔的书论与诗论中处处可见对精神风貌的推崇,论书法则曰: “有锋以耀其精神,无锋以含其气味。”( 《草书》)“点者,字之眉目,全藉顾盼精神。”( 《真书》) 他最欣赏的书法作品必须具有飘逸气韵与超迈风神,《续书谱》又云: “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 《真书》)“《定武》虽石刻,又未必得真迹之风神矣。
字书全以风神超迈为主。”( 《临摹》) 他还在《续书谱》中单列《风神》一节,足见其对字之精神层面的重视。姜夔论诗亦将其视作生命整体,他说:“大凡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他论诗书均喻之于生命体,不仅都以“血脉”论之,且书之气韵、风神即诗之气象、韵度也。此处论诗之“血脉欲其贯穿”即可用《续书谱·血脉》一节作为注脚: “字有藏锋出锋之异,粲然盈楮,欲其首尾呼应,上下相接为佳。后学之士,随所记忆,图写其形,未能涵容,皆支离而不相贯穿。”诗书之会通可见一斑。姜夔诗论中的“气象”指的是“诗人的人格力量与艺术精神的体现。其论“韵度”又追求飘逸,这与他追求书法的“飘逸之气”与超迈之“风神”也正相通。
人之精神寓之诗书,故姜夔提倡读诗观书当“以心会心”。他在《诗说》中明确提出: “三百篇美刺箴怨皆无迹,当以心会心。”这一方法的提出根源于孟子的“以意逆志”论,即以自己的阅历与修养为基础去体悟作者之思想感情。南宋理学家对此十分推崇并有所发展,朱熹在《诗集传序》中说: “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吕祖谦也指出: “《诗》者,人之性情而已。必先得诗人之心,然后玩之易入。得诗人之心以玩之,以自我之情而体之,于情性隐微之间而察之,此即姜夔“以心会心”的具体内涵。而这需要一个基本的理论支撑,即薛季宣所云: “人之性情,古犹今也。”( 《序反古诗说》) 古人性情可以今人性情移而观之,古今之人才得以冲破时空界限而进行心与心的交流。“以心会心”的方法可体作者之情,亦可见其性,因此姜夔强调以主体之品性论文艺。
如其论草书时说: “襟韵不高,记忆虽多,莫湔尘俗。若使风神萧散,下笔便当过人。”( 《草书》) 他认为人品决定书品,若书法家襟怀风韵不高,其书法不可避免地被尘俗所浸淫; 倘若情怀疏朗,其书自可过人。他还在《风神》一节将“人品高”作为首要条件,足见其对主体品格的重视。“字如其人”论源自扬雄的“书为心画”论,宋人尤其重视创作主体之胸次修养,如苏轼说: “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黄庭坚也说: “若使胸中 有 书 数 千 卷,不 随 世 碌 碌,则 书 不 病韵。”707)理学家更是奉行书札细事关乎人之德性的文艺观念。可见姜夔“以心会心”及以人论书均与宋人内倾的文艺观念相接轨。
诗书可以观人见性,这就要求创作者必须积学以致涵养,并且尚雅去俗。涵养是姜夔论诗书时对主体素质提出的一个重要条件,其意有二,即学问修养和德性修养。《诗说》云: “思有窒碍,涵养未至也,当益以学。”此论学问修养。姜夔又说: “吟咏情性,如印印泥。止乎礼义,贵涵养也。”此即德性修养。涵养既至,则自然尚雅而去俗。姜夔论诗书时多处强调去俗,论诗曰:“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又说: “体物不欲寒乞。”论书时亦以俗为病: “专务遒劲,则俗病不除。”( 《总论》)“俗浊不除,不足观。”“然极须淘洗俗姿,则妙处自见矣。”( 《用笔》) 可见,诗论与书论可会通观之。
二、义理法度不可乱
对于诗歌和书法创作,姜夔均特别推崇义理古法。他认为,诗须含美刺箴怨义理,书须遵点画施设情理,诗书虽形式变化多端,而古法不可乱。
姜夔的义理法度意识,无疑是对“专论句法,不论义理”之江西诗学的一个超越。
姜夔认为,诗之作须含美刺箴怨之义理,而书法起应变化、点画施设各有情理,均非苟然而作。
《诗说》云: “《三百篇》美刺箴怨皆无迹。”他认为《诗经》各篇非随意而发,皆由兴寄而作,其中隐含着深刻义理。南宋的真德秀也曾提出: “三百五篇之诗,其正言义理者盖无几,而讽咏之间,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谓义理也。后世之作,虽未可同日而语。然其间兴寄高远,读之使人忘宠辱,去鄙吝,翛然有自得之趣。而于君亲臣子大义,亦时有发焉。”380-381)姜夔“美刺箴怨皆无迹”即真德秀“正言义理者盖无几”之同调也。对于后世之诗,他认为优秀作品均须具有义理,因其皆应由《三百篇》而出: “诗有出于《风》者、出于《雅》者、出于《颂》者。屈宋之文,《风》出也; 韩柳之诗,《雅》出也; 杜子美独能兼之。”屈宋之文、韩柳之诗均是兴寄高远之作,多发不平之鸣,其中亦时有发君臣义理者。姜夔的这种文艺思想也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中,如他的著名词作《扬州慢》即是兴寄高远之作。南宋诗坛对江西诗派只讲句法的形式主义诗学进行了反拨,主张恢复古诗重兴寄义理的传统。如朱熹对沉溺于句法精工的诗风批评道: “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辞之善否,今以魏晋以前诸贤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于其间者,而况于古诗之流乎?”
他也提倡诗文须含义理:“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至说义理处,又不肯分晓。”需要注意的是,朱熹作为理学宗师,其文艺思想自然重道轻文; 而姜夔虽也讲兴寄义理,但毕竟没有放弃对形式之美的追寻。
姜夔在《续书谱》中对义理的重视,相对其诗论来说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认为,文字初造时非随意组合点画而成,施设点画各有义理存乎其中,因此欲作书须先识得造字之理。他说: “向背者,如人之顾盼、指画、相揖、向背。发于左者应于右,起于上者伏于下。大要点画之间,施设各有情理。”( 《向背》)“向背”指字的笔画形态变化关系的处理,姜夔虽也讲顾盼伏应之法,但非仅从字之形态论,而是上升到义理高度。他在《用笔》中说: “作字者亦须略考篆文,须知点画来历先后,如‘左’‘右’之不同,‘刺’、‘剌’之相异,‘王’之与‘玉’,‘示’之与‘衣’,以至‘奉’‘秦’‘泰’‘春’,形同理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字有形态相似者,作书时笔画易混,然而“草不离真”,要想写好草书就必须了解文字义理渊源,因义理即体现在字之点画施设中。那么字之渊源何自? 他认为当源于日常生活: “草书之体,如人坐卧行立、揖逊忿争、乘舟跃马、歌舞擗踊,一切变态,非苟然者。又一字之体,率有多变,有起有应,如此起者,当如此应,各有义理。”( 《草书》) 草书中变化多端之笔法实则饱含一切生活情景,因此点画起应也须合乎情理。他认为,能于书中见出义理的书法名家,“求之古人,右军盖为独步”( 《向背》) 。北宋书论家朱长文也曾以义理论书: “古之书者志于义理而体势存焉。《周官》教国子以六书者,惟其通于书之义理也。是故措笔而知意,见文而察本,可以劝善,可以惩恶,可以明事,可以辨形,岂特点画模刻而已哉! ”这样书教就具有了诗教功能。可见,义理书学在宋代颇为流行。
姜夔诗论与书论均极重法度,他的尚法意识非仅指形式技法而言,而是关乎诗书义理。《续书谱》论书之理与法曰: “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理也,唐人师之,法也。”何谓“字之真态”? 他解释说: “字之长短、小大、斜正、疏密,天然不齐,孰能一之? 谓如‘东’字之长,‘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疏,‘萬’字之密,画多者宜瘦,画少者宜肥。”( 《真书》)“天然不齐”即“字之真态”的外在表现,“天然”即对应着“理也”,字之真态即源于造字义理。字因义理不同而有大小疏密之异,而唐人主张“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之齐一论,姜夔应是据此而发。魏晋之书尚不失义理古法,能尽字之意义情态,故而高明。唐人师其形而亡其理,故仅进乎技而未达乎道。唐之书尚法,然而陷入“法工夫技”的误区,未能法其理,因而失却古法之本质。可以说唐法的建立正是对古法的解构。姜夔所尚之法,正是源于义理的古法,而非今人形式之法。他说: “颜柳结体既异古人,用笔复溺于一偏,予评二家为书法之一变。数百年间,人争效之,字画刚劲高明,固不为无助,而魏晋风轨扫地矣。”( 《用笔》) 姜夔虽深喜王羲之书,然而亦恨其失却汉魏古法: “大抵右军书成而汉魏西晋之法尽废,右军固新奇可喜,而古法之废实自右军始,亦可恨也。”
同样,姜夔论诗也重义理法度,《诗说》以“守法度”作为诗的定义,而此处的法度不能仅从句法格律方面去理解,也应包含兴寄传统及温柔敦厚诗教,这是他重义理古法的内在要求。
书法与诗歌创作在形式上会有诸多变化,但姜夔认为,义理法度必须遵守。他论草书曰: “虽复变化多端,而未尝乱其法度。张颠、怀素最号野逸,而不失此法。”( 《草书》) 这与朱熹论苏轼之文语气甚为相似: “东坡虽是宏阔澜翻,成大片滚将去,他里面自有法。”
( 3322)姜夔认为,王羲之字虽已达到随心所欲境界,依然有法度存乎其中而不可逾越: “右军书‘羲之’字、‘当’字、‘得’字、‘慰’字最多,多至数十字,无有同者,而未尝不同也,可谓所欲不逾矩矣。”( 《草书》) 同一字书写数十遍而无有同者指其笔势起应率多变化,而未尝不同则指笔画所含义理尚存。在论诗之奇正时,姜夔也主张万变不离其法: “波澜开阖,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是奇; 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可见,重义理法度是姜夔诗书理论的共同追求。
三、精思悟入以成自家风味
受“活法”论的影响,姜夔论诗书虽然主张不脱于古法,却又提倡不为成法所缚。他认为,只要博习而精思,识得优劣,久之自然悟入。一旦悟入,即可由法而出,自成一家风味。
古法含义理而今法重形式,姜夔认为应遵守古法而不为今法所缚,这与他追求韵度飘逸与超迈风神正遥相呼应。《续书谱》论真书曰: “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古今真书之妙,无出钟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 良由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书,类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矧欧、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楷书要求平正是唐人之法,而姜夔却认为唐前楷书笔势皆潇洒纵横,故比唐人更为飘逸。在论到“折钗股”、“屋漏痕”、“锥画沙”等笔法时,他认为“此皆后人之论 …… 然皆不必若是”( 《用笔》) 。这些均体现了他尊重古法的同时冲破今法的冲动,这种欲望也体现在他的诗论中。《诗集自叙》云: “三薰三沐,师黄太史氏,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而后来“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何以禁语? 此即为法所缚的结果。他后来自成一家完全得益于对江西诗学之成法的摆脱。
针对法缚之病,姜夔提出博习而精思的治愈方法。他论书曰: “真有真之态度,行有行之态度,草有草之态度。必须博习,可以兼通。”( 《行书》) 何谓博习呢? 他在《诗说》中云: “多看自知,多作自好矣。”
这其实就是一个由生入熟的过程,与吕本中所谓“只熟便是精妙之处”362)意思相近。精熟论同样体现在姜夔书论中: “所贵熟习兼通,心手相应,斯为妙矣。”( 《总论》)“此必至精至熟然后能之。古人遗墨,得其一点一画,皆昭然绝异者,以其用笔精妙故也。”( 《真书》) 如何能由生入熟呢? 这便需要一个精思玩索的过程。姜夔论诗道: “诗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虽多亦奚为?”
姜夔之“精思”论亦是宋代“尚理”文艺思潮的体现。《续书谱·临摹》云: “皆须古人名笔,置之几案,悬之座右,朝夕谛观,思其用笔之理,然后可以临摹。”精思其理而后识得用笔之法,这正是姜夔“精思”论的实质所在。
关于精思,还有一个识与悟的过程。识即识得优劣,见得病处。他说: “不知诗病,何由能诗? 不观诗法,何由知病? 名家者各有一病,大醇小疵,差可耳。”他以诗之对偶举例说: “花必用柳对,是儿曹语。若其不切,亦病也。”由识而悟才是识的根本目的,因此姜夔主张悟入。他论诗说:“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舍文无妙,胜处要自悟。”这与陆游的体悟可谓感同身受,陆游讲述自己学诗过程时说: “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
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弘大。”( 《示子遹》) 可见,只有悟入才可使诗歌创作从文辞格律束缚中解脱出来,以达既工且妙的境界。这与范成大论书也颇为相似: “又学时不在旋看字本,逐画临仿,但贵行住坐卧常 谛 玩,经 目 著 心。久 之,自 然 有 悟 入处。”理悟的工夫自然是不易的,因此姜夔感慨道: “岁寒知松柏,难处见作者。”
悟入是冲破法茧之缚的必然途径,唯有悟入才能自得神气。在悟到为江西诗法所缚后,姜夔将黄诗“偃然高阁”,至此而后蜕化出新的诗风,他引他人之论曰: “物以蜕而化,不以蜕而累。以其有蜕,是以有化。”他大悟“学即病”,此处的“学”即指一味按照他人诗法模仿而作,而不是指学问修养,因此他才提出“不若无所学之为得”的忠告。在他的诗书理论中均反映出强烈反对因袭模仿的倾向。他论书曰: “大抵下笔之际,尽仿古人,则少神气。”( 《总论》) 唐人尽仿颜鲁公《干禄字书》,故而“应规入距”,“类有科举习气”。于是他在论书之风神时提出“时出新意”的主张。
反对模仿在姜夔的诗学思想中表现尤为突出,其《送项平甫倅池阳》诗云: “论文要得文中天,邯郸学步终不然。如君笔墨与性合,妙处特过苏李前。”在他看来,诗之因袭模仿最大的弊端则在于“语虽似之,韵亦无矣”,因此他主张诗文笔墨出于自家之真性情方妙。反对因袭则贵在自得,姜夔在《诗说》结尾处提出了创作初衷:“《诗说》之作,非为能诗者作也,为不能诗者作,而使之能诗; 能诗而后能尽我之说,是亦为能诗者作也。虽然,以我之说为尽,而不造乎自得,是足以为能诗哉? 后之贤者,有如以水投水者乎? 有如得兔忘筌者乎?”
可见,姜夔认为,初学诗者可以依《诗说》之法而作,而对于能诗者则要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即不为法缚而造乎自得。他还用乐调比喻自得曰: “一家之语,自有一家之风味。如乐 之 二 十 四 调,各 有 韵 声,乃 是 归 宿处。”
正所谓“余之诗,余之诗耳”。这与杨万里、陆游等人诗学思想可谓异口同声,诚斋曰: “传派传宗我替羞,各家各自一风流。”( 《跋徐恭仲省干近诗》) 陆游也高唱: “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龙黼黻世不知。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 《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 他们的独创自得精神何其相似,以致姜夔自己也惊讶道: “诸公咸谓其与我合也。”对于如何自得他还提出了诸多方法,即语言上: “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用事上: “僻事实用,熟事虚用。”章法上: “篇终出人意表,或反终篇之意,皆妙。”
四、自然中和之审美旨趣
姜夔还提出“四种高妙”的审美追求,其最高审美原则为“自然高妙”。他论书法提倡用笔自然和纵横萧散,论诗主张天籁自鸣和“无见乎诗”,其本质内涵是相通的。姜夔论诗书均反对人工雕刻,尚平拙黜险巧,追求一种平和冲淡之美。
“四种高妙”说由姜夔在《诗说》中提出: “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碍而实通,曰理高妙; 出事意外,曰意高妙; 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 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即“自然高妙”,姜夔论诗强调自然流出,随意而发。在《诗集自叙》中,他说:“诗本无体,三百篇皆天籁自鸣。”又说: “其来如风,其止如雨,如印印泥,如水在器,其苏子所谓不能不为者乎?风雨之自然而来以喻诗之自然而出,水之随物赋形以喻诗之自然浑成,均出于苏轼之论,此处明显见出当时“以苏正黄”的诗学倾向。他还称赞杨万里诗: “年年花月无闲日,处处山川怕见君。箭在的中非尔力,风行水上自成文。”
由人力到天然,落尽豪华见得真淳,这是学诗的两个阶段,姜夔将其概括为“见乎诗”和“无见乎诗”。他说: “彼惟有见乎诗也,故向也求与古人合,今也求与古人异; 及其无见乎诗已,故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见乎诗”自是人力琢雕而成,“无见乎诗”则是天籁自鸣,如水之随物赋形,行于当行,止于当止。“自然高妙”不仅是姜夔的诗论主张,亦是他书论中的审美祈尚。如他论笔法时说: “然而方圆、曲直,不可显露,直须涵泳一出于自然。”( 《方圆》) 楷书贵方笔,草书贵圆笔,而姜夔却主张相互参用,这样方能笔不露锋,含蓄浑厚。在《风神》中他指出: “自然长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泽之臞,肥者如贵游之子,劲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贤士。”此即追求字之自然真态,反对人工雕琢,所谓“非奇非怪,剥落文采”之意。
姜夔追求自然高妙,表现在具体的理论上则是尚平夷黜险怪,尚朴拙去妍巧。他论书法用笔时认为: “不得中行,与其工也宁拙。”( 《用笔》)工未达乎上,则欲刻意求工之字愈下,不若返而求拙,拙且尚有古韵。他反对“古人拙处今人巧”的创作现象,于是对于提倡古拙的他来说只能慨叹“乾坤虽大知者少”论诗如此,论书亦如是。魏晋之书能尽字之真态,而“大令以来,用笔多失,一字之间,长短相补,斜正相拄,肥瘦相混,求妍媚于成体之后,至于今世尤甚焉”( 《真书》) 。
追求形式上的妍媚,则失于巧密,这也是唐人书法弊病: “不可太密、太巧。太密、太巧者,是唐人之病也。”( 《位置》) 反对巧密,正是宋代复古思想在诗书理论中的共同追求。在《诗说》中姜夔提出“雕刻伤气”,对于人工雕琢之弊可谓一语中的。
陆游所说的“琢雕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 《读近人诗》) 正可作姜夔“雕刻伤气”之注脚。
叶适《王木叔诗序》也提出相似的观点: “夫争妍斗巧,极外物之变态,唐人所长也; 反求于内,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这与姜夔批评唐人书法巧取妍媚而不能尽字之真态在审美本质上可谓相通。
姜夔又主中和观,反对偏执放荡以至狂怪怒张的文艺风格。他论诗之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有“四失”; 又论诗中“七情”之失曰: “喜词锐,怒词戾,哀词伤,乐词荒,爱词结,恶词绝,欲词屑。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其惟《关雎》乎! ”
论诗之文辞: “若鄙而不精巧,是不雕刻之过; 拙而无委曲,是不敷衍之过。”从诗之内在性情到外在形式,均体现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姜夔论书法之中和主要从用笔、用墨等技法上展现出来,在《用笔》中云: “不欲太肥,肥则形浊; 又不欲太瘦,瘦则形枯; 不欲多露锋芒,露则意不持重; 不欲深藏圭角,藏则体不精神。”笔之肥瘦藏露均需约于中道,过则有失,犹如不及。再者,他认为,用笔垂放之际亦须懂得收缩,运笔不可肆意,他引米芾的话说: “无垂不缩。无往不收。”( 《真书》) 又说:乍徐还疾,忽往复收。”( 《草书》) 均主张有所“止”。《续书谱·用墨》云: “墨浓则笔滞,燥则笔枯。”他认为,书法至颜、柳为之一变,其原因则是“结体既异古人,用笔复溺于一偏”( 《用笔》) 。
颜柳用笔劲健有力,号称颜筋柳骨,而姜夔认为其雄健有余而圆润不足,这种偏执一端的书法自然与其中和文艺观相违。
自然高妙与中和观最终导向了平淡含蓄的美学风格。宋人普遍推崇中和平淡、含蓄蕴藉之美,如苏轼提倡“外枯中膏”、“似癯实腴”的诗美主张。
欧阳修之文“虽平淡,其中却自美丽”。宋理学家也多喜陶诗,朱熹说: “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陆九渊也称赏陶诗: “来自天稷,与众殊趣,而淡泊平夷”。姜夔对陶渊明平淡诗美体悟道: “陶渊明天资既高,趣诣又远,故其诗散而庄、澹而腴,断不容作邯郸步也。”他充分认识到陶诗之淡而实美,并体会到其具有蕴藉之意味。因此,他论诗书均尚意而重含蓄。论书曰: “平藏善含蓄。”( 《笔势》)“不欲多露锋芒,露则意不持重。”( 《用笔》) 其论诗云: “语贵含蓄”,“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此处隐约可见受杨万里以意味论诗的影响,《诚斋诗话》曰: “诗已尽而味方永,乃善之善者也。”“诗有句中无其辞,而句外有其意者。”含蓄尚意自是中和平淡美的内在要求。
总之,姜夔于诗歌、书法均有很高的理论建树,而他的文艺思想又是融通一体、自成整体的理论体系。他认为,诗书与创作主体的精神相通,因此在他的书论与诗论中均有尚意的理论倾向,即以气韵、风神论书和以气象、韵度论诗; 因人之精神寓之诗书,所以他又提出“以心会心”的鉴赏方法以及重涵养、尚雅去俗的主体修养论。对义理法度的重视也是姜夔诗书思想的共同追求,但他又受到当时“活法”与“悟入”理论的影响,提倡尊重古法而又能自成一家风味。而自然高妙与中和平淡也是他对诗歌和书法共同的审美追求。对姜夔诗论与书论进行融通观照,打通艺术门类界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其综合文艺思想。
注释:
①参见夏承焘的《姜白石系年》,《唐宋词人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第 425—448 页。
②本文所引《续书谱》内容均来自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13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553—562页,《续书谱》共分《总论》、《真书》、《用笔》、《草书》等凡二十篇,下文凡《续书谱》引文仅随文注出各篇之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