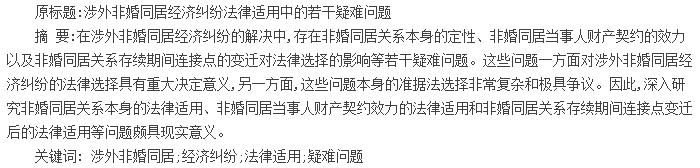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以及伦理道德观念的变迁,世界各国的非婚同居现象日益普遍。人类社会进入 21 世纪以后,非婚同居更是跨越国界出现了涉外非婚同居现象。作为世界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和重要的移民输入国,我国学界加大对涉外非婚同居经济纠纷法律适用的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鉴于涉外非婚同居相对于传统涉外民事关系的特殊性,我们在构建其法律选择体系时,有关非婚同居关系本身的定性、非婚同居当事人财产契约以及非婚同居关系存续期间连接点的变迁等疑难问题,对涉外非婚同居当事人之间经济纠纷的法律适用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为更好地解决涉外非婚同居当事人之间经济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对以上几个疑难问题有必要予以专门研究。
一、非婚同居关系定性的准据法选择
(一) 非婚同居关系定性之意义
我们探讨涉外非婚同居经济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首先有一个明确的前提,那就是具有涉外因素的非婚同居关系是确定存在或被认可的。因为,涉外非婚同居关系倘若不存在,或者涉外非婚同居关系没有被相关国家法律认可,那么,探讨涉外非婚同居经济纠纷如何适用法律便有违该问题的内在逻辑顺序。因此,涉外非婚同居关系的定性是解决涉外非婚同居经济纠纷法律选择问题的前提性问题。
目前,世界各国对非婚同居关系的立法存在重大差异。其中,既有中国、埃塞俄比亚、美国的佐治亚州、伊利诺伊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等国家和地区完全否认非婚同居关系的合法地位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法律既不承认非婚同居者相互之间的特定权利、义务关系,也不承认非婚同居者对第三方的任何权利);也有诸如瑞典、丹麦、挪威、荷兰等一些国家,将非婚同居看作是一种新的家庭关系模式,从而制定了很多类似婚姻家庭关系的专门制度,较大程度地维护了非婚同居者的合法权益;而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则通过立法仅仅赋予非婚同居者部分权利。还有像德国这样相对保守的国家,只承认同性非婚同居关系,其立法只对婚姻关系中的异性同居关系予以保护。
因此,一旦涉及具体的涉外非婚同居经济纠纷,根据不同国家的法律,往往导致非婚同居关系本身的不同定性问题,继而对非婚同居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造成决定性影响。因此,解决涉外非婚同居经济纠纷,首先面临的如何选择对非婚同居关系进行定性的准据法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非婚同居关系定性之法律选择
关于非婚同居关系定性的法律选择问题,笔者认为,需要从非婚同居关系成立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在非婚同居关系成立的实质要件上,世界各国的立法千差万别。大多认为,非婚同居关系,应该从有无同居能力 (主要包括是否成年以及有无婚姻关系在身等)、有无同居持续时间条件、有无性别要求等几个方面予以考察。然而从实际情况看,这些要件在不同国家的立法中相距甚远。
比如,在同居持续时间条件上,丹麦的正式同居要求同居持续时间为三年以上,英国、西班牙等的法律要求持续两年以上,菲律宾则要求同居时间满五年,而挪威的 《联合家庭法》 以及澳大利亚部分州却无具体的时间要求;在同居的性别规定上这种差异则更大,美国的佛蒙特州、德国、芬兰、冰岛等只认可同性同居关系,很多国家 (地区) 对异性伴侣同居和同性伴侣同居都予以承认。
综上,认定非婚同居关系的成立与否,其实质要件标准有很大的差别,这时候如何选择准据法就具有了决定意义。
本文认为,对非婚同居关系实质要件的准据法选择,既不能背离国际私法的基本理论和相关领域的经验,应将非婚同居当事人共同住所地国法、非婚同居登记地国法、国籍国法等与非婚同居具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作为非婚同居关系实质要件的准据法,同时,鉴于尊重既得权的思想以及最大限度地维护非婚同居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考虑,将尽可能使非婚同居关系得以成立的法律确定为准据法,也是我们确定非婚同居实质要件准据法的重要价值依托。
至于非婚同居关系成立的形式要件,世界上有非婚同居关系立法的国家大体采用了 4 种方式:与婚姻相同的同居登记制、与婚姻不同的同居登记制、与婚姻相同的同居不需登记制以及与婚姻不同的同居不需登记制。丹麦、芬兰、荷兰、德国、南非、冰岛等国家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佛蒙特州、加拿大魁北克省等地区采用的是第一种方式;西班牙、法国、比利时等国家和美国新泽西州、夏威夷州等地区是采用第二种方式;丹麦、菲律宾等国家是采用第三种方式;而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挪威、瑞典、日本等国家和美国华盛顿州、加拿大普通法系地区采用的是第四种方式。
综上,由于世界各国对非婚同居关系形式要件规定了四种不同的模式,从而导致对同一个涉外非婚同居关系由于选择了不同的准据法而面临认可与否的不同命运。
本文认为,关于非婚同居关系形式要件的准据法选择问题,应该因应国际私法理论的发展趋势,借鉴相关领域的立法经验,以行为地法为主 (即非婚同居形式上是否成立应当以登记非婚同居关系所在地国的法律作为准据法),或者采用同居所在地国家法律作为准据法 (主要针对非婚同居关系无顺登记的国家)。同样,基于国际私法理论中维护国际民商秩序稳定的既得权思想,尽量使非婚同居关系不因形式要件上的瑕疵而归于无效,这既顺应了国际私法理论的发展方向,充分体现了国际私法准据法选择中的“有利原则”,从而有利于最大限度保护非婚同居当事人的权益。
总之,无论是实质要件方面,还是形式要件方面,非婚同居关系本身的定性问题,本文认为,既要遵循国际私法的基本理论,又要从维护国际民商秩序的既得权思想和“有利原则”出发,力求使非婚同居关系尽量有效的法律得到适用,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非婚同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非婚同居财产契约的准据法选择
涉外非婚同居当事人双方基于意思自治在同居开始前或同居期内就双方经济关系缔结同居财产契约,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此一来,非婚同居财产契约本身的许多问题,诸如契约的实质效力、形式效力、同居者是否具备财产行为能力等应该由何种法律支配,便成了涉外非婚同居经济纠纷法律适用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一) 涉外合同准据法选择的相关理论
从涉外合同领域的法律适用理论及相关实践来看,目前,合同自体法理论已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
《戴赛与莫里斯论冲突法》 对合同自体法理论有系统表述:“合同自体法”,是指当事人意欲适用于合同的法律,或者在当事人的意思没有表示,也不能根据情况作出推断时,指与交易有最密切、最真实联系的法律。分规则一:对于支配合同的法律,如果合同当事人用文字表达了意思,那么该明示意思原则上决定了合同自体法。分规则二:如果合同当事人关于支配合同法律的意思表示没有用言语表达出来,他们的意思表示应该从合同的条款、性质及案件的一般情况推断出来,该推断的意思表示即决定了合同的自体法。
分规则 3:如果合同当事人对支配合同的法律的意思表示没有明示,也不能从情况作出推断,那么合同授予与交易有最密切、最真实联系的法律支配。1980 年罗马 《合同之债法律适用公约》 完全采纳了这一理论,同时,为了平衡客观论与主观论的分歧,公约在最密切联系理论基础上创新出特征性履行原则,将特征履行方的惯常居所地、主营业地推定为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地方。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公约明确指出,它所规定的基本方法不适用于与夫妻财产制有关的婚姻财产约定。
至此,笔者不得不深思,上述在涉外合同领域已被奉为经典的合同自体法理论究竟能否应用于与夫妻财产契约十分类似的非婚同居财产契约呢?
(二) 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契约实质效力的准据法选择
诚然,无论是夫妻财产契约,还是非婚同居财产契约,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身份属性而与普通的商事合同有本质的差别。
一般说来,后者在法律适用上几乎没什么限制,1980 年 《合同之债法律适用公约》 正是因为赋予了合同当事人合意选择准据法的极大自由,因而慎重地将夫妻财产契约排除在外。因此可以说,合同自体法理论总体上并非因为身份性质而排除适用,而且当今世界各国也普遍承认这一点。英国学者戴赛、莫里斯等认为,“(1) 婚姻财产契约的效力、解释与效果一般适用合同自体法; (2) 婚姻财产契约的自体法,除非存在相反的理由,就是婚姻住所地法; (3) 婚姻财产契约当事方可以通过明示或默示选择适用住所地法之外的法律。”
从上述戴赛与莫里斯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适用合同自体法的理论上,具有人身性质的财产契约与普通的涉外合同并无本质差别,他们不过是将婚姻住所地法直接视为与婚姻财产契约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而已。笔者认为,由上可知,对于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契约本身而言,按照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理论及实践,将合同自体法理论引入非婚同居契约是完全可行的。具体说来,我们首先应该考察非婚同居契约当事人双方是否在同居财产契约中有明示的或者默示的选择准据法的合意,如果没有这种合意,那么就要考察与该具体非婚同居财产契约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作为准据法。通常情况下,与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契约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应该包括共同住所地国、惯常居所地国、共同国籍国等地的法律。
(三) 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契约形式效力与缔约能力的准据法选择
对于非婚同居财产契约的形式效力以及非婚同居者的缔约能力是否也应该由同居财产契约的自体法决定?这种法律适用对于非婚同居当事人而言是否公正?这是我们需要继续深入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非婚同居财产契约的形式效力问题。目前,世界各国关于合同的形式主要有书面契约、口头契约以及其他形式三类;而且对于不同种类的合同,其形式要求也不一样;另外在是否需要登记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如此一来,对于非婚同居财产契约而言,很可能会因为适用不同国家的法律而造成不同效力的局面。那么,究竟应该适用何种准据法来作为判断非婚同居财产契约形式效力的标准呢?笔者认为,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契约本身就是非婚同居当事人双方选择非婚同居这一较之于婚姻同居更加自由的同居生活模式的主要内容,是非婚同居者自主决定他们自己财产关系的重要体现。因此,在非婚同居财产契约的形式效力方面,也适宜遵循当代国际私法理论和实践的一般做法,即遵循尽量使合同有效的原则,将尽可能使非婚同居财产契约有效的法律作为准据法。具体说来,我们应当为非婚同居财产契约形式效力问题构建一个选择性冲突规范,只需满足其中一个国家的形式要求,就应当肯定非婚同居财产契约形式上的效力。当然,契约自体法、契约缔结地法、共同住所地国法、共同国籍国法等都可以成为这个选择性冲突规范中的选项。
第二,我们来考察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契约缔约能力的法律适用问题。非婚同居财产契约作为一类特殊的合同,同居当事人的缔约能力问题是否也应援用普通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则?对普通涉外合同的缔约能力问题,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是,当合同缔结地法或者合同自体法认为当事人有缔约能力而根据属人法却没有缔约能力时,往往会限制属人法的适用,从而尽量使当事人具有缔约能力,以维护法律行为的效率和交易的安全。值得注意的是,在非婚同居财产契约中,非婚同居者缔约能力的有无,主要影响的是非婚同居当事人内部财产契约的效力,一般不会像普通商事合同那样对交易安全和商事效率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本文认为,在非婚同居财产契约缔约能力的法律适用上,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差别。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普通商事合同缔约能力法律适用规则的合理性,因为它毕竟有利于维护契约本身的严肃性、符合当事人的可预见性。所以一方面,在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契约的缔约能力问题上,也应当在非婚同居当事人可预见的范围内尽量使当事人具有缔约能力,以维护非婚同居当事人财产契约的严肃性、尊重非婚同居者自主决定私人事务的权利。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契约与普通涉外商事合同的本质差别,因而不宜完全剥夺非婚同居者以无缔约能力主张合同无效的权利。
当然,这种以欠缺缔约能力主张非婚同居财产契约无效的权利不得滥用,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一般认为,这种欠缺缔约能力的判断必须是来自与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这也体现了对另一方同居当事人最起码的契约公正。无论是非婚同居财产契约的缔结本身还是契约目的都是指向同居生活,因此,本文认为,非婚同居双方当事人的共同住所地国 (惯常居所地国) 一般可视为是与非婚同居财产契约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
三、涉外非婚同居关系存续期间连接点变迁的准据法选择
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的准据法选择,还有一个疑难问题,那就是,在非婚同居关系存续期间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中的连接点发生了改变,该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的准据法是否需要随之而改变?这一问题直接影响了涉外非婚同居经济纠纷最终适用何国法律作为准据法,因而是涉外非婚同居经济关系准据法选择中又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涉外非婚同居关系存续期间,存在以下三种可能改变的连接点情况:一个是非婚同居者通过新的合意改变之前的准据法选择合意;第二个是非婚同居者在同居期间将共同住所地 (惯常居所地) 由一国迁到另一国;第三个是非婚同居者在同居期间改变共同国籍的情况。对第一种情况,普遍认为,非婚同居当事人基于主观意愿变更准据法选择的合意,其实质就是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形成了新的合意,其本身恰恰就是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实践都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适用选择合意变更后的准据法,除非这种法律选择合意的变更具有损害第三人权益等不正当目的。
因此,当涉外非婚同居当事人用新的准据法选择合意变更之前合意的情况下,我们也不作继续的探讨,即原则上也应该将意思自治变更后选择的法律作为准据法。
在继续探讨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连接点改变所引起的准据法选择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准据法的不可变理论与可变理论作一简要介绍。所谓不可变理论 (也有学者称其为准据法恒定论),是指准据法一旦经过连接点的指引得以确定后,就不再因连接点的事后变更而改变,即仍然适用依据之前的连接点所确定的法律。英国、法国以及日本等国的相关国际私法实践中都有采用不可变理论的情况。在戴赛所代理的 De Nicols v. Curlier 夫妻财产纠纷一案中,英国法官最终认为,夫妻财产制不会因为婚姻住所地的变迁而改变,该案中当事人的婚姻住所地原来在法国,因此,作为夫妻双方财产关系准据法的法国法,既要适用于他们在法国生活期间的全部财产,也要适用于他们移居英国后新获得的所有财产。这是奉行准据法不可变理论的一个典型案例。
后来,戴赛和莫里斯在其名著 《戴赛和莫里斯论冲突法》 中阐述的“婚后婚姻住所的变迁并不因此而改变夫妻对于对方财产的权利”就是对该权威案例所奉行的不可变理论的概括表述。
所谓可变理论,是指准据法可以随着涉外民事关系中连接点的变更而变更,即适用依据新的连接点所确定的法律。很多国家的国际私法实践也采纳了这一理论。如日本法例中对婚姻效力、扶养义务、父母子女关系、动产物权等都允许采用可变连接点;英国则将自然人国籍、住所、居所以及动产所在地等视为可变连接点;此外,1989 年生效的 《瑞士国际私法》 第 55 条和 2007 年 《土耳其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与国际民事诉讼程序法的第 5718 号法令》 第 3 条也采用了准据法的可变理论。
准据法不可变论的理论基础在于,基于之前连接点选择的准据法被视为是当事人双方“默示选择”的结果,因此这种“默示选择”也应该具有和明示选择一样的效力,即一经选定准据法都不能改变。20世纪以来,这一理论基础饱受质疑,主流的观点转而将此视为是法律自身运作的结果。德国学者萨维尼认为,默示合同的一般假定是没有根据的。
相反,可变理论则是立足于当代社会客观现实,从法律上承认并尊重涉外民事关系当事人自由改变生活场所尤其是住所地的权利,相应地,准据法选择理论势必要对此作出回应。因此,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准据法应该是与当事人和案件“当时”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而不应该是与当事人或案件已经没有任何实际联系的甚至是几十年前的法律。显然,可变理论由于更加强调涉外民事关系与某一地域法律 (准据法) 之间内在实质联系的动态性,因而更符合连接点的国际私法价值。综上,在涉外婚姻财产关系以及与之相似的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中,连接点变更是否导致准据法变迁的问题,种种趋势表明采用可变理论更符合国际私法理论发展的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可变理论长期以来饱受诟病,主要在于它的稳定性、当事人的可预见性及可能出现的法律规避等问题。因此,本文认为,在采用可变理论的同时,有必要对其予以适当限制:对于借改变连接点以达到规避法律目的的任何行为,在选择准据法时都应该予以限制,应该否定其准据法可变的主张。这一点也早已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对于同居住所地改变导致非婚同居财产关系准据法变迁的情况也要作具体分析。一是为了保持非婚同居财产关系准据法适用的相对稳定性以及对当事人双方的公平考虑,在另一方反对的情况下,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同居住所以实现非婚同居财产关系准据法变迁的情况不能支持。
二是基于国际私法的实体价值取向,为体现对非婚同居关系中弱势地位一方的保护,在改变准据法会明显损害弱势一方权益的情况下,也不宜采用可变理论。三是当非婚同居住所地变更导致准据法变迁,但一方当事人确实能够举证证明财产来源,适用新的准据法对其明显不公平的,本文认为可考虑放弃可变理论转而适用原准据法。
对于涉外非婚同居经济纠纷是以共同国籍国法作为准据法的情况,如果同居当事人双方获取了新的共同国籍,除非争讼财产确实与原国籍国法有更密切联系,或者有其他必须适用原国籍国法的情况,本文认为也可采用可变理论。
随着全球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开放,近年来,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和重要的移民输入国。因此,随着我国国民对婚恋家庭观念的日渐开放,可以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涉外非婚同居必将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基于此,在加强对国内层面非婚同居进行法律规制的基础上,如何应对和解决涉外非婚同居所带来的法律冲突,如何对我国涉外非婚同居财产关系准据法进行选择是我们国际私法学界不得不认真考虑的一个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