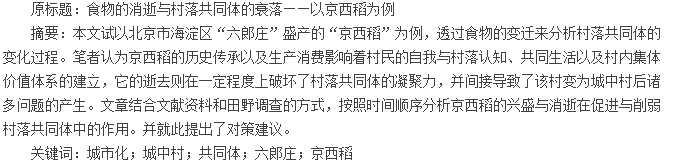
一、问题提出与理论准备
在社会变革时期,许多学者都在试图寻找新的概念来理解传统社会如何向现代社会转型。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用共同体的概念描述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群体,主要包括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等几种基本形式。他用共同体的概念来与现代社会做区分,认为“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与此相反,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
在滕尼斯的定义里,血缘共同体逐渐发展为共同居住的地缘共同体,之后又发展为精神共同体。因此共同居住和共同的信仰是共同体得以形成和维系的重要因素,共同体内的人们有共同的朋友,共同的敌人。而社会里的人们则表面上和平生活和居住在一起,实际上却并没有集合在一起,是分离的。类似于滕尼斯对精神共同体的定义,涂尔干用“机械团结”的概念来描述社会中成员基于共同感情和信仰所形成的集体,认为不论范围大小,这种团结方式都建立在共同意识之上。然而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学中形成了另一种“有机团结”。他强调这种团结是由一些特别而又不同的职能的部分通过相互间的确定关系结合而成的系统。在第一种团结中,个人附属于集体,只有群体没有自我;第二种团结则强调个人的人格和特征,这时人们通过分工,而不是共同的信仰联系起来。此后,学者们对共同体的探讨逐渐转向城市。作为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将城市理解为城市社区,认为它不仅是单个人的集合,也不是各种社会设施的聚合,而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城市同其居民的各种重要活动联系密切,是自然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帕克对城市共同体的定义依旧延续着滕尼斯的传统。随着时代的发展,学者们也开始从对实体共同体的讨论转向对网络社区等新型共同体的关注。有学者认为虚拟社区可以取代传统社区,更有相信地域仍是组成共同体的重要因素,而虚拟社区只是对传统社区的一种补充。虽然西方学者们对共同体概念有许多不同的理解,所强调的重点也从血缘和地缘逐渐向集体认知与共同信仰所转变。但是总体而言,共同体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其中的个体有规律的参与群体生活;其次,不同成员有集体信仰和共同的认同;最后共同的地域仍是共同体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费孝通等人首先将community的概念译为“社区”并将其引入中国社会学研究。吴文藻认为“社会是描述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到的。”
费孝通从农村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的社区是以传统农业为基础、以自然村社为单位、以传统权威及血缘、地缘、亲缘关系连接起来的、具有生产生活上相互协助功能的人群聚合体。
之后社区的概念经历了许多变化,而国内学界也逐渐将community赋予“社区”与“共同体”两种理解。随着近年来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和城市的扩张,城乡结合部地区出现了许多城中村并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有学者通过社区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自然村落在向城中村转变的过程中既保留着相对完整的地缘基础又有着人民公社时期留下的集体化遗产,因此村落共同体在城市化进程中会重新获得生存活力。
她提出“新村社共同体”的概念,用它定义城中村在非农化经济结构基础上形成的新共同体。然而在笔者研究中发现,虽然在非农化的过程中许多村落基本保持着原来的地域基础,但是在自然村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同认同、价值观与传统不断弱化,共同的村落生活也不断减少,村落共同体并没有获得新的活力,而是不断衰落并导致了村内的诸多问题。
由此,本文将以食物为切入点,作为观察共同体的视角。即以北京市六郎庄村特产的京西稻为例,通过透视其产生、兴盛以及消亡的过程,分别从地域、共同生活和村落集体认同与信仰这三个方面探讨村落共同体的变化。人类学家们一直将食物视为了解这个世界的透视镜,如道格拉斯(Douglas)提出食物的选择反映着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布迪厄(Bour-dieu)则较强调食物在社会区隔方面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人们对于食物的偏好在很小的时候便习得,并反映着他们的社会地位。相比之下,另有人类学家如梅格斯提出食物在建立社会联盟和促进团结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故本文试图借助这些理论,通过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讨论京西稻的兴盛与衰亡对六郎庄村落共同体形成与削弱的作用,并进一步分析共同体在城市改造中的重要意义。
二、京西稻的产生与共同体的形成
六郎庄村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玉泉山脚下,是个风景秀丽的自然村落。因其土壤肥沃、水源充足,从东汉便开始种植水稻。明朝时期已形成规模,到清朝末年“京西稻”的出现和发展则帮助村民们建立起了集体认同,成为了村民定义自我和区分他者的重要象征符号。清朝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在皇家园林里发现一株稻子“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便在玉泉山一带开始推广。雍正年间,稻田的面积不断扩大。除了六郎庄,还逐渐扩大到海淀、功德寺、北坞等地区。自此,京西稻作为皇家贡米有了重要的象征意义,在它被皇宫贵族用来区隔与普通百姓的地位的同时,也被村民用来区分六郎庄村与其他村落,建立着“我们”与“他们”的区隔。慈禧当政时期,她将颐和园外半里包括六郎庄在内的一带皆划为“御田”,归朝廷所有,不允许农民私自交易稻谷。于是京西稻的美名享誉京城,六郎庄村作为京西稻的试验田,有着“京西第一村”之称。虽然六郎庄的普通村民只能享用到非常少量的京西稻,但他们却将其看作是自己村落的重要标志,并将流传下来的皇上种稻米的故事作为重要的象征资本,以定义村落和自己的地位。随着京西稻的象征意义不断被建立起来,它逐渐变成了自我和村落认同的基础,在村落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京西稻的发展与村落共同体的壮大
从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初,六郎庄村落的地理面貌并无很大的改变,但在京西稻不断增产后,村落共同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大部分现居六郎庄的原住村民出生并成长在这个时代,因此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京西稻一方面仍是村民集体认同的象征符号,另一方面则为村民提供了宝贵的集体经历、共同回忆甚至经济收入。从50年代就由国家统一收购加工成“特供”大米,作为中央机关用米。一直到70年代,京西稻仍按等级收购,分入仓库,单独保管。集体化时期,京西稻的产量和面积都有所增加,六郎庄的地位也不断提升,那时村民们在稻田中的生活成为了重要的集体记忆。虽然当时人们生活水平还并不高,但是他们却对村落有着深厚的感情。据当时关于村落的记载“六郎庄是个庞然广阔的大庄,地广而肥沃,人多而擅于多种经营。但大多数人还是玉米糊糊窝窝头,两根咸萝卜一碗涮锅水,生活简单到了极点。”
当被问到当时的生活,68岁的张女士回忆到:“那个时候我们还小,家里日子过的虽然清贫,但是特别开心。六郎庄是块宝地,田里长得都是好东西,荸荠和藕随便吃,夏天还可以摸到小鱼。”
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京西稻不断增产,人们的生活质量也逐渐提高。1956年,海淀区54个社都改为高级社,引进了喷雾器、脱粒机等大型农业机械。1958年,海淀人民公社成立,海淀区京西稻亩产达到290公斤,创历史新高。1963年之后,随着水利设施的发展,京西稻发展到2.37万亩,亩产338公斤。在整个海淀公社中,六郎庄大队所种京西稻比重最高,在总耕地面积三千一百多亩中,京西稻占了两千七百多亩。据73岁的老王回忆:“那个时候村子里的景色特别美。秋收的时候就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稻穗金灿灿的。在麦地中间还有碧绿的藕和荸荠田,现在再也看不见这样的景色了。”
作为一种共同生活,在集体耕作中京西稻凝聚了人们之间的关系。村民儿时在田间玩耍,以及长大后共同耕作京西稻的经历不仅成为了他们重要的共同生活,也建立起来了一套价值体系。村民老谭告诉笔者:“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小孩,一起在田里玩大的,下了课经常一起去稻田里抓青蛙,逮蜻蜓。长大一点之后,我们就一起在田里干活,感情非常深。家里面不论有个大事小事,大家都互相知道而且相互帮忙,跟亲兄弟一样。”
58岁的老高感慨说;“那个时候六郎庄的村民都拧成一股绳,人情味也浓。要是有六郎庄的人出去被别人欺负了,所有六郎庄人都得站出来为他打抱不平。”
村里另一位葛姓村民说,“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选干部都是看谁种稻子种的好,人家才信服你。”“我那个时候带头干活,所有的队员都听我的,我跟他们的关系就像家长和孩子一样,很多队员家里调节不了的私事都是由我出面协调。比如说当年队里有个队员家里要办丧事,选日子的时候家里大大小小都拿不定主意,还是我出面给确定的(日期)。”
这种共同生活和日常接触加深了人们之间的关系和对村落的认同感,而围绕着生产京西稻的生产所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念也把村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改革开放初期,京西稻品种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日益提升。随着国家敞开收购,其供应范围越来越大,逐渐进入普通百姓家庭。京西稻独特的美味,以及外界对其的赞誉更加加深了村民对该稻米以及自己村落的认同。70年代末期,海淀区技术人员从日本引进了越富品种,并在1979年至1986年全面推广。
80年代后,随着栽培技术的提高,在1981年干旱低温的情况下,京西稻亩产424.3公斤。1995年,插秧逐渐机械化,水稻亩产达到490.3公斤。与此同时,六郎庄的人口也不断增加。据村民老葛回忆:“小时候京西稻是朝廷贡米,特别珍贵,因此每逢重要日子,母亲才会在小米里掺一点点京西稻。吃过以后那味道一辈子都忘不了,总是想吃。以至于到了后来,吃京西稻不再成为问题的时候还是总舍不得吃。”
63岁的老高说:“京西稻原来一直是贡米,很难吃到。改革开放以后,普通民众才真正吃上京西稻。那米味道非常香,谁家一煮,隔着好几条街都能闻到。而且煮出来的米汤都是绿色的,米粒一粒一粒都能数出来。吃了那个米,别的米都不想吃了。”
由于京西稻的名气传遍北京城,在它逐渐市场化的过程中,村民不仅可以亲自享用到京西稻,也可以将其所具有的象征资本转化为经济收入。葛队长给笔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出去办事,跟办事的人聊了起来。他无意中提到爱吃京西稻,我说这个简单,我就是六郎庄的人。他立马变得特别兴奋,问了我好几次是否能给他带点米尝尝,而且态度一下变好了很多。”
可见京西稻的美味和美名不仅将村民们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也为他们带来了收入。布迪厄不同,梅格斯认为食物在建立社会联盟和促进团结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初这段时间内,村民不仅加深了对村落的认同也围绕着京西稻的生产建立起来了一套价值体系。
四、京西稻的消逝与共同体的衰落
80年代后期我国城市化飞速发展,位于城市近郊的村庄和耕地不断被城市所吞噬,六郎庄亦是如此。到了1990年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水资源的短缺,京西稻的种植面积逐渐减少。据报道,1996年以来,海淀区农业人均收入增长力下降。海淀区政府顾问汪定涯认为海淀的水稻虽为经济增长做出过重要贡献,但成本过高,耗水量过大,对化肥依赖性越来越强,制约了人口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并衍生了环境问题。不仅失去了市场竞争力,还与中关村的发展形成了鲜明反差。2000年,海淀区正式宣布“京西贡米”第二年停种。2001年,京西稻便挥别京城。
此后,田地上建起了中关村科技园区,金黄的麦穗被一片片高楼大厦所取代。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一方面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打工者,他们试图寻找廉价的住所。另一方面,失去耕种收入来源的六郎庄的村民们开始通过加盖房屋并以相对便宜的价格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获取收入。据2010年《北京晚报》的一篇文章报道,“小小的村庄里居住了5万多人,其中4万多人全是外来打工者。”
村子的主干道“六郎庄大街”上挤满了各式店铺和移动小商贩,于是村内店铺参差不齐,道路上经常污浊不堪。在被主干道分开的南北两个居住区内,村民一方面保留着传统的生活习惯,在家周围种植蔬菜水果,或是饲养家禽家畜;另一方面为了增加租金收入,不断扩建房屋,增加楼层。由于缺乏管理,村内许多搭建十分危险,垃圾随意倾倒,居住环境恶劣。2010年,北京市政府将其列为重点整治的50个城中村之一,并计划用两年的时间将其拆除。
六郎庄环境的恶化和众多社会问题的产生与京西稻的消逝密不可分,村落不仅失去了其象征符号,原有的集体生活和共同信仰也遭到破坏,村落共同体不断瓦解。首先,村民原来的集体生活的经营方式被各自为战的方式所取代。白天客居六郎庄的流动人口外出打工,原住村民则聚在一起打牌下棋,或是聊天喝茶。这表面看是一种消遣,实则是在寻找潜在的租户。老吴说:“现在村子里的人都没有原来那么团结了,主要是白天都在自己的出租房里,照顾着自己的生意,互相接触少了很多。年轻的一代也不像我们年轻时都在田里种地,感情比我们那会儿差远了。”
老吴的夫人对我说:“你看现在的村里面,垃圾乱扔,公共厕所也总是臭气熏天。原来有稻地的时候,这些粪便都可以用来种地,种出来的稻子又好又没有污染,还不浪费。现在没有稻地了,大家都只想着租房子,也没有人关心村里的环境了。”
其次,围绕着京西稻建立起来的认同和价值体系开始变化,衡量个人能力的标准逐渐从耕种技巧的好坏变为了赚钱多寡,这也导致了村民对公共事物参与的减少和对集体认同的弱化。葛队长说:“自从不种地以后,村里给好多人安排了打扫村子的工作。但大家都不爱做,挣不到钱。都愿意租房子,来钱快,现在村子里是越来越乱。”
由于大量流动人口住在村内,许多家的出租房内都安装了防盗门,监控录像等设施防止偷窃。老吴说:“原来家家户户都敞着大门,因为我们都是六郎庄人。大家都非常熟悉,如果有外人进来,马上就能知道。现在村子里都是各地来的人,为了安全考虑,家家户户的门上都上了锁,已经没有原来的人情味了。”
可见随着京西稻的逝去,村民的共同生活不断减少,原来在京西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念和对村落的认同也在城市化过程中被打破,村民对集体的信任和关注逐渐转到对个体和金钱的关注,村落共同体不断遭到破坏。
由京西稻的案例可以看出,虽然地域对建立和维系共同体有着重要作用,但集体的共同生活和信仰对共同体的发展亦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村落原住民前后的变化非常类似于滕尼斯所描述的共同体与现代社会的区别,村民逐渐从共同生活向单纯的聚合发展。流动人口的涌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出租与承租相互依赖的关系,但村落内的分工并没有发展全面,因此也未形成涂尔干所说的“有机团结”。旧有共同体的打破和新秩序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种非城非村地带的诸多问题。
五、结论与应对措施
在我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经济飞速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随着城市周边的自然村落逐渐变为城中村,村落原有的文化秩序遭到破坏,即在村民共同生活和集体回忆减少的同时,对村落的认同也不断弱化,以自然村落为基础的价值体系逐渐被以个人主义和经济收入为信条的价值所取代,村落共同体也随之衰落。
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通过一个较长时段的观察,以京西稻的变迁来分析六郎庄村落共同体从形成到衰落的过程。调查显示,村落共同体在建立村落秩序和凝结村民关系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的破坏是导致村落环境恶化、犯罪率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笔者认为,在城中村整治和改造的转型期,应该将共同体中的一些重要特质保存下来,并注重其与城市社会的结合。首先应该重新树立村民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对新的村落或者社区的认同。让他们明确自己是“农民”还是“市民”的身份,以及自己所属的群体。因此除了在户籍上对村民的身份予以改变,还应该使他们在文化和心理上对自己的身份和行为方式有新的认同。其次要加强村民在村落或者改造以后的新社区中的对公共事物的共同参与以及共同生活。要将村民的生活与村落或社区联系在一起,加强其参与感与集体感。最后要重新树立一套围绕着新的社区生活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念。随着自然村落生产和生活方面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观念与之相适应才能解决转型期产生的诸多矛盾。我们认为,只有通过这些方面的改造才能建立新的共同体以并重新树立集体的认同,逐渐使村落共同体过渡到城市共同体。这些方面在改造城中村的过程中虽然时常处在隐形的地位,却有着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