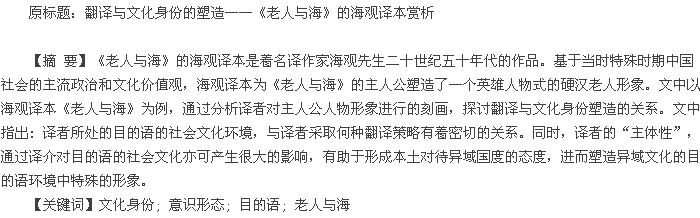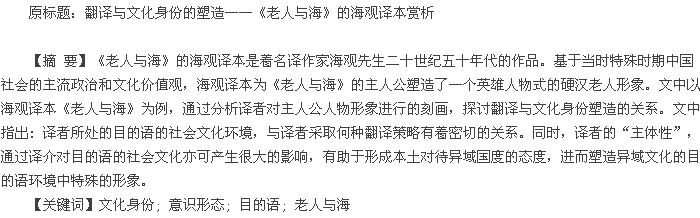
1 引言
自翻译学诞生之日起,人们便从未停止过关于翻译如何最贴切的表达原文的意义,译文与原文怎样才能做到意义上完美的对等的讨论。传统翻译学追求译文要忠实于原文,认为原文与译文之间是“模型—复制”的关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兴起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潮推翻了传统翻译学以原文文本为中心的翻译理念,而尝试将翻译放在社会和文化这个大环境下进行审视。以意大利裔美国籍学者劳伦斯·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学者尝试从社会形态和历史文化的角度,解释不同译者采取不同翻译策略和“话语策略”的原因,认为翻译文本的差异是建立在目的语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差异的基础之上的。韦努蒂( 1996) 还指出,不同译者所采取的不同的翻译策略同时也对目的语的社会和文化历史产生影响。译者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理念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由此所产出的译文很可能在读者心中形成一种对异国的思维定式,塑造源语文化在译入语社会的一种“特定的文化身份”( 韦努蒂 1996) 。
翻译不仅受到历史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会反过来作用于历史和意识形态。对于这一论点,韦努蒂进行了认真而系统的研究。他认为( 1996) ,翻译通过对外国文本的译介而谋取对目的语文化的文学典律、理性范式的修正和维护。
翻译即是对外来的社会属性进行的“篡改”,由于这种篡改体现在了文本的实体和话语策略之中,翻译便可以被称为文化政治实践( Cultural Political Practice) ,为外国文化建构一种本土的自我认同感,或者说颠覆了本土文化。
在《翻译、共性、乌托邦》一文中,韦努蒂将翻译称为是一种“本土的抄写”,即翻译总是尝试将外国文本的语言和文化进行归化处理,使得受众更容易接受这种外语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差异,进而能够与外语文本进行交流。翻译的本土抄写将外语文本的魅力施加在另一种文化的大量受众身上。一部翻译的畅销书很有可能会使得外国文本蜕变为本土支持者本来所共有的东西,如一种方言、一种文化话语、乃至一种意识形态,翻译对假想的受众产生了商业效果,也产生了文化和政治效果( 韦努蒂,2005: 186 -187) 。
在《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一文中,韦努蒂( 1996) 论证了翻译对目的语文化的塑造、革新和变动都产生着影响。韦努蒂指出:
“翻译的文本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被出版、评论、阅读和教授,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环境下,产生着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异域文本通常被改写以符合当前本土文学中主流的风格和主题。翻译能够制造出那些显现本土政治与文化价值的外国定式……翻译有助于塑造本土对待异域国度的态度,有助于塑造对特定族裔、种族和国族的尊重或者蔑视,能够孕育出对文化差异的尊重或者基于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之上的仇恨。”
翻译对文化身份的塑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通过对异域文化的阐释,在目的语社会中树立异域文化的典律和范式; 另一方面则是塑造一个本土主体( 韦努蒂 2003) ,将目的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已占权威的价值观投射到译本中去。由此可见,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构成了重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无形中指导了译者的翻译趋向和定位,进而决定了原作在目的语环境中的文化身份的塑造。本文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通过对《老人与海》的最早的大陆译本,海观译本的分析,探讨翻译对原作在目的语社会的文化身份的塑造的影响。
2 社会意识形态对海观译本的影响
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文艺批评的标准是“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1949 年后,这一思想被视为“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指导性纲领”,因此,文学艺术中浓厚的政治色彩可见一斑。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虽然没有制定明确的翻译政策,但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以及文艺界一系列方针、政策无疑也对翻译选择起到规范作用。如果说当时有具体的翻译选择规范的话,那么这个规范的关键词就是‘优秀’和‘进步’”( 查明建 2003: 73) ,而所谓的“优秀”和“进步”的标准,便是“看作品在意识形态上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和巩固,在创作方法上能否体现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查明建 2003: 73) 。
不仅如此,由于进行了文学艺术的机构化,即“所有的作家都隶属某一组织机构( 国家‘干部’) ,都有固定的薪俸”( 洪子诚 1999: 32) 。而翻译家也必须加入某个翻译协会或作家协会,这样一来,翻译便被纳入了官方控制的体制之中。再加上50 年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体制内的作家、翻译家,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表现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追随和迎合的态度。文学翻译家金人先生曾经说过: “翻译工作是一个政治任务。而且从来的翻译工作都是一个政治任务。不过有时是有意识地使之为政治服务,有时是无意识地为政治服了务”( 查明建 2003: 73) 。
新中国成立之初,海明威的作品在中国是命运多舛的:1949 年,中国停止了对海明威的译介; 1956 年,《译文》在 12月号上,突然刊登了海观翻译的《老人与海》; 第二年,新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林疑今 40 年代的旧译《永别了,武器》的修订本,并且新文艺出版社还在同年出版了海观译的《老人与海》的单行本。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 原来,1956 年 7 月,苏联刊物上发表了称赞海明威《老人与海》的文章,海明威在中国也因此获得了译介资格。1961 年,海明威逝世,《世界文学》在 7 月号上刊登了海观译的海明威短篇小说《打不败的人》”( 查明建 2003: 73) 。
由此可见,海译的《老人与海》,本身就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是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译介的典型缩影。不幸的是,六十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海明威的作品不再符合中国文学翻译的规范,在此后的十几年间,中国对海明威的译介又出现了一片空白。
3 海观译本对文化身份的塑造
在五十年代的政治文化环境下,海观对《老人与海》的译介也是必须遵循主流的意识形态的规范,为政治服务的。海观有意识地谴责了海明威作品中表现出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但同时又高度赞扬他与劳苦大众的亲密情谊以及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的 1962 版译本后附的《译后记》( 海明威1962: 87) 就足以说明这一切:“海明威是一个有良心的正直的作家,他憎恨强暴,对普通人寄予无限的同情,对庸俗的资产阶级抱着内心的鄙视。
但海明威是一个思想极其复杂、世界观极其矛盾的作家,这种矛盾反映在他的每一部作品里面……他的人物又往往是悲观的、绝望的、孤独的、往往是没有目标的斗争,没有代价的死亡。作品中的景物也是荒凉的、寂寞的。总之,他赞美了爱,又赞美了死,他就在爱与死的搏斗中赞美着他的英雄,可是他所赞美的只是个人主义的英雄的悲剧……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面一个正在探索中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苦闷的心情。为了加强作品中的凄凉的情调,作者运用了他惯常使用的那种反复不已的独白,来增加它的艺术力量……同时,在老渔人和孩子中间,在他和他的同行中间,却存在着温暖的友爱。这部小说虽然有悲观,有宿命论,但是比起作者以前的作品来已经添上了一种新的东西,这就是淡淡的乐观主义,这在作者的创作历程中应该说是一个好的倾向。”
海观将海明威描述成为一名“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制度上苦苦探索,十分苦闷: 一方面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有局限,作品充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色彩,另一方面他的新作的“进步性”也是不容忽视的,与之前的作品相比较,《老人与海》多了一种属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的“淡淡的乐观主义”。
译者对文本的解读必将直接影响其采取的翻译策略和倾向,而且进一步对译文读者产生直接的引导作用。海观的《译后记》充分反映了他对《老人与海》一书的解读。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译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对 50 年代社会意识形态的维护和加强。
海观的《译后记》写到,老渔人的身上反映出了海明威思想上的矛盾,一方面有超乎寻常的毅力,一方面又感到胜利很渺茫。海明威的这种矛盾心理在以下两个分析例子中清晰地反映了出来。
例 1:
原文:
“I told the boy I was a strange old man,”he said.“Now iswhen I must prove it. ”
The thousand times that he had proved it meant nothing. Nowhe was proving it again. Each time was a new time and he neverthought about the past when he was doing it.
“I wish he'd sleep and I could sleep and dream about thelions,”he thought.“Why are the lions the main thing that is left?
Don't think,old man,” he said to himself. “Rest gently nowagainst the wood and think of nothing. He is working. Work aslittle as you can. ”。
译文:
“我告诉过那孩子,我是一个古怪的老头儿,”他说。“现在我一定要证实这句话。”他证明了一千次都落了空。现在他又要去证明了。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开端,他也决不去回想过去他这样做的时候。
他想: “我希望它睡去,这样我也能够睡去并且梦见狮子了。为什么狮子是我留在脑子里一件主要的东西呢?”他自言自语的说: “别想吧,老家伙。靠在木板上休息去,什么事儿都别去想它。它正在处理干活哩。你呀,你气力花的越少越好。”
为了突出体现小说中的这种“苦闷的心情”,海观有意识地对原文进行了一定的“改写”,以渲染一种凄凉的情调,反映出海明威思想上的矛盾以及他对现实的无奈之感:
在与大鱼周旋了两天里,老人有无数内心独白,在他筋疲力尽而鱼儿终于快要浮出水面之时,老人再一次给自己鼓劲。原文中的“the thousand times that he had proved it meantnothing”被译为“他证明了一千次都落了空”,显然和原文有出入。原文的本意是过去的一千次证明都算不了什么,表达的是老人迎接新挑战,再一次证明自己生存力量的豪迈,这是老人精神胜利的一大证明。作为一名迟暮的老人来说,出海捕鱼恐怕是唯一能再次证明自己的机会了,因此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完成。
海明威曾经说过: “谁也不能长生不老。但是一个人到了临终,到了必须同上帝进行最后一次战斗时,他总是希望世人记得他的为人,一个真正的人。如果你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那就会使你永生”( 吴然 2005: 181) 。这是一种对死亡之美的情结,不畏惧死亡,也就对一切无所畏惧了。《老人与海》的主人公正是带着这种情结上路的。
但是海观却似乎曲解了原意,“落了空”三个字满满是对现实的无奈之情,看起来老人是身不由己,不得不迎接挑战,在挣扎中给自己鼓劲,乐观主义中却尽显无奈。说到底,这样的处理是为译文的整个苦闷,悲观的基调服务的。译文中流露出了海观对海明威的“死亡情结”的负面评价,显然他很不赞成海明威对死亡的赞美,认为“他所赞美的只是个人主义的英雄的悲剧”( 海明威 1957: 87) 而已。
此外,海观在翻译中采用了大量北方方言的口语习惯,像儿化音如“老头儿,事儿”和语气助词如“吧”,“哩”,“呀”等从某种程度上刻画了一副老人喃喃自语的画面,让人不禁感到老人有英雄迟暮的感觉。
例 2:
原文:
“I'd like to buy some if there's any place they sell it,”hesaid.
What could I buy it with? He asked himself. Could I buy itwith a lost harpoon and a broken knife and two bad hands?. . . . . .
I must not think nonsense,he thought. Luck is a thing thatcomes in many forms and who can recognize her?
译文:
“我倒想买点儿运气,要是有地方买的话,”他说。
“我拿什么去买运气呢?”他自己问自己。“我买运气,能够用一把丢掉的鱼叉,一把折掉的鱼叉,一把折断的刀子,一双受了伤的手去买吗? ……”他想: “别再胡思乱想吧。运气是各式各样的,谁认得出呢?”
在最后一群鲨鱼到来之前,筋疲力尽的老渔人自言自语,希望上天能给他更多的运气。与例 1 的译文一样,译者在这里也使用了语气助词,一改原文的快节奏,语气显得异常的沉重,“别再胡思乱想吧”更流露出老人信心的不足。老人在考虑“买运气”的时候,译者故意把“买运气”放在句首,更强调了老人对得到运气的怀疑。
4 结语
本文以解构主义的“文化转向”为基础,根据韦努蒂提出的翻译和文化身份的塑造理论,以着名翻译家海观 20 世纪 50年代的译作《老人与海》为例,分析探讨了翻译与文化身份塑造的关系。海观译本中所描写的老人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大海上漂泊数天,以超乎寻常的毅力与厄运搏斗却最终失败而归。译者将老人最后的结局定义为失败,定义为悲剧,将其归咎于个人英雄主义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这是对英美文化中所弘扬的个人主义的强烈谴责,无疑是和社会主义对集体主义精神的弘扬和礼赞保持了一致。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垂垂暮年的老人依然不忘与厄运搏斗,这种不服输的精神也成为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的象征,是《老人与海》值得译介,并在读者中传播的重要原因。
透过上文的分析,结合解构主义的文化翻译论,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一方面,译者所处的目的语的社会文化环境,对译者在翻译时采取的翻译策略产生着重大的影响。译者对原语的解构和阐释,都要围绕目的语文化来进行。这时,译者对原文进行的“本土抄写”,深深打上了目的语文化的烙印,如必须尊重目的语文化的传统和禁忌等等。最终,本来属于异域文化的陌生的东西,转化成为了目的语读者能共同分享的,熟悉的东西。这样做最终的目的,若不是迎合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鉴赏趣味,对主流文化浪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和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就是尝试颠覆这种主流文化,创造出一种新的东西来。显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海观先生的《老人与海》译本,遵循的就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文学标准。而另一方面,译本所努力传达的信息,在当时的大陆读者中产生了如此大的共鸣,说明翻译本身反过来又对当时的社会文化潮流施加着巨大的影响力。换言之,通过《老人与海》的中文译本,中国读者在异国的社会与文化中,看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同时,在译本引导下,对个人主义等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进行批判。
译者的“主体性”是通过译介对目的语的社会文化产生影响。翻译有助于形成本土对待异域国度的态度,进而塑造异域文化的目的语环境中特殊的形象,即树立了一种“典律”( canon) ———目的语文化对异域文化的一种思维定式。诚如韦努蒂所言: “翻译能够制造出那些显现本土政治与文化价值的外国定式,这些影响有可能上升到民族层面的意义,从而排斥那些与本土习见所设定的议题不相关的争论与分歧”( 韦努蒂 1996) 。而这种典律一旦建立,便具有延续性的,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成为了两种文化之间沟通的主导思想。
分析以上种种因素,我们于是不难理解海观的《老人与海》所采取的话语策略。总而言之,翻译从某种程度上并不属于译者个人的行为,而是上升到了整个民族的层面,是一个民族与另一民族的沟通交流。事实上,对翻译的研究也由此衍生上升到了对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的层面,为我们反思政治、文学和社会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参考文献]
[1]海明威·厄内斯特( 1957) ,老人与海( The Old Man andthe Sea) ,海观译[M]. 上海: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2]海明威·厄内斯特( 1997) ,老人与海 ( The Old Man andthe Sea) [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3]海明威·厄内斯特( 2005) ,老人与海 ( The Old Man andthe Sea) ,海观译[M].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4]海明威·厄内斯特 ( 2006) ,老人与海 ( The Old Man andthe Sea) . 曹德志,白云天编[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5]洪子诚( 1999) . 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6]韦努蒂·劳伦斯( 2005) . 翻译、共性、乌托邦,见: 陈永国( 编) ,翻译与后现代性[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86 - 214.
[7]韦努蒂·劳伦斯( 1996) . 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
[8]吴然( 2005) .“硬汉”海明威作品与人生的演绎[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9]查明建( 2003) . 意识形态、诗学与文学翻译选择规范——— 20 世纪 50 ~80 年代中国的( 后) 现代主义翻译研究[D]. 香港: 博士学位论文,香港岭南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