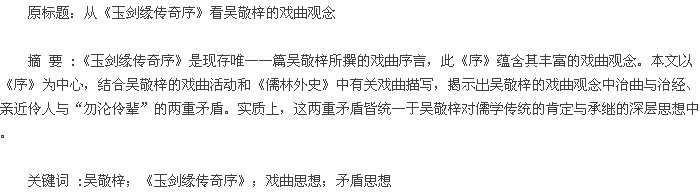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是一位对戏曲十分熟悉的小说家,他本人也非常爱好戏曲。在《外史》中,吴敬梓描写了大量戏曲演出活动(涉及之处迨几十处之多),有的全景式展示了清代雍乾时期南京、扬州等地戏曲发展的盛况,有的详述了士绅堂会演出的完整过程,对“莫愁湖湖亭大会”的描写更是着意借助戏曲活动,营造真实的儒生士子生活环境,塑造出一大批栩栩如生的士林群像。有的时候,吴敬梓还有意利用戏曲剧目来预示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发展。因此,戏曲不仅是吴敬梓创作《外史》凭借的艺术手段,同时也成为其传达创作主旨和表达思想倾向的重要载体。作为“思想家的小说家”,吴敬梓本人对戏曲的态度和主张,或潜藏在《外史》的戏曲活动描写中,或零星地散落于其他文学作品中,其中他为友人李本宣所作传奇《玉剑缘》题的序文,为我们了解吴敬梓的戏曲思想打开了一扇窗户。
一
《玉剑缘传奇》是吴敬梓友人李本宣所作,今有刻本传世。李本宣,字蘧门,江都人,祖籍扬州,后定居南京长达二十年之久,是吴敬梓生平诗友,常结伴冶游。《文木山房集》中就有四首有关李本宣的诗,而李本人也曾为《文木山房集》作过序,二人交往甚密,友谊深厚。据陈美林先生推考,吴敬梓大约作此序于乾隆十七年(1752)冬。(P420)在此前三年,即乾隆十五年(1749),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已全部脱稿,并且,是年小说已开始广泛被人传阅 “: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之。”(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外史》的完稿和为《玉剑缘》作序,都是吴敬梓晚年的事,这时文木先生的文艺思想已定型了。《玉剑缘传奇序》中蕴含的戏曲思想,是吴敬梓成熟的文艺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玉剑缘传奇》主要写淮南人杜器(子材)和李氏才女珠娘一笑之缘,历经曲折终成良配的爱情故事。《玉剑缘》未能摆脱才子佳人始离终亨的俗套旧窠,多遭人訿诟。但吴敬梓或出于对友人的客套颂美,或缘于对李剧切实的体认,在《序》中对《玉剑缘》的人物刻画与辞采风神有赞美之词,“吾友蘧门所编《玉剑缘》,述杜生、李氏一笑之缘,其间多所间阻,复有铁汉之侠,鲍母之挚,云娘之放,尽态极妍”,“读其词者沁人心脾”.除却这些赞美的文字,细品序文,不难发现《玉剑缘传奇序》虽区区百言,但蕴含着吴敬梓对戏曲这种艺术形态的深刻认识。
首先,他认为戏曲作品是剧作家借以寄慨的产物。《序》中云 :“君子当悒郁无聊之会,托之于檀板金樽,以消其块磊。”从戏曲创作动机角度申明剧作家是在“悒郁无聊”的时候,“以消其块磊”而创作的戏剧。阐发了戏剧创作的原动力不是外在的功利性目的,而是剧作家在生活中积聚的感受及在此感受基础上产生的一种难以遏止的激情。“消其块磊”的观点,一方面吸取了司马迁“发愤著书”、韩愈“不平则鸣”的精神内核,一方面也是对“兴观群怨”说的一种改造。“兴观群怨”是孔子对于诗歌所能发挥社会作用比较全面的概括,但吴敬梓的着眼点主要在“怨”,将内心激情尤其是对现实的抑郁不平作为戏剧创作原动力。
“抑郁无聊,消其块磊”的戏剧创作原旨,与其友人程廷祚、金兆燕等人别无二致。程廷祚曾作《莲花岛》传奇,意欲借用离奇的情节一吐胸中抑郁块磊,表达建功立业的愿望。金兆燕为其作序云 :“度《莲花岛》之作,盖自为立传,而与天下共白其欲表见于世者耳。”金兆燕本人作传奇二种 :《旗亭记》、《婴儿幻》。后者取《西游记》孙悟空借芭蕉扇,大战红孩儿二事,揉合而成,而《旗亭记》写唐人王之焕状元及第事,虽非有真事,但因“间出醉笔,挥洒胸臆”(卢见曾《序》),也被人们认为是“特为才人吐气”(沈德潜《题词》)之作“,亦快人心之论也”(梁廷柟语)。可见他们创作传奇常常是借以抒发自己的胸臆,这与吴敬梓的戏曲创作思想是一致的。
其次,吴敬梓虽然在《序》中表明文人创作传奇的原动力是“抑郁无聊,块磊之气”,但没有明确的意识把戏剧当作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艺术手段。这样一来,吴敬梓在《玉剑缘传奇序》中表露了另一个重要戏曲思想 :戏剧作品不如诸子百家。对多以男女情爱为题材的情形,颇有微词 :“南北曲多言男女之私心,雕镂毚刻,畅所欲言,而后丝奋肉飞,令观者惊心骇目。”吴敬梓对明末清初,传奇创作“十部传奇九相思”的局面,并无好感。自然他对《玉剑缘》沿袭男女之事敷演成剧,并不十分认同,说“[私盟]一出,几于郑人之音矣”.[私盟]一出,词虽是“沁人心脾”,但只是“多言男女之私心,雕镂毚刻,畅所欲言”,所以被吴敬梓认为是“郑人之音”.所谓“郑人之音”,是借用《论语?卫灵公》中“郑声淫”的论断。其所谓的“子衿佻达之风”,则取自《诗经?子衿》。
这种文艺思想,在近年来重新被世人发现的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中有充分表露。在《诗说》中吴敬梓转引《毛诗?小序》、孔颖达疏、程颐《程氏经说·诗解》三段文字,对《子衿》篇进行了评价。吴敬梓转引诸文解读《子衿》之说基本遵循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原则,大体上遵从了正统的儒学观点。
如果吴敬梓这一文艺思想在《诗说》中还有些隐晦,那么读了欧阳修《诗本义》对《子衿》的解读评析,就不难理解吴敬梓“羽翼圣学”,“方立言以垂于后”的思想内涵。欧阳修在《诗本义》卷四中云 :“《子衿》,据《序》但刺郑人学校不修尔。郑以学子在学中,有留者,有去者。《毛传》又以‘嗣’为‘习',谓习诗乐,又以’一日不见,如三月‘,谓礼乐不可一日而废。
苟如其说,则学校修而不废,其有去者,犹有居者,则劝其来学。然则,诗人复何所刺哉?郑谓’子宁不嗣音‘为责其忘己则是矣。据三章皆是学校废而生徒分散,朋友不复群居,不相见而思之辞尔。’挑达城阙‘间,日遨游无度者也。”(据康熙丙辰年刻《通志堂解经》)有学者对吴敬梓的经学思想进行总结说,“吴敬梓治《诗》,虽然宗主毛传,但能于毛、郑之外,间采今文三家,对朱《传》也有所取舍,其标准在于’醇正可传‘,符合孔子的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的观念以及毛《序》所提出的’经夫妇、成孝敬、原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正是缘于此,吴敬梓在《玉剑缘传奇序》中才会以充分肯定李本宣“勤奋治经”的态度,来消解“多言男女之私心”爱情剧所带来的“郑人之音”、“子衿佻达之风”的消极影响。事实上,这位秉承家学渊源,饱受儒学思想浸染和熏陶的小说家,在头脑中无处不留有儒家传统思想和印迹。他在《遗园》诗中就流露了“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治生儒者事,谋道古人心”的拳拳振继家声的志愿。
一位极力主张“醇正可传”儒学传统的饱学之士,男女情事题材自然难投其意。对《玉剑缘》传奇男女情爱题材颇有微词的同时,吴敬梓本人坚守文学创作不滥涉情事的圭臬。吴敬梓创作《外史》后曾自鸣得意“自言’聘娘丰若有肌,柔若无骨‘二语而外,无一字稍涉亵狎,俾闺人亦可流览”(金和《〈儒林外史〉跋》)。在这一点上,吴敬梓或多或少受颜、李学派的影响。颜元、李塨在妇女的态度上比较保守,他们一方面承认男女之情是“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存人编》卷一),但又极为重视三纲五常,要“修道立教”,“使家喻户晓之”(《颜氏学记》卷五)。李塨还主张“作禁止妇女入庙焚香、当街看戏示”(《恕谷年谱》卷四)。事实上,《外史》因为反映社会生活面之深广为其后的小说评论家所极力称道,但小说唯独没有涉及男女情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吴敬梓的“一片婆心”,是对明末“主情说”泛滥后的反拨,反映在戏曲创作的思想上即是对“治曲”的另眼相待。
二
《玉剑缘传奇序》主要从戏曲创作动机和题材选择两个角度表明了吴敬梓的戏曲思想,此外也简单涉及到了人物刻画、语言艺术等方面的问题。这些观点对于研究吴敬梓的文艺思想弥足珍贵。事实上《,外史》中很多戏曲场景的描写和戏曲人物的塑造,无不浸透着作者对戏曲的态度和看法,对戏曲演员的态度集中体现了其戏曲思想,是对《序》中所表露出的戏曲思想的重要补充和延展。
《外史》中,鲍文卿就是作者极力塑造的一个正面戏曲演员形象。他对埋首制艺、久困场屋的老秀才倪霜峰的极力周济,对继子鲍廷玺的厚待优养,对舞弊考生的宽待仁厚,都体现了他待人厚道、为人正直的品质。鲍文卿在与向鼎交往过程中体现出的轻财重义、正直无私的品质也为作者看重敬仰。此外,鲍文卿对“斯文”的敬重和尊卑等级的恪守,也得到了吴敬梓的充分渲染。作者极力塑造这样一位穿行于儒林群丑之间品行高洁的戏曲演员,目的何在?卧闲草堂评本在其评语中作了揭示 :“鲍文卿之做戏子,乃其祖父相传之世业,文卿溷迹戏行中,而矫矫自好,不愧其为端人正士,虽做戏子庸何伤?天下何尝不有士大夫而身为戏子之所为者?则名戏而实儒也。”这段评语可谓洞穿了吴敬梓塑造鲍文卿形象的真实意图。除此之外,尊崇德行而忽略身份的品评人物的做法,也显露出吴敬梓对戏曲演员的态度。
这种对戏子的态度,源于作者与戏伶的接触和对戏曲艺术的熟悉与喜爱。吴敬梓“生小性情爱吟弄,红牙学歌类薛谭”(金两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从小就喜爱戏剧艺术。青年时期漫游秦淮,更是“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 ;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词·庚戌除夕客中》)。特别是遭遇屡试不第、父母辞世、族人夺产的接连不幸后,吴敬梓为了背叛礼法世俗和蔑视宗法制度,他索性沉湎于声色之乐。在这段时期里,一掷千金,过着“老伶小蛮共卧起,放达不羁如痴憨”的生活。中年家业衰败,被迫移居金陵,但依然“寄闲情于丝竹,消壮怀于风尘”,“妙曲唱于旗亭,绝调歌于郢市”(《文木山房集·移家赋》)。
青壮年时期的“放荡”生活,使吴敬梓对出身下层的歌儿舞女、优伶戏子的人生遭遇有了更加深切的了解,与戏曲演员的交往使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戏曲思想,其中也包括对戏曲演员的态度。他甚至在治业之余,曾象薛谭从秦青学歌那样,亲手执红牙板拍曲按歌。这种情趣到他中年时,由于科考失利,世人轻视的外界刺激,吴敬梓更是沉湎于歌舞声色。“有时干脆把演员歌女一齐招来,就在家中或清唱或演出,还宴请同好友朋饮洒听戏,一时满堂腰鼓,男女演员,浅斟低唱,喧闹之声,时闻于外。有时甚至留下演员歌女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豪兴不衰。”(P129)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诗中说 :“一朝愤激谋作达,左马真 右妠恣荒耽。明月满堂腰鼓闹,花光冉冉柳鬖鬖。
秃衿醉拥奴童卧,泥沙一掷金一担。……香词唱满吴儿口,旗亭法曲传江潭。以兹重困弟不悔,闭门嚄唶长醺酣。”金两铭诗 :“迩来愤激恣豪侈,千金一掷买醉酣。老伶少蛮共卧起,放达不羁如痴憨。”
乾隆七年(1742),吴敬梓花朝夕与八十七岁歌手王宁仲参加城北市民晚会,随后作《老伶行--赠八十七叟王宁仲》。这篇歌行中,这位年少时就技震宫廷的优伶 :“宫女私惊声绕梁,侍臣共见颜如赭。
君王亲顾赐缠头,中使携来宠渥优。”在晚年落魄后仍受到作者的尊重,被作者置于文人学士之上,“才人多少凌云赋,白首何曾献至尊”,甚至在歌行之尾还用“秦淮流水,钟山明月”喻其歌声之永恒。这种与伶工的纯真友谊正是平日吴敬梓与歌儿舞女、戏子优伶交往的真实写照 :“别有何戡白首,车子青春。
红红小妓,黑黑故人。寄闲情于丝竹,消壮怀于风尘。”(按 :何戡、车子是三国名歌手 ;红红、黑黑是唐时名歌手)这些都可以看出吴敬梓对戏曲、歌舞艺人的亲近和喜爱。
如果说与优伶的亲密交往和对戏曲的喜爱,还只是吴敬梓风流自适,鄙弃世俗,甚至是归隐理想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对有德有艺的戏曲演员的尊重,则是他内心深处人格理想和民主启蒙思想的直接体现,这些观念和思想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三
吴敬梓戏曲思想中有两个声音在讲话,一个属于现实生活层面,另一个属于深层观念层面。吴敬梓蔑视世俗、反叛宗法制度,寄情于声色之娱,他的生活是玩世不恭,洒脱寄形的,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儒学大家的后继之孙,儒学家承与从小至老的治经经历不可能使吴敬梓脱离中国封建思想的主流。正是这样的生活经历和人生信仰,使吴敬梓对戏曲的态度和观点也产生了表层行为和深层意识之间的矛盾。
矛盾之一 :治曲与治经二者关系的矛盾与调和。在《玉剑缘传奇序》中,吴敬梓对友人李蘧门传奇情节的婉曲,人物的多姿多予褒奖,可见他并不反对文人治曲。审视作者的人生历程,吴敬梓平生喜爱戏曲,喜爱结交戏曲演员,前文已有论述,而他的好友中也不乏喜好戏曲、度曲填辞的文人儒生。金兆燕就是其中一位,他是敏轩的挚友,其父金榘更是敬梓平生好友,兆燕本人是吴敬梓长子吴烺的儿女亲家,据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记载,金兆燕“工诗词,尤精元人散曲”,在卢见曾幕中居近十载,“凡园亭集联及大戏词曲,皆出其手”,曾创作过传奇《旗亭记》、《婴儿幻》二部。幕主卢见曾,字抱孙,号雅雨山人,曾两任两淮转运使,雅望好客,“筑苏亭于使署,日与诗人相酹咏”(《扬州画舫录》卷十),吴敬梓晚年曾作客卢见曾幕中,与卢有诗歌唱和,卢本人就喜好戏曲,金兆燕居于卢幕中时,“大戏词曲,皆出其手”,可知卢见曾幕中丝竹不断,家班演戏不绝。敏轩的另一至交是程廷祚,程是颜李学派传人,是敏轩三十三岁移居南京时所识,为其后半生的精神师友。程也曾作《莲花岛》传奇,以寄建立功业之宏愿。吴敬梓的这些雅好戏曲的友人,作者并未因为他们创作戏曲而产生交往的隔阂,反而对戏曲独钟的共同爱好,成为他们谈论经吟诗唱和之余最好的娱乐方式和情感交流的纽带。
然而一旦关涉到文人士夫安身立命、不朽于世的严肃命题,吴敬梓就明敏地摆出经学家的面孔,宣言“立言以垂于后”.在《玉剑缘传奇序》中为李本宣辩解,打出的牌子就是治经,“然吾友二十年来勤治诸经,羽翼圣学,穿穴百家,方立言以垂于后,岂区区于此剧乎!”企图以李本宣“勤治诸经,羽翼”圣学来消解人们产生李蘧门专工情事,沉湎治曲的“不良”影响,更不可“以此想见李子之风流”.儒生学士在处理治经与治曲的关系上,自宋元始,并没有改变治经是正途,治曲是旁业的偏见,即使是在元、明两次文人治曲的高潮中,也未得到颠覆。文人广泛参与治曲并未改变戏曲在儒生士绅心目中的地位和“喜而薄之”的社会风气。在吴敬梓的精神深处,治曲是旁业,治经是正途的思想根深蒂固。戏曲是治经之余的戏娱所在,是文人士大夫附庸风雅,以消除心中块磊的平台,而“治经”则是文人儒生通过“立言”实现人生不朽的重要路径,这也是读书人区别于贩夫走卒、俗子凡夫的精神优势之所在,失去这个根本的立世法则,就枉为儒生文士。
矛盾之二 :对演员人格的尊重和对演员职业的不认同。一方面,他乐于亲近戏曲,亲近艺伶,另一方面又主张“勿为沦为伶人”(《文木山房诗说?简兮》),二者的反差,十分真实地反映出吴敬梓对戏曲的真实看法 :儒生可以狎伶赏戏,却不可沦为伶辈。在思想深处视戏剧为贱役,戏子为“贱人”(鲍文卿自称)的传统思想,并没有在吴敬梓这里得到改变。在《外史》中,吴敬梓极力渲染鲍文卿这位老艺人恪守“戏子”身份,敬重“斯文”的德行操守,不能不说是文木先生这种意识的真实流露。
在文人涉戏问题上,吴敬梓也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亲近归亲近,一旦文人士夫无缘仕进,若要沦为伶途或通过“戏而优则仕”的方式获取功名,他则坚决反对。他在《文木山房诗说?简兮》中,驳朱传“贤者不得志而仕于伶官”时说 :“余反复读《简兮》之诗,而叹《硕人》之所见浅也。士君子得志则大行,不得志则龙蛇,……何必以仕为?”“士君子得志则大行,不得志则龙蛇”,即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注解,在这里吴敬梓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 “:士君子”可以与歌儿舞女、戏子伶工相交相娱,但决不可“不得志而仕于伶官”,沦为倡伶之流。
吴敬梓在文人治曲和对伶人态度上的矛盾,源于思想深处的正统儒学观念,这些观念在受到当时社会风气和时代意识的影响的同时,也与其儒学世家的家承有关。吴敬梓出自安徽全椒的读耕世家,“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曾祖吴国对更是清代有名的八股文大家,“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文木山房集序》),对于家学渊源,吴敬梓多次表达要承继家学,振继家声 :“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治生儒者事,谋道古人心”(《遗园》),“家世科名,康了惟闻毷氉声”(《减字木兰花?庚除夕客中》)。此外,他本人“晚年亦好治经”,曾作有《诗说》若干卷,还申言“此人生立命处也”(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可见他对儒家经典的重视。所以人们在肯定《儒林外史》进步思想的同时对体现在小说之中的儒学思想进行指讁“,吴敬梓所吹捧的真儒,实际上是封建帝王提倡的孔孟之道的化身”,即使是作为全书的最大事件和高潮“,也是儒家思想的集中表现”[5].
四
《儒林外史》以其高超的文学艺术成就称于世,也因深刻的思想性而名于今。吴敬梓有着初步的民主思想的启蒙,但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自然有其思想上的落后性和不足,诚如他不能为绝意科考又看破世情的儒生找到真正出路一样,吴敬梓的思想之不足,在他的戏曲思想上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
陈汝衡先生的《吴敬梓传》评《玉剑缘传奇序》中吴敬梓为友人李本宣竭力开脱时说 :“这就表明我们传主的文艺观还是贬低戏剧作家和作品,认为治经才是’羽翼圣学‘.传主的时代局限性,从这些地方不是看得一清二楚么?”[6](P102)陈先生的说法,指出了吴敬梓戏曲(戏剧)思想的局限。据一篇《玉剑缘传奇序》短文评说吴敬梓的“文艺观还是贬低戏剧作家和作品”,很难有说服力。但对吴敬梓戏曲思想局限性的判断,却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在评判一个作家,特别是像吴敬梓这样的伟大小说家时,更应做到不虚美,不掩“恶”.吴敬梓的戏曲思想是综合的、复杂的,是其文艺思想真实的表达和重要组成部分。了解其戏曲思想的优长和缺失,有助于全面深刻地分析评价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及吴敬梓的创作思想。
参考文献 :
[1]陈美林。吴敬梓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陈美林。试论“思想家的小说”的作者吴敬梓的思想[J].东南大学学报,2002(2)。
[3]范 宁。儒 林 外 史 中 的 伦 理 思 想 问 题[J].学 习 与 思考,1982(1)。
[4]李汉秋。儒林外史泰伯祠大祭和儒家思想初探[J].江淮论坛,198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