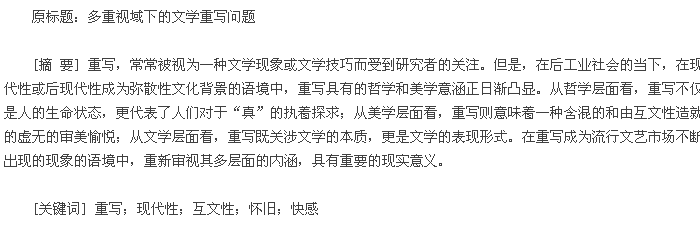
重写,这是一个并不受人——尤其是作家们——欢迎的字眼。在事事、处处讲求创新的当下,对一个作家最大的羞辱,莫过于指出他的得意之作“重写”了某部早已存在的经典作品,或者他自鸣得意的风格“重写”了某位已故作家的神韵。然而,重写,无论是作为一种技巧,抑或是一种文学形态,却超越历史、跨越时空,鲜活地行走在文学的殿堂之中。
正如佛克马所言:“只需回顾一下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传统,就可以发现,所谓重写(rewriting)并不是什么新时尚。”
且不论“三国”、“水浒”、“西游”在成书之前就已经具有了大致的故事轮廓,就以在阅读界和电影界都炙手可热的作家李碧华的创作来说,《青蛇》、《诱僧》、《潘金莲的前世今生》等一系列所谓“故事新编”小说都可以找到“前文本”的存在。《尤利西斯》重写了《奥赛罗》,《绣襦记》重写了《李娃传》,《月下小景》重写了《法苑珠林》,《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重写了《义妖传》,《人间》又重写了《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声势浩大的新历史创作潮流则把整个中国历史作为重写的对象,而消费文化鼓动下的经典翻拍和恶搞创作现象更是成为当今流行文艺思潮中不容小觑的存在。无论在经典文学体系,还是在流行文艺市场,诸如此类的重写实践不胜枚举,以至于哈罗德 布鲁姆早在《西方正典》中就不得不承认“伟大的作品不是重写即为修正”,“一首诗、一部戏剧或一部小说无论多么急于直接表现社会关怀,它都必然是由前人作品催生出来的”。
“道沿圣而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无论是作为“道”的最终产物,还是“圣”体认“道”的中介,“文”都包蕴着人们对于最终大道的认知,而此处所谓的“道”,在本质上乃是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这就是文之所以能“与天地并生”的原因所在。由于蕴藏着人对于自然宇宙的思索,文学就不仅仅是文字的累积,而更是人类思考的姿态。作为一种超越技巧层面的文学样态,重写同样具有深刻的意涵。
一
从哲学层面来说,重写是人类生命的一种状态。
关于生命,柏拉图曾经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于古希腊祭司观点的赞同,即人的灵魂不朽。在《美诺篇》中,柏拉图说:“既然灵魂是不朽的,重生过多次,已经在这里和世界各地见过所有事物,那么它已经学会了这些事物。如果灵魂能把关于美德的知识,以及其他曾经拥有过的知识回忆起来,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对此感到惊讶。一切自然物都是同类的,灵魂已经学会一切事物,所以当人回忆起某种知识的时候,用日常语言说,他学会了一种知识的时候,那么没有理由说他不能发现其他所有知识,只要他持之以恒地探索,从不懈怠,因为探索和学习实际上不是别的,而只不过是回忆罢了。”
生命在此世的学习、探索进程,在本质上乃是回忆。
因为人从理想的天堂跌落之后,回望就成了一种固执的姿态,此生的所作所为,莫不是在重蹈旧辙,只不过这旧辙是完美和圆满,此生的努力都是在尽可能靠近前世的路途。因此,对于理想世界的重写,成了人生在世不可不承担的重责,也成了此世永难实现的创痛。因为怀想而伤痛,因为伤痛而难以抑制回望的姿态;因为难以抑制的回望,人不得不一再重写前世的辉煌。诚如刘小枫所言,人是欠然的存在,因为欠然而苦痛,而重写连接了此在与彼岸,将彼岸的理想之光引入暗昧的此在,无疑是拯救自身的一条捷径。尤其是在当下,在资本主义和机械复制剥蚀了一切自然与神圣之物的光晕之后,在人类普遍葆有一种“流离感”的现代性语境下,重写更是与人的存在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现代性的时间指向是单向的、永不止息地前行的。在现代社会,人们不由自主地被卷进程式化流水作业的工序中,衡量时间的指标不再是个人的喜怒哀乐或者春华秋实的自然絮语,而是量化的工作成果和细化的评价体系。在现代性的时间语境中,人失去了最本真的存在意识,被切断了与自然宇宙的内在联系,成为整个社会进程中不值一提的细小部件,因而感到一种渺小的压迫。失去自我,这是人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最大窘境。
未来是可预见的,因而也是绝望的;当下是迅疾、无聊,也是难以挣脱的。因此,留给现代人的只有恒常未变的过去、历史和记忆,“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波德莱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只有在昏黄的历史中,人才能找到田园牧歌和诗意的生存,才能意识到“人”的真正意义。因此,怀旧成为这个时代消费文化中不可忽视的潮流,老照片、老课文、老歌、老电影以及复古的时装设计,都流露着人们对于往昔岁月的追怀。
将记忆移植到现实生活,以影像和实践的形式重演过去的风华,这正是消费文化中最核心的“重写”。
利奥塔说,“‘重写’这一词汇的模糊之处也同样萦绕在现代性与时间的关系上”。现代性的时间指向未来,重写的时间指向过去,现代人正是在这两个相悖的向量中确定着当下的意义和自身的实存性。失去了所谓“现代性”,人仍能在历史中确立存在的坐标系;失去了“重写”,人就会沦落为冰冷的符码,依附于庞大的现代性机器而失去自我。在这种意义上,重写是具有某些后现代特征的实践,通过这一行为,人们反抗着现代性的一体化和模式化,在宏大的大写历史中构筑个人的私密世界。
从哲学层面来说,重写同时也是人对于“真”的执着探索。
由于主体性的存在,再加上诸多客观性的制约,人总是无法接近纯正的“真”。历史的单向度流逝,更使得人们对于“真”的探求形同向壁借光。
然而,重写使得这种逆向的历史呈现成为可能。通过重写,人们可以随意组合构成历史的要素,探究不同要素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和价值;通过重写,人们还可以排除造成历史扭曲的诸多制约因素,在某种程度还原“真实的”历史,实现对于“真”的抵达。也就是说,重写一方面可以将人们带回历史的原点,“将时钟回拨至零重新开始,将往事一笔勾销,从而揭开新年代和新时期的序幕”,在万物方生未生之时寻求新的出发点和可能,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置换的方式呈现不同要素在造就历史的场域中所处的位置,以弗洛伊德“彻底研究”(Dur-charbeitung)的形式“研究一种被事件或事件的意义所掩盖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仅被以往的偏见所掩盖,而且还会被未来的方方面面所掩盖”。无论是回到原点还是“彻底研究”,重写带给人的都是一种“掌握”真实的快感,满足了人对于“真”的探求。
二
从美学层面来讲,重写意味着一种含混的愉悦。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人们是在现代性与重写造就的两个相悖时间向量中确定着当下的存在。在此处,重写其实不仅仅是单纯的历史重现,更是一种混合历史与当下的错综状态。经由重写,历史进入了当代人的生活,而重写这一动作却受制于当代的文化氛围。通过当代意识形态的折射,历史已经不可能获得纯粹的展现,而不得不渗透了当代的社会文化、权力意识以及重写者的人生经验,最终成为视域融合的产物:较之现代性,重写因为加入了田园牧歌般的历史意蕴而有了后现代的反抗意义;较之原初的历史,重写又因为渗入了现代性的因子而破坏了历史的圆融统一。所以,一方面是“前进和后退的双重姿态”造成的时间张力,一方面是历史与人生重合的审美张力,张力结构所造成的是一种混杂的美学体味:无论是重写者还是重写的检阅者,既能从中辨识出历史的唯美,又能体认到现实的错愕;既是历史现实化的想象突破,又是现实历史化的此在超拔,由此造成的是一种“熟悉的陌生人”的审美愉悦——正如佛克马所指出的:“美感经验通常是由含混性或刺激而产生的。”
无论是新历史写作还是流行文艺市场不断出现的经典翻拍、历史演义作品,都借由历史与现实的比照或直接拼接制造审美噱头,吸引读者/观众的眼球。例如莫言和王树增早年合作创作的话剧《霸王别姬》,便借助史书叙事的缝隙展开演绎,将原本轰轰烈烈的英雄美人故事改编成为项羽、吕雉和虞姬之间错综复杂、糅合了情欲与权力斗争的三角恋情。历史的空白角落为当代人的审美观照提供了足够广大的意义生成空间,在与历史的若即若离之中,现代性的审美意识便与经典的历史叙述顺利接榫,制造出既古典又现代的审美愉悦。
从美学层面来讲,重写还意味着一种由互文造成的后现代虚无愉悦。
无论是现实历史化—历史现实化的社会重写实践,抑或是经典文本当下讲述的文学重写实践,重写都关联到两个紧密依存的场域:此文本/生活与彼文本/历史。新生成的文本(此处的文本意指泛化的文本,即一切社会实践的成果)时刻提醒着旧文本的存在,而旧文本也很有可能是更旧文本的重写,这种关联和指向是无始无终的,最终将所有文本串联起来,构成一个无边无垠的互文网络。所谓互文,正是指这种大量文本互相勾连阐释注解的状态。在经典时代,文本通常具有自足的意义体系,具有独立的地位,因而能获得人们的敬畏。重写的出现,加上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推动,经典文本或者叙事的封闭性被打破,互文造成的文本重合矩阵,使得原本整一性的意义被散播到数个甚至不可胜数的文本和叙述之中,庞大的意义丰碑被肢解,随之瓦解的还有整体叙事的权威性。在延异和消解的过程中,重写者和检阅者都享受到征服权威的快感,在加冕和脱冕的狂欢进程中树立了主体的地位。叶兆言的长篇小说《后羿: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的神话》以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的神话为底本,却没有塑造出传说中高大全的后羿和背情受罚的嫦娥,而是将后羿刻画成为母系权威引导、推动下不断蜕变的具有浓重恋母情结的孩童,嫦娥则具有了圣母加贤后的光环。神话与新文本的不断重叠牵连所造成的反讽结构,完全消解了传承至今的神话叙事,取而代之的是当代审美心理的强势登场。
三
从文学层面来看,重写既关涉到文学的本质,亦是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文学本质的诸多观点中,童年记忆说一直是不容忽视的。这种观点认为,作家的文学创作与童年记忆密切相关,每一部作品都是作家童年经历的再现。如果我们联系到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创伤转移观点,就可以清晰地勾勒出这种观点的大致轮廓:作家在童年的经历作为一种压抑长期存在于潜意识中,由此造成巨大的焦虑,为了合法而稳妥的转移这种焦虑,作家通过白日梦的形式将这些经历灌输在文字当中,于是就产生了文学。抛开这种观点是否具有普适性不谈,童年记忆说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作家乐于从事自传性书写的原因——何况大多数作家的处女作都是童年记忆的展现。即使童年记忆说有一定偏颇性,但下面的观点却不那么轻易被驳倒:文学作品都是作家对于所见所闻的社会生活的改造。因此,佛克马才认为,应该将文学看作是“陈年旧事的重新书写,看作对科学结果、报刊文章以及我们日常使用的陈词滥调的重写”。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经区分了“以我观物”与“以物观物”这两种视点,“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其实,无论是“以我观物”还是“以物观物”,所看之物都不再是物本身,而是对于物的重写。除了生理准确度的因素之外,个人的经历和文化修养也都是导致物变形的原因。所以,文学不可能如实地展现这个世界,而只能是对世界的重写。
此外,就文学使用的语言来说,也不存在原创的问题。诚如佛克马所言:“文学的材料就是语言,但并非泛泛的语言,而是使用过的语言,曾经使用过的语言被重新型塑为文学,这就产生了某些效果。”
语言是有限的,如何运用这有限的语言创造出全新的感官效果,这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每种语言,每个单词,都承载着不同人的不同记忆,文学正是借助于语言的这种混杂意义,通过组配唤起了读者的审美想象,也即是重写了每一位读者的文字记忆,因此达到了共鸣的艺术效果。
重写同时也是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表现技巧来说,重写是对既有文学作品或者叙事文本的改编,这种改编体现在人物、情节、结构、手法等诸多方面;从文学类型来说,重写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古已有之且绵延不绝的一种类型。在中国文学史上,历史文学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四大名着中,至少有三部是对历史的变相书写,而历史演义小说更是一直影响到了当代文学的格局。众多的重写型文学已经造就了重写文学这一独特门类的产生,以至于有研究者称“中国小说史应是关于中国小说的创作史及其重写史的总和”。如果考虑到诗歌和散文在用词和主题上的互相借鉴,这一论断基本可以推而广之:中国文学史应该是关于中国文学的创作史及其重写史的总和。
重写虽然经常被视为一种文学现象或文学技法,却具有着深厚的哲学和美学意涵。尤其在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成为弥散性的背景文化的当下,重写更是具有了还乡或者田园牧歌的意味,成为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人们自我抚慰的一种方式。重写之所以会成为流行文艺较为常用的手段,也在于重写勾连起了历史与现实的两极,使身处当下社会的“单面人”有了借助怀旧的光晕而充实审美享受的机会,进而得以确认自己在生活序列中的存在感。也正是这多层面的意涵,吸引着作家、艺术家将创作的眼光投向过去、投向经典,在日新月异的时代节奏中回溯古老的故事,也吸引着观众/读者在多次的审美体验之后仍能从旧话语中体认到常新的况味。
[参考文献]
[1] 佛克马. 中国与欧洲传统中的重写方式 [J]. 范智红, 译. 文学评论, 1999 (6): 144-149.
[2] 哈罗德 布鲁姆. 西方正典 [M]. 江宁康,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3] 刘勰. 文心雕龙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4] 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 第一卷 [M]. 王晓朝,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5] 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 [M]. 郭宏安,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6] J-F. 利奥塔. 重写现代性 [J]. 阿黛, 译. 国外社会科学, 1996(2): 65-69.
[7] 生安锋. 文学的重写、经典重构与文化参与——杜威 佛克马教授访谈录 [J]. 文艺研究, 2006 (5): 62-70.
[8] 王国维. 人间词话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9] 黄大宏. 唐代小说重写研究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