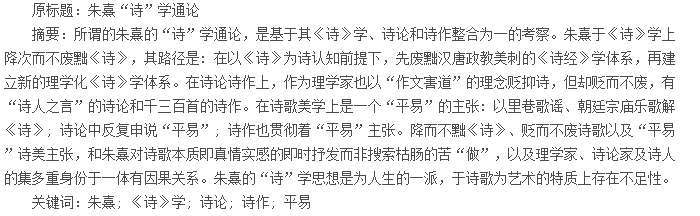
本文所谓朱熹的“诗”学,包括他的《诗》学、诗论、诗作及贯穿三者的诗歌美学“平易”主张,是整合三者并揭橥其诗歌美学主张的研究。朱熹“四书”学体系的建立是儒家思想史上的革命性事件,其实质是对汉以来千年“五经”地位的降次。
这一降次行动是他怀疑进而废黜汉唐“五经”学的结果,如他以《诗》为里巷歌谣、朝廷宗庙的乐歌而不是汉唐经学体系化的政教美刺工具。但是,朱熹对汉唐《诗经》学的由疑而黜并不代表他对《诗》的废黜,因为他在对《诗》篇诗歌本体认识的基础上,又新建了理学化的《诗》学体系。朱熹于《诗经》的思路也适用于他对诗的态度,作为理学家,他和其他理学家一样也是贬抑诗的,但他却又是贬而不废的,这一点表现在他既有诗人的诗论又有千三百首诗的创作上。诗歌美学风格上,朱熹整体是一个“平易”的主张,《诗》三百篇的里巷歌谣、朝廷宗庙的乐歌指向了“平易”,其反复于诗的申说也是“平易”,其诗歌创作的以古体为主则是“平易”主张的实践。
一、降而不黜《诗》
儒家“六经”之说始于《庄子》,其《天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1](P.531)公元前136年,汉武帝设“五经”博士,以行政干预的手段奠定了《五经》千年儒家经典的尊贵地位。公元1190年,朱熹合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以之为“《六经》之阶梯”[2](P.2629)。朱熹“四书”、“五经”的新儒家典籍体系,实质上已是对“五经”的降次。
朱熹降次“五经”,作为“五经”之一的《诗经》当然在被降次之列。就《诗经》来说,朱熹尽管以其为诗而客观上降低了其儒家思想的承载价值,但他并没有将其剔除新儒学的理学体系,而是怀疑汉唐旧《诗经》学并加以辨正后,将其化为新的理学《诗》学。
(一)对汉唐《诗经》学体系的由疑而废
朱熹降次《诗经》,基本表现是其对千年汉唐《诗经》学的怀疑进而废黜。欲亡其木先斩其根,就汉唐《诗经》学来说,《诗经》编纂上的“孔子删《诗》”说和诗篇内容上的“思无邪”说,无疑是《诗经》作为圣经的两块基石。孔子“删诗”说的提出者是司马迁,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3](P.1936)后为班固、郑玄等大儒所赞同,遂为千年不易之论。
但朱熹一句“那曾见得圣人执笔删那个,存这个!也只得就相传上说去”[2](P.2056),以传言之不可信目孔子“删诗”说,无疑是在动摇汉唐《诗经》学的根本。和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相比,《论语·为政》的“思无邪”说则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因为它出自孔子之口,但朱熹一句轻描淡写的“不是一部诗皆‘思无邪’”[2](P.2056),就颠覆了诗篇思想内容纯正的权威。朱熹认为就《诗》三百篇的内容来说,不是全部“无邪”而是部分“有邪”:“林子武问‘《诗》者,中声之所止’。曰:‘这只是正《风》《雅》《颂》是中声,那变《风》不是。……今但去读看,便自有那轻薄底意思在了。如韩愈说数句,‘其声浮且淫’之类,这正是如此。’”[2](P.2068)朱熹以“思有邪”论《诗》,显然是在和圣人唱对台戏,尽管他能够以“有邪”之诗的作用在于“惩创人之逸志”来自圆其说而维护了圣人的尊严。但朱熹的目标不在圣人而在于汉唐《诗经》学。朱熹打击汉唐旧《诗经》学,炮火集中在了《毛诗序》上。《毛诗序》有《大序》、《小序》之分,其内容在于指出诗篇主旨,代表汉唐《诗经》学以美刺解《诗》的体系。汉唐学者为抬高其《诗经》学地位,有《大序》为孔子或者孔子弟子子夏所作之说。朱熹说:“诗《大序》亦只是后人作,其间有病句。”[2](P.2072)以“有病句”这样的低级错误,直接否定了圣人所作的谬说,并激烈批评曰:“《诗序》作,而观《诗》者不知《诗》意!”[2](P.2074)这无疑是在说,《诗序》于诗篇主题的理解,是偏离甚远的谬以千里!朱熹的疑《序》并不孤独,其前郑樵已开先河,据朱熹说:“《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2](P.2076)《诗序》非圣人作,《诗序》不足信,朱熹这里无疑已经否定了《诗序》对《诗经》的存在价值,而这一认识的直接结果是他的《诗集传》的废黜《诗序》以解《诗》:“诗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于汉儒,反乱《诗》本意。且只将四字成句底诗读,却自分晓。
见作《诗集传》,待取诗令编排放前面,驱逐过后面,自作一处。”[2](P.2074)鉴于《毛序》对《诗》的负面价值太大,朱熹的《诗集传》不再以《毛序》为《诗经》有机组成部分,而是另行处置,专门以《诗序辨说》一书辨析《序》说之谬:“作《诗传》,遂成《诗序辨说》一册,其他缪戾,辨之颇详。”[2](P.2079)由于《毛序》是汉唐《诗经》学的标志,朱熹《诗集传》的废黜《毛序》,其实质也就是对汉唐《诗经》 学内容的废黜。何者为汉唐《诗经》学内容?美刺政教而已。在朱熹降而不黜《诗》的中间有一个环节,也就是他的视《诗》是诗。这是他以“毛、郑,所谓山东老学究”[2](P.2089)评论汉唐毛郑美刺政教《诗经》学的基础。正是基于视《诗》是诗,所以朱熹目光犀利地发现并指出,欧阳修于三百篇本义的有所发明在于他的文学功底:“意欧阳会文章,故诗意得之亦多。”[2](P.2089)朱熹视《诗》是诗,具体又有里巷歌谣、朝廷宗庙乐歌之分: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歌乐之词。[4](P.105)情感表达是《诗》三百篇第一位的东西,是本、是体,政教美刺是第二位的,是末、是用。但是,汉唐《诗经》学却本末倒置,说什么“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5](P.16-17)。总之,因为朱熹视《诗》是诗,故而其《诗》学逻辑是:诗人情感即时直接的抒发并非篇篇具有美刺动机,所以汉唐《诗经》学的政教美刺内容体系是应该废黜的不科学体系;《诗》篇意义的含混性、能指的多样性、功用的可择取性,为新的理学化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附着的母体。
(二)建立新的理学《诗经》学体系
朱熹的不黜《诗》,表现在他在废黜汉唐《诗经》学政教美刺内容后,建立新的理学《诗经》学体系上。朱熹的新理学《诗经》学体系,可以划分两大板块展开论析:一是所谓的正《风》、正《雅》及三《颂》之篇,再是变《风》、变《雅》之篇。
前者以内容的正价值被朱熹做了理学解释,后者则体现朱熹劝惩以敦风化的诗歌功用观。所谓正《风》,即二《南》的二十五诗篇,朱熹结合《大学》对其作了周文王政治教化效用的解释,将诗篇分类比附到《大学》之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上:《周南》前五篇的《关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等,体现了“文王之修身齐家之效”[6](P.411)[《桃夭》、《兔罝》、《芣苢》体现了“家齐而国治之效”[6](P.411);《汉广》、《汝坟》,则见“天下已有可平之渐”[6](P.411);《鹊巢》至《采萍》“见当时国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6](P.420),《甘棠》以下则“见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国君能修之家以及其国也。其辞惟无及于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6](P.420);周文王政治教化所达成的最终境界,朱熹说是“其民皡皡而不知为之者”[6](P.420)的天下从化却浑然不知的止于至善。正《雅》又分正小《雅》和正大《雅》:前者朱熹以儒家伦常主要是君臣、兄弟朋友之伦解之;后者朱熹说是朝廷之上的受厘陈戒之辞以发先王之德[6](P.543)。正小《雅》,朱熹认为以君臣伦理为内容的有《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采薇》、《出车》、《杕杜》、《蓼萧》、《湛露》和《彤弓》等。其中《鹿鸣》是溥泛适用的君臣之义;《四牡》是“劳使臣”[6](P.544);《皇皇者华》是“遣使臣”[6](P.547);《采薇》是“遣戍役”[6](P.522);《杕杜》是劳还役[6](P.557);《出车》是“劳率,故美其功”[6](P.557)之诗;《蓼萧》、《湛露》和《彤弓》则是言君主和诸侯之义。《常棣》诗写兄弟之义。《伐木》篇则以朋友之伦为内容。正大《雅》的先王之德主要是周文王之德,此外还涉及后稷、太王等,其中以文王之德为内容者有《文王》、《大明》、《思齐》、《皇矣》、《灵台》等诗。文王之德上合“天理”下得“民心”,《文王》诗的“聿修厥德。永言配命”文中的“命”,朱熹释为“天理”,说“命,天理也。……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无不合于天理”[6](P.654);《皇矣》篇诗文“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则以“帝之则”为“天理”,言文王能“不作聪明,以循天理”[6](P.668);《思齐》篇的“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闻亦式,不谏亦入”文,朱熹解为“性与天合”,“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难虽不殄绝,而光大亦无玷缺。虽事之无所前闻者,而亦无不合于法度。虽无谏诤者,而亦未尝不入于善……所谓性与天和是也”[6](P.664);朱熹还进而主张,王道政治的“循天理”,其旨归在于得民心,故而《灵台》篇“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文,朱熹解释为“文王之台,方其经度营表之际,而庶民已来作之,所以不终日而成也。虽文王心恐烦民,戒令勿亟,而民心乐之……不召而自来也”[6](P.669)。文王的“敬”德:《文王》篇的“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朱熹解为“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6](P.347),《大明》篇的“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文,朱熹解为“恭慎之貌……所谓敬也”[6](P.347)。至于三《颂》伦理学,朱熹曾曰:“《颂》之诗,何尝一言一句不说道理……里面有多少伦序,须是仔细参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穷理。”[6](P.503)朱熹变《风》变《雅》的惩戒之用思想,立足是诗篇内容的非“中和”:“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6](P.347)变《风》内容的非“中和”,朱熹说“‘发乎情,止乎礼义’,又只是说正诗,变《风》何尝止乎礼义!”[2](P.2072)并指出具体篇章曰:“《桑中》诸篇曰‘止乎礼义’,则不可。”“《桑中》有甚礼义?”[2](P.2072)若说变《风》中非“中和”之诗对于接受者的作用在于“惩”的话,朱熹则认为变《雅》主于“戒”:“皆一时贤人君子闵世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闲邪之意。”[6](P.351)变《雅》是有识之士秉持中正良心而有感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鉴戒之作,就诗篇来说:“《六月》至《何草不黄》五十八篇为变小《雅》,《民劳》至《召旻》十三篇为变大《雅》,皆康召以后作。”[6](P.344)
总之,朱熹降而不黜《诗》,废黜汉唐《诗经》学美刺政教的体系,建立新的理学化体系的根基是视《诗》是诗,即不以《诗》篇为高深难测的圣人意旨而是普通诗篇看待进而理解之,用朱熹自己的话说就是当做今人作的诗看待:“读《诗》,且只将做今人做底诗看。”[2](P.2083)甚至当做自己作的诗看待:“读《诗》正在於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诗,自然足以感发善心。”[2](P.2086)朱熹视《诗》是诗,主张将其看做今人甚至自己作的诗来看待,那么他又是怎样看待诗、古今诗人诗作的呢?他自己的诗作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二、贬而不废诗
作为一个理学家,朱熹和同时代的其他理学家一样,对诗也持贬抑态度。诗歌是文学的基本样式,贬抑文学逻辑上也包括贬抑诗歌。他们以文学(文辞)为鄙陋:“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8](P.32)以文学是道德余事:“力有馀则学文。”[8](P.80)甚至有作文“害道”、“玩物丧志”、文人为“俳优”之说[8](P.44)。具体到诗,朱熹曰:“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陷溺尔。”[2](P.3333)又曰:“近世诸公作诗费工夫,要何用?……然到极处,当自知作诗果无益。”[2](P.3333)又曰:“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第二义。”[2](P.3334)但朱熹又不像有些理学家那样完全否定诗的价值,而是持贬而不废的态度和做法,这和他对《诗经》在经典中的地位的降而不黜是同一的思维和处置模式。朱熹的不废诗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被明代文征明誉为“诗人之言”的诗论,二是亲力亲为地创作了千三百首诗并以之名家。
(一)“诗人之言”的诗论
朱熹论诗材料于《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有辑,另有明人所辑《晦庵诗话》以及今人《宋诗话全编》本《朱熹诗话》。朱熹的诗论,文征明《晦庵诗话序》的评价可谓公正之论,一曰朱熹“未始不言诗”,再曰“其所为论诗,则固诗人之言也”,指出朱熹不但论诗,而且还是很专业的诗论家。此以《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为据考察,发现朱熹论诗时间跨度大、品评诗人多且有明显的侧重。以时代顺序,朱熹品评的诗人诗作有:周代论到《关雎》诗,汉代论到乐府,汉魏论到曹操、曹丕诗,六朝论到陶渊明、谢灵运、刘琨、鲍照等诗人及其诗作,唐代论到杜甫、李白、韦应物、李隆基、韩愈、李贺、刘叉、白居易、刘禹锡、王维、孟浩然、寒山诗等,宋代论到石延年、杨亿、苏舜钦、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秦观、刘季孙(景文)、觉范、参寥、张耒、苏辙、崔鶠、潘大临、李清照、与魏玩(魏夫人)、曾文清、张栻、刘叔通、江文卿、方伯谟父子、黄子厚、徐思远、程克俊、赵昌父、徐斯远、韩仲止、刘淳叟、上官仲恭、杨廷秀诗。自周至时下,跨度两千年,品评诗人自曹操起五十余,可谓多矣。但朱熹于各代又不是均衡用力而是有侧重点的,五十位诗人中唐前诗人仅六人,可见其侧重的是唐宋诗,这也合情合理,因为中国诗歌发展到唐宋,才真正走向了它的成熟和高峰。唐宋诗中,他重点论及的是李杜诗和苏门诗人黄庭坚诗及江西诗派诗,因为它们在中国诗史上有重大影响,地位突出,任何论诗者皆不得回避,尽管可以有不同看法。朱熹的诗歌理论主张也是在评论这些诗人诗作时表达出来的,如他的多面向的诗歌风格论。
朱熹能辩证地看待诗人的诗风,并能对诗人作心灵洞悉,如他一面说陶渊明的诗“平淡出于自然”[2](P.3324),一面又说陶渊明骨子里豪放,只不过“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2](P.3325)。
李白诗以豪放着称,但朱熹却看到其也有“和缓”之处,“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如……‘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2](P.3325)朱熹还谈到了性格气质和风格的一致关系,他说唐明皇诗风的“飘逸气概”源于其性格气质的“资禀英迈”[2](P.3325),石延年的胸次极高为人豪放则导致了其诗风的“雄豪而缜密方严”[2](P.3329),李清照诗的雄风豪气,源于他们性格中乾乾刚健的大丈夫气概:“李有诗,大略云‘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云云。‘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汤武得国,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2](P.3332)性格气质和诗歌风格的关系外,朱熹还有风土人情和风格关系的理论,他说:“某尝谓气类近,风土远;气类才绝,便从风土去。且如北人居婺州,后来皆做出婺州文章,间有婺州乡谈在里面者,如吕子约辈是也。”[2](P.3335)但他认为性格气质、风土人情两者对诗歌风格的影响又不是同等的,是前者重要于后者的。朱熹还有诗人诗作的渊源论,除苏黄江西诗人的渊源外,他还具体论到了某些诗人:他说李白诗是在学《文选》,“李太白终始学《选》诗”[2](P.3326),李白的古风学陈子昂《感遇诗》,并说“多有全用他句处”[2](P.3326);他还以家学渊源论诗,说某人“是某人外甥,他家都会做诗,自有文种”[2](P.3335),又说徐思远诗较好是有家学渊源的,他是“程克俊之甥,亦是有源流”[2](P.3331)。朱熹还以虚静论创作,认为作不出好诗是因为“心里闹,不虚静之故。不虚不静故不明,不明故不识。若虚静而明,便识好物事。虽百工技艺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虚理明,所以做得来精。心里闹,如何见得”[2](P.3333)。虚静是做一切事情的必备心理状态,作诗当然也不能例外。朱熹的诗论尽管是专业的“诗人之论”,但有意无意也会露出理学的马脚,如:“人不可无戒慎恐惧底心。………韩文《斗鸡》联句云‘一喷一醒然,再接再砺乃’,谓虽困了,一以水喷之便醒。‘一喷一醒’,即所谓惧也。”[2](P.3327)这里就对“一喷一醒然,再接再砺乃”诗句做了理学“戒慎恐惧”内容的解读。朱熹尽管以学诗为第二义,但他还是给出了学诗的正确路径:“作诗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经。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苏黄以次诸家诗。”[2](P.3333)他批评学诗走了弯路者曰:“不去学好底,却只学去做那不好底。作诗不学六朝,又不学李杜,只学那峣崎底。……如近时人学山谷诗,然又不学山谷好底,只学得那山谷不好处。”[2](P.3334)这也是朱熹贬而不废诗的表现。
(二)以诗名家的创作成就
朱熹的贬而不废诗,还表现在他以诗名家,有和诗圣杜甫相当的千三百首诗的创作成果上。朱熹诗歌创作在当时已天下有名,并以此被胡铨举荐朝廷,据《鹤林玉露》甲编卷六:“胡澹庵上章荐诗人十人,朱文公与焉。”[9](P.112)他的诗在历史上也屡获好评,宋人李涂就赞其为“《三百篇》之后一人而已”[10](P.95),明人胡应麟《诗薮》则说朱熹古体诗南宋第一。今人钱穆《朱子新学案》说朱熹如果不是一个理学家,也肯定会以诗人而名垂青史。
看来,朱熹尽管贬诗,但他已确然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突出成就。朱熹的诗歌创作和他的诗论是基本一致的。在诗体方面,他创作上贯彻了提倡古体而批判今体的主张,其诗作几乎全为古体,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上文胡应麟就将其评为南宋第一。他主张诗人诗作的渊源,而他的古体诗作也有家学和师承。朱熹的父亲朱松好诗而推崇古体。朱熹自己为其老师刘子翚的诗集所作的跋文“此病翁先生少时所作《闻筝》诗也。规模意态,全是学《文选》、《乐府》诸篇,不杂近世俗体,故其气韵高古,而音节华畅”[11](P.3968)所流露的褒赞之义,不难得出他的古体诗创作会受其所敬重师尊的影响的结论。朱熹主张诗歌创作“适情”说,他的诗篇多是有感而发的即时之作,而非为做诗而做诗的苦“做”之得。朱熹的诗作可分为应酬赠答诗、感事抒怀诗、咏物写景诗、理趣理学诗等。应酬赠答诗在朱熹诗作中占了很大的比重,由于这部分诗没有多少社会价值,也多不是哲理感悟的名篇,故而影响不大。说其价值不大,也并非说这类诗一点儿积极价值也没有,其实,这类诗中的某些篇章,还是有可以称道之处的,如《雨中示魏惇夫兼怀黄子厚二首》就向读者展示了友情之可贵。还有一些游览酬唱之作如知南康军时对山水胜景的描写及其游览之乐的再现也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朱熹的诗有较大社会价值的是那些感事抒怀诗,感事抒怀诗为有感于事的即事命笔之作,如绍兴三十一(1161年)欣闻南宋军民取得抗金胜利的消息时,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兴奋写下的《感事抒怀十六韵》、《闻二十八日报喜而成诗七首》,有感于民生疾苦的《杉木长涧四首》,还有自己身心处境的心理写照的《夜坐有感》、《病告斋居作》等。咏物写景诗是朱熹诗作中的又一大类,多为对物对事即时地有感而发,如《邵武道中》是行役游子悲情的书写,《夜闻子规》则是孤寂之感的倾诉。这类诗中最应引起注意的是他吟咏梅花之作,有《梅花两绝句》及组诗《十梅诗》的《江梅》《岭梅》《野梅》《早梅》《寒梅》《小梅》《疏梅》《枯梅》《落梅》《赋梅》等,朱熹是在通过梅花不同情状的咏叹以自况自己即时的心境。朱熹的理趣理学诗是历来最受关注的一类,这当然是由于其理学宗师的身份所造成。理学诗是宋代诗的一类,是理学家以诗的形式阐发理学的内容,如邵雍的《伊川击壤集》。朱熹理学诗的代表是“病中默诵《四书》,随所思记以绝句”[12](P.5)的《训蒙绝句》百首,由“随所思”之语可见也是他“适情”诗论主张的贯彻,因而在创作的缘起上具有些许的诗性。
不惟如此,朱熹的理学诗还多以其形象性而给人美的享受,如《克己》是以“拂垢鉴”喻“克己”的理学修养功夫,《曾点》诗的“曾点气象”胸次的春游过程的描写等无不如是。当然,朱熹理学理趣诗中的精品之作,还是那尽人皆知的《观书有感二首》和《春日》一首。其实,我们分朱熹的诗作为应酬赠答诗、感事抒怀诗、咏物写景诗、理趣理学诗等类别,只是为了研究需要的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严格说来这并非完全符合朱熹诗作的现实,因这四种之间其实是相互渗透而互有彼此的,如应酬赠答诗、咏物写景诗中也会有理学理趣的内容,咏物写景诗中也有应酬赠答之什,如《十梅诗》,正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无论怎样,有一点是不变的,即即时有所感有所悟的“适情”之作始终是朱熹诗作的主导面。道学是严肃的,抵制异端邪说的侵袭于隐微之间是醇儒内在的基本要求,故而朱熹《近思录》专辟“异端之学”一卷,以杨、墨、申、韩、佛、老之学为异端而佛老为害尤甚。朱熹在正规场合批佛老不遗余力,但在他的诗作中,却时不时有佛老思想的流露。就是这个时不时的流露,恰可是朱熹“适情”为诗主张的证据:《读道书作六首》流露恋仙羡道之意,《闻蝉》诗“悄悄山郭暗,故园应掩扉。蝉声深树起,林外夕阳稀”以适闻蝉声而以蝉鸣反衬环境的静寂,给人蝉与禅谐音双关的联想,禅味十足。
朱熹反对“做”诗,宠爱古体,主张诗应是“适情”之作,其实都和一个因素有关,即他于诗歌风格上所提倡的“平易”诗风,因为所有这些,和“平易”诗风的提倡存在着内在的甚至是互为因果的关联。朱熹提倡“平易”诗风,这是他论诗时反复申说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其实也适用于他的《诗》学,或者说,他的《诗》学中也贯穿着他的“平易”的诗学思想,这一点可以从他以歌谣解释《诗》三百诗篇来证明:十五《国风》是里巷歌谣,《雅》《颂》之篇是朝廷、宗庙的乐歌。故而可以说,“平易”是朱熹的“诗”美主张。
三、“平易”的“诗”美主张
在“诗”的美学上,朱熹整体上是一个“平易”的主张。他批评程子以义理解《诗》有深化《诗》义之嫌:“程先生《诗传》取义太多。诗人平易,恐不如此。”[2](P.2089)批评了张载的言行不一:“横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诗。’然横渠解诗多不平易。……云:‘横渠解“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却不平易。’”[2](P.2090)批评吕祖谦:“伯恭说诗太巧,亦未必然,古人直不如此。今某说,皆直靠直说。”[2](P.2092)而他自己以“平易”解释《诗》三百篇最直接体现是谓之以歌谣、乐歌。朱熹诗论也反复地标举“平易”,以“平易”衡裁历代诗人诗篇。
再者,他的诗歌创作也体现其“平易”的诗美主张。
(一)以歌谣、乐歌解《诗》
朱熹的以歌谣、乐歌解《诗》指的是他以里巷歌谣说《风》诗和以朝廷、宗庙乐歌说《雅》、《颂》之篇。以里巷歌谣说《风》诗,他曰:“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4](P.105)认为它们是下层男女的“相与咏歌”。朱熹又以正、变别十五《国风》,其中《周南》、《召南》由于是“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4](P.105)的“中和”之音,故而为正《风》;其他十三《国风》由于“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4](P.105),“所谓先王之‘风’”的“中和”之音于此而变,故为变《风》。是为朱熹的《风》诗“里巷歌谣”说。从他的“里巷歌谣”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二《南》正《风》诗篇是“中和”的治世之音;变《风》诗篇是乱亡之世的“淫乱”之音。作为“里巷歌谣”,《二南》诗篇也是抒情的诗歌,只不过是“中和”之音而已。从情感类型看,据其《诗集传》可分赞美、赞叹之情,男女情感,和乐之情三类。抒发赞美、赞叹之情者,如《关雎》篇赞美后妃之德,《樛木》篇赞美后妃不妒忌而能团结众妾,《螽斯》篇赞美后妃不妒忌而能子孙众多,《兔罝》篇赞叹即使兔罝之人也是国家栋梁的社会现象,《麟之趾》篇赞美公之子信厚,《鹊巢》篇赞美诸侯夫人的贞静纯一,《采蘩》和《采苹》篇赞美诸侯夫人能够守妇道、尽祭祀之礼,《甘棠》篇赞美召伯,《羔羊》篇赞美大夫节俭正直,《小星》篇赞美夫人不妒忌,《江有汜》篇赞美夫人能悔过,《何彼秾矣》篇赞美王姬能敬且和、执妇道等。抒发男女情感的诗篇,根据抒情主体和客体的不同,又可细分为思夫之情、反抗之情、单相思之情和怀春之情等,其中思妇诗最多,涉及的主体也较宽泛。思夫之情者,如《卷耳》是太姒思念文王之诗,《草虫》是大夫妻思念大夫之诗,《汝坟》和《殷其雷》是民间妇女思念丈夫之诗。表达反抗之情者有《行露》和《野有死麕》,朱熹认为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青年女子表达反抗无礼男子强暴的激烈情感。《汉广》表现了一青年男子看上一年轻女子,因为女子贞洁自守而不敢追求的单相思情感,《摽有梅》则是关于一个到当嫁年龄的女子抒发怀春之情的诗篇,这两篇是写单相思的。表现和乐者,如《葛覃》篇写后妃尊贵后依然保留朴素的生活方式,《桃夭》篇是关于民间男女婚姻及时、家庭和睦的内容,《芣苢》篇描写了民间妇女无忧无虑地采摘芣苢的画面。可见在朱熹的解释视野中,《二南》二十五篇,篇篇抒情。“淫诗”说是朱熹变《风》乱世之音的代表,它最能体现朱熹《风》诗“里巷歌谣”说精神实质,因为这些诗篇今天看来是地道的男女爱情诗,只不过其自由结合是不符合古代伦理规范的“淫奔”而已。依朱熹《诗集传》,“淫诗”以《郑风》、《卫风》为代表:“《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经》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女相悦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以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6](P.481)但“淫诗”的具体篇数朱熹却没有给出,研究上文,发现他所谓的“淫诗”是所谓关涉淫奔的诗歌,既可以是淫奔之人所作,也可以不是淫奔之人所作。淫奔之人所作之诗,既可以表达淫奔之时的男女相悦,也可以表达如《氓》那样的淫奔之后被抛弃的后悔之意。非淫奔当事人所作的“淫奔之诗”,既可以就淫奔表达讽刺的态度,也可以像《凯风》那样婉辞委谏,当然也可以是其他。这样一来,《卫风》之中“淫奔之诗”恰好十篇,完全符合《诗集传》的“四之一”说。而整个变《风》“淫诗”之篇当是四十之数,占总篇数一百五十九的四分之一强。
朱熹认为《雅》、《颂》分别是朝廷、宗庙的乐歌。关于《雅》诗,《诗集传》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会朝之乐,受厘陈戒之辞也。故或欢欣和悦,以尽群下之情;或恭敬齐庄,以发先王之德。……及其变也,则事未必同,而各以其声附之。”[6](P.344)朱熹接受旧说别《雅》诗以大小、正变,是朝廷音乐的歌词:正小《雅》是欢欣和悦以尽群下之情的朝廷宴飨的乐词;正大《雅》是恭敬齐庄以发先王之德的会朝之乐的歌词;变小、大《雅》则是用了《雅》的朝廷之音的乐调,但内容已不再符合原调的主旨而有变化,是为“事未必同而各以其声附之”,类似后来的依声填词。总之,朱熹的以乐歌说《雅》、《颂》和以“里巷歌谣”说《风》诗有着共同的意图,即《诗》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平易”特质。朱熹以《诗》为诗甚至为今人诗,是他《诗》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出发点云者,其意在于《诗》的平易;归宿云者,在于体现其诗歌美学风格的追求和对时人诗歌创作上违背优良传统的提醒,如他曰:“或言今人作诗,多要有出处。曰:‘关关雎鸠”出在何处?”[2](P.3324)
(二)诗论中的“平易”倡导
朱熹的“平易”诗美主张,还体现在他的诗论中。他要求诗“须是平易不费力”[2](P.3328),表扬陆游诗“‘春寒催唤客尝酒,夜静卧听儿读书’”不费力,好”[2](P.3328),说“韩诗平易”[2](P.3327)。朱熹“平易”诗美主张表现在诗体倾向上是重古体而轻今体。古体、今体的不同在于,古体重胸臆的抒发而今体重诗艺的雕刻,古体多真性情的直接表达而易为读者接受因而平易,今体因诗作者的精力放置在字句的雕琢上而导致内容枯燥隐晦多为读者不易知。朱熹倡导“平易”诗风,故而他崇尚古体而批评今体。他说:“古诗须看西晋以前,如乐府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2](P.3324)推重西晋以前古体及褒扬乐府诗而贬抑西晋以后古体,原因在于后者已有走向今体而有了格律化倾向;推重杜甫夔州以前诗而批评夔州以后诗“不可学”,原因在于杜诗夔州以后诗已是“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的今体诗。古体、今体倾向也是朱熹优李劣杜的依据:“李太白终始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渐放手,夔州诸诗则不然也。”[2](P.3326)李白诗因为始终为古体,所以优于杜甫,因为杜甫夔州以后诗背叛了古体的“平易”
而走向了今体,故而朱熹反复地批评杜甫的夔州以后诗:人多说杜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不如他中前有一节诗好。[2](P.3326)杜子美晚年诗都不可晓。吕居仁尝言,诗字字要响。其晚年诗都哑了,不知是如何,以为好否?[2](P.3326)文字好用经语,亦一病。老杜诗“致思远恐泥”,东坡写此诗到此句云:“此诗不足为法。”[2](P.3327)杜子美“暗飞萤自照”,语只是巧。[2](P.3327)朱熹对杜诗的批评,集中体现了他对“平易”
诗风的提倡以及由此所导出的推崇古体,且提出了一些和“平易”对立相犯的情况:夔州以前诗好是因为多古体,夔州及以后诗的“郑重烦絮”是指今体即格律化倾向;平易要求“字字要响”而杜甫晚年诗“都哑”了;平易和用典比如使用“经语”是相互矛盾的。朱熹在批评不合平易要求的诗歌诗人时最好用“巧”字,“巧”字的蕴意还是人工雕琢的“做诗”而导致诗不“平易”的意思,如他还在批评李贺诗不平易时使用了“巧”字曰“贺诗巧”[2](P.3328)。朱熹不厌其烦地数落杜甫今体格律诗的不是,其意也在于针砭当下的苏黄尤其江西诗人的“做”诗风气,因为“做”诗不仅有玩物丧志之嫌,更有违吟咏情性的根本,而苏黄尤其江西诗人是最推尊杜甫的。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朱熹不但多言杜诗,而且还直接把矛头对准苏黄及江西诗人。他一面以“精绝”赞扬黄庭坚诗“做”得好,一面仍不忘记拿古体诗的标准衡量他:“精绝!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但只是古诗较自在,山谷则刻意为之。”[2](P.3329)他尖锐批评江西诗派的诗人做诗:“不知穷年穷月做得那诗,要作何用?
江西之诗,自山谷一变,至杨廷秀又再变,遂至于此。”[2](P.3334)批评的立论依据还是平易诗风的提倡,说“本朝杨大年虽巧,然巧之中犹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来不觉”[2](P.3334),欧阳修喜欢梅尧臣诗、王建的“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句,均在于其有“平易”特点,朱熹因而批评今人的“做”诗:“今人都不识这意思,只要嵌字,使难字,便云好。”[2](P.3334)但需要注意的是,朱熹所倡导的平易是一种美学风格,它排斥几点误会。一,平易不是诗的草率,如他就批评了草率为诗的张耒,说他尽管有些诗写得不错,但“颇率尔,多重用字”[2](P.3330);说张南轩诗“卧听急雨打芭蕉”句“不响”,认为“不若作‘卧闻急雨到芭蕉’”[2](P.3331),并暗批张的“文字极易成。尝见其就腿上起草,顷刻便就”[2](P.3331)的草率为诗。二,“平易”不是语意直露而是“平易”中要含蓄蕴藉,因而他批评梅尧臣诗太直露,说“圣俞诗不好底多。如《河豚诗》,当时诸公说道恁地好,据某看来,只似个上门骂人底诗;只似脱了衣裳,上人门骂人父一般,初无深远底意思”[2](P.3334)。朱熹“平易”诗美主张的最终归宿还是在对道体体认后的人诗一体境界,这也是他推崇喜爱韦应物为“平易”诗风最高代表的原因,说韦应物诗“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气象近道,意常爱之”[2](P.3327)。朱熹认为韦应物诗之所以“高于王维孟浩然诸人”[2](P.3327),正在于其“无声色臭味”[2](P.3327)的人意与诗意一体无间境界,这一点也是韦诗高于陶渊明、杜甫诗之所在:“陶却是有力,但语健而意闲。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韦则自在,其诗直有做不着处便倒塌了底。……杜工部等诗常忙了。”[2](P.3327)朱熹的“平易”诗歌美学主张,还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上,如上文所及的他诗作即时即地即事即物的有感而发的“适情”性,他诗作多为古体之篇且取得巨大成就等,则是贯彻着体现着“平易”的诗美主张的精神实质,鉴于篇幅,此不展开论述。
总之,降而不黜《诗》、贬而不废诗以及“平易”的诗美主张,构成朱熹“诗”学的整体骨架,三者实为朱熹对“诗”态度的三个面向。这三个面向的形成实和他的两个身份有因果关系,一是理学家的身份,再是真知诗有诗情的诗论家、诗人身份。又和他对“诗”的本质认识即“适情”,也即即时即地即事即物情感的抒发有因果关系。从为人生的视角看,朱熹的“诗”学思想无疑是有正面价值的:即时即地即事即物情感的抒发以及对接受者的感发惩创作用显然是白居易所谓的“救济人病”、“泄导人情”。但其于诗学的整体来说又是不充足的,因为诗作为文学重要类型,还有为艺术的一面,也即诗自身有其作为艺术如声调韵律是其内在的本质属性,但这要求匠人般的精雕细琢即朱熹反对的苦“做”才能有所成就。
参考文献:
[1](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新编诸子集成[Z].北京:中华书局,1961.
[2](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宋)朱熹着,束景南辑.诗集解[M]//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5](汉)毛亨撰,(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宋)朱熹.诗集传[M]//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7](宋)朱鉴.诗传遗说[M]//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
[8](宋)朱熹,吕祖谦撰,严佐之导读.近思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9](宋)罗大经.鹤林玉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宋)李涂.文章精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11](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M]//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2](宋)朱熹着,束景南辑.朱子佚文辑录·训蒙绝句[M]//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