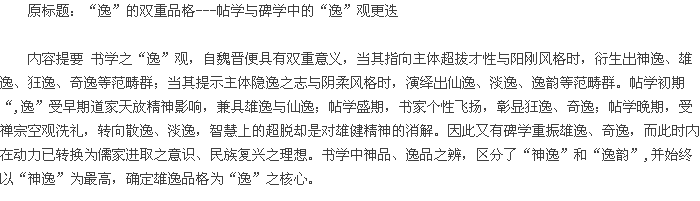
“逸”属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关于它的内涵诠释及讨论,在文论和画论领域已有深入全面的研究,但在书法美学领域却着力不多。事实上,“逸”范畴在书论史上颇多异义,它在主体才性与志趣上的歧义,在历史语境中的所指变换,都造成了理解的模糊,因此特别需要厘清。本文立足书法史和书论史自身的特点,剖析“逸”在主体才性与志趣上的歧义,梳理帖学从“雄逸”到“淡逸”的转变,“散逸”对“狂逸”、“奇逸”的解构,以及碑学振拔“雄逸”,推崇“奇逸”、“宕逸”的过程,并对书论中“神品”和“逸品”的具体所指和品次做出辨析,最终揭示“逸”
观的不同精神底蕴和主导倾向。
一、“逸”在主体才性与志趣上的歧义==由于“逸”在词源上的多义性,书论在描述主体才性和志趣时选择了两种不同的衍生义,这是导致风格层面“逸”之差异的起源。
“逸”在善跑的本义上延伸出超越一般之义,也即从强健飞驰的运动能力跃升为超凡拔俗的气禀和才能,所以词源上有“逸足”、“逸才”之说。譬如陆机《辩亡论上》:“逸才命世,弱冠秀发。”陈子昂《堂第孜墓志铭》:“实谓君有逸群之骨,拔俗之标。”
①唐代书论突出了这种天赋才能的超拔性,如张怀瓘《书断》曰:“天假其魄,非学之功。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
②“(皇象)八分雄才逸力。”
③窦臮《述书赋》评:“长民则全效子敬,便于性分。宏逸生于天机,众妙总而独运。”“思光逸才,挥翰无滞。”
④吕总《续书评》曰:“史鳞逸气雄振,超然不群。”
⑤晋唐是书法俊杰涌现的高峰期,因此多用“逸才”“、逸气纵横”、“逸气雄振”等激赏他们的卓越天赋。
正如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对“逸”的阐发:“魏晋时的所谓‘逸',实际应包括在当时人伦品藻中对人所把握到的’神‘的概念之内,亦即应包括在对神作分解陈述的气韵观念之内……神由拔俗而见;拔俗有程度上的不同,于是神可以表现为许多层次的形相;拔俗拔得最高,升华升得最高时的形象,即是逸的形象。严格地说,逸是神的最高的表现。”
⑥张怀瓘《书议》评王献之“情驰神纵,超逸优游”⑦,这种神纵超逸,多有纵横、宏大、雄振等偏于阳气盛大的特点,甚至以颠狂恣肆的非常态创造奇迹。宋以后书论对“神逸”、“超逸”也有相似运用,比如蔡襄《论书》曰“:张芝与旭变怪不常,出于笔墨蹊径之外,神逸有余。”
⑧王澍《论书剩语》评:“子昂天才超逸不及宋四家,而功夫为胜。”
⑨何绍基评苏轼:“天分超逸,不就绳矩。”
⑩这些内涵与“隐逸”之萧散淡泊、闲雅绝俗等偏于虚静收敛的精神特点迥异。
“逸”因善跑而有“逃离”之义,先秦已有超脱出世的逸民文化。隐逸是人生志趣上的抉择,因为精神清高,不容于浊世,所以遁世隐居。魏晋时期由于玄学和道教的深刻影响,对隐逸行为倍加尊崇,将隐士生活高度理想化甚至神化,使隐逸更具仙逸的审美特点。王羲之在《十七帖》中就有“吾为逸民之怀久矣”的表白。《晋书·王羲之传》记述他誓墓不仕后,“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这种纵浪大化的生活,是晋人神往的仙逸境界,也是他们在书写中流露出的潇洒飘逸、倜傥风流,具有飘升飞举与天地大化融合为一的特点。以“仙”喻书,时见于晋唐书论,如袁昂《古今书评》“薄绍之书字势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欧阳询《用笔论》喻用笔至境“仿佛兮若神仙来往,宛转兮似兽伏龙游”,窦臮评窦蒙书法“比夫得道家之深旨,习阆风而欲仙”,李嗣真《书后品》评王羲之书法“其难征也,则缥缈而已仙”.正如张怀瓘《书断》所言,晋人运笔之际,“幽思入于毫间,逸气弥于宇内”,“举众仙之奕奕,舞群鹤之纷纷”.这样的仙逸,有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气质,也有早期道教羽化登仙的玄远缥缈。
帖学早期,仙逸之气浑融在雄逸与妍媚中,由于晋唐书论把后者视为书法品质的重点,因此并未对仙逸有深意的抉发,多将其视为逸才的风神,是形式优美的一部分。帖学后期,仙逸所特有的心性超脱意味被剥离出来,备受关注,但已退却了外在超越的神仙气质,并被置换为宋明士人推崇的萧散淡逸。后者的出世态度经过禅宗的洗礼,立足平易简淡的现世生活,心性趋向内在超越的内敛幽独。这样的书风不再追求雄才逸力,而着意经营蕴藉散淡的逸韵。
二、帖学从“雄逸”到“淡逸”的转变
“雄逸”属于“气”范畴领域的审美范畴,其书法本体依据是自然生命力的美,表现天才的创造和灿烂,偏于早期道家追求天人合一的宇宙豪情和天放精神。徐复观《两汉思想史》指出,道家思想在此四百年中,一直是一支巨流。陈鼓应《老庄新论》也指出道家各派在战国和秦汉时期表现出积极有为的天健精神。因此汉隶普遍具有雄浑之气,魏晋书家多从隶书起步,行草书自然沾溉汉隶的宏大气象。而“淡逸”属于“心”范畴领域的审美范畴,其书法本体依据是主体心性之美,特别受到禅宗放下欲望烦恼、自由清净的心性熏染,表现哲人的沉思和超脱,进取的精神逐渐削弱,退隐悠闲平淡的心态凸显。所以晋唐书论用到“逸”,多为逸气遒拔、逸气雄振,以雄逸、宏逸、遒逸、横逸、纵逸为多,而宋以后则逐渐向“淡逸”转变。
萧衍评“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王羲之笔力过人,用笔腾挪自如、变幻多姿,其书法气象轩昂超拔,有天健精神和王者气度。魏晋六朝的书论喜用龙凤之类譬喻书法美的最高状态,都是对“雄逸”的形象注释。张怀瓘《书断》评王次仲八分“龙腾虎踞兮势非一,交戟横戈兮气雄逸”,评魏武帝曹操“尤工章草,雄逸绝伦”,蔡希综《法书论》评张旭草书“雄逸气象,是为天纵”,说明晋唐书论更多地强调“逸”超乎寻常的力量性、运动性和变化性,认为它是“神”的最高状态。因此缺乏热情和力量的“淡”被批评,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赞颂张旭的激情与神力,指责高闲的书法:“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
宋以后,随着时代精神从壮丽高华转向内省沉静,对晋唐杰作的品评悄然发生了转向,“雄逸”退隐,而“淡”韵凸显。苏轼评:“永禅师书……精能之至,反造疏淡。”
杨慎《墨池琐录》云:“晋贤草体虚淡萧散,此为至妙。”
汤临初《书指》评:“伯英(张芝)、休明(皇象),右军所师,今其书不可概见,意右军简淡处,从二公来为多。”
晋唐以雄逸、狂逸着称的书家在董其昌的品评里退却了气势,凸显出淡韵:“此王珣书,潇洒古淡,东晋风流,宛然在眼”,“唐林纬乾书学颜平原,萧散古淡”,“自学柳诚悬,方悟用笔古淡处”,“藏真(怀素)书……以淡古为宗”,“余谓张旭之有怀素,犹董源之有巨然。衣钵相承,无复余恨,皆以平淡天真为旨。人目之为狂,乃不狂也”.他认为米芾的“奇逸”尚不如“平淡”之境界高:“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米老犹隔尘,敢自许逼真乎?”
董其昌作为明代文宗,其淡逸的趣味和书风影响深远,代表了帖学晚期的书法境界。
清代杨景曾作《二十四书品》,专列“澹逸”一品,释曰:“轻云出岫,随意卷舒。客来不速,月见生初。偶然插柳,姿致如如。无端过雨,风韵於於。兴酣落墨,既清且虚。矜心躁气,于焉以除。”
此“澹逸”在清淡、恬淡的意义上与“淡逸”通用,并多了一层恬静安然之意。再参考他的“超迈”一品:“和风吹林,偃草扇树。古岸闲花,水田逸鹭。机趣横生,具兹尺素。靖廊庙心,起山林慕。深涧投竿,坡间小住。渺虑沉思,访桃源路。”
所举意象皆是超脱隐逸的田园生活。清虚渺虑荡涤了矜心躁气,书法之“逸”美,已经由惊虬逸骏、虎跳凤舞之“雄逸”,演变为轻云初月、闲花逸鹭的“澹逸”.弘一法师曾自述其书风的变化“:拙书尔来意在晋书,无复六朝习气”,“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从董其昌到弘一,书法表现出排斥力量和气势的趋向,并在弘一这里达到了松弛、静穆而空寂的高峰。由此可窥汉魏晋唐崇尚的偏于刚健的士人风骨,经过现实的挫折与沉思,已经转向内敛清虚以至枯寂。这是一个生命进取精神逐渐淡化弱化的过程,也是人生智慧趋于老熟后的澄明与放下。
三、“散逸”对“狂逸”、“奇逸”的解构
“狂逸”和“奇逸”是帖学早中期推崇的审美境界,是对严谨却流于刻板的法书的突破,在行笔速度和结体上追求创新,以纵横意气为高。继东汉张芝、东晋王献之之后,唐代狂草达到了新的高峰,书论多有激赏。虞世南《笔髓论》认为草书“或体雄而不可抑,或势逸而不可止,纵于狂逸,不违笔意也”,怀素在《自叙》中赞颂张旭“姿性颠逸,超绝古今”,而自谓“狂僧”,“以狂继颠”,并形象地诠释了“狂逸”的创作状态:“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叫绝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
“狂逸”是在“雄逸”基础上的颠狂恣肆,兼具“雄逸”的力量性和天才特点,在形式上更加狂放,更具内在张力。
超越方正规矩,创造“奇逸”姿态是草书发生时的天然追求,崔瑗《草书势》最早提示“放逸生奇”,张芝、二王是早期的典范,袁昂《古今书评》评“张芝惊奇”,孙过庭《书谱》说王羲之“书《画赞》则意涉瑰奇”,张怀瓘《书估》也评王献之“志在惊奇”.但晋唐书法总体以华美典雅为尚,对“奇逸”尚未能发挥。直到北宋,在尚意书风的激发下“奇逸”才焕然出彩,特别指向杨凝式、米芾书法。譬如杨慎《墨池琐录》记“米南宫奇逸超迈,烟云卷舒”,赵宧光评“杨凝式为奇逸之品”,朱履贞《书学捷要》云“米襄阳奇逸超迈,体势似疏散”.“奇逸”是在“雄逸”基础上的创变,更具奇特的个性风格。
米芾的奇逸并不能挽回帖学向着隐逸气质的倾斜。唐代诸家法书的雄健精严一再被指责,因其失去了晋书萧散和畅的逸气。黄庭坚《论书》云:“余尝论右军父子翰墨中逸气破坏于欧、虞、褚、薛,及徐浩、沈传师几于扫地。”
项穆《书法雅言》评陆柬之:“予尝见其所书兰亭诗,无一笔不出右军,第少飘逸和畅之妙。”
曾经备受推崇的“狂逸”和“奇逸”也被否定,项穆把“纵放悍怒,贾巧露锋,标置狂颠,恣来肆往”列为“傍流”,在“品格”中居最末。赵宧光批评:“好狂逸家书故是妙用,而气质或随之坏,张、素、米、黄是也”,“世间恶札,一种但弄笔画妍媚,一种但顾雕体圆整,一种但识气象豪逸。求其骨力,若罔闻知。更进而与谈韵度,尤不知其九天之外也”.“散逸”之韵度转而成为最高的书境,于令淓《方石书画》诠释道:“逸韵如深山高士,俱道适往,萧散自如,不受人羁。”
张照曾评述董其昌书法“:世人以其萧散纵逸,脱尽碑版窠臼,疑其天资高而人力浅。余曾见其二十三岁时写《普门品》,学《麻姑仙坛记》,便如印印泥然。则其苦心力学为何如也?此道亦有三关:初若印泥,中若印水,终若印空。”
董其昌的“纵逸”已经被“萧散”所缓释,他学颜真卿和米芾最多,但最终追求的是骨力豪逸之外的萧散韵度,此韵度已非单纯的道家出世精神,更经历了禅宗空观的陶化。
“散逸”不仅回避雄强的力量和精严的法度,更要在峥嵘的狂逸与奇逸之外另辟蹊径,表现人生的轻松、和畅、萧散和率意,因而它在人生志向上具有解构性,它将精进有为的儒家精神以及强烈的艺术个性追求瓦解,以表现精神超脱为高,与“淡逸”一起构建起帖学晚期的书法趣味。
四、碑学振拔“雄逸”、“奇逸”和“宕逸”
事实上,帖学在明代晚期对自身进取精神的弱化和超脱已经进行了反拨,秦祖永《桐阴论画》评“瑞图书法奇逸,钟王之外,另辟蹊径”,以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王铎为代表的草书家都为重振雄奇做出了努力。而清代碑学的兴盛,彻底摆脱帖学窠臼,回到秦汉魏碑,对雄逸精神作了最大程度的鼓吹。康有为批评董其昌的淡逸书风:“若董香光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太淡则肉薄,然与其淡也宁浓,有力运之不能滞也。”曾经笼罩宋明书坛数百年的淡韵被强劲的碑学话语否定。碑评中用到“逸”,大多指向飞动、雄奇、豪宕等,试图以丰茂盛大的阳刚之气振疲起痹。早中期篆隶勃兴,王宏撰评:“汉隶古雅雄逸,有自然韵度。”王澍评《石鼓文》:“书严正铦利,遒劲而有逸气,为大篆之祖。”
由于篆隶总体上偏于整饬,不宜发挥个性才情,所以清后期偏于飞动奇宕的汉隶和魏碑大倡,书家追求更加自由奔放的行笔和结体,“飞逸”、“宏逸”、“奇逸”、“宕逸”备受推崇。譬如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列《石门铭》为上宗:“为飞逸浑穆之宗,《郑文公》、《瘗鹤铭》辅之。”
刘熙载《书概》评《瘗鹤铭》:“举止历落,气体宏逸。”再如对《石门颂》的评价,张祖翼《石门颂跋》曰:“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也,力弱者不能学也。”
《石门颂》的雄逸特别因康有为的推崇而大放异彩。“奇逸”的所指发生巨大变化,多指向《石门颂》、《石门铭》、《郑文公》、《瘗鹤铭》等汉魏碑版或异于中原的奇字。如罗复堪《论书绝句》曰:“高超奇逸石门颂,胆怯何由敢问津。”
沈曾植《海日楼书论》评:“金文中楚人书体甚奇逸于中原也。”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其余若萧衍之造像、慧影造像、石井阑题字,皆有奇逸。”“《新罗真兴天王巡狩管境碑》奇逸古厚,乃出自异域。”“奇逸之《瘗鹤铭》,则有《石门铭》当之。”他列举魏碑十美,其中“五曰意态奇逸”,他认为“书若人然,须备筋骨血肉,血浓骨老,筋藏肉莹,加之姿态奇逸,可谓美矣”.康有为自身书法多取此类碑版,他在碑学大倡的时代推崇“奇逸”,不仅是对软弱僵化帖学的批判,更是其雄奇超拔的政治抱负在艺术领域的折射,他将宋明以来个性化、文雅化的“奇逸”演化为一种民族精神的“奇逸”,所以在精神气象上更加崇高伟岸。
在重振“雄逸”和“奇逸”的同时,碑学亦张扬自身特有的“宕逸”.帖学评价行草书多取“纵逸”,因其章法连贯,纵势而下;而隶书或魏碑字字独立,以结体的横宕开张取势,依托高碑大碣、巨石摩崖而具雄伟高古之气。包世臣《历下笔谭》评:“《太公望碑》是《乙瑛》法嗣,结字宕逸相逼,而气加凝整。”“《朱君山碑》用笔尤宕逸……骨血峻秀。”康有为评“《孔宙》、《曹全》是一家眷属,皆以风神逸宕胜”.《慈香造像》“使转斫折,酣纵逸宕”,“《张猛龙碑阴》笔力惊绝,意态逸宕”.他总结魏碑特点:“质实厚重,宕逸神隽”,“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着而出以涩笔,要以茂密为宗”.晚清士人以豪宕雄逸之气,试图挽民族危亡之狂澜于既倒之际,他们将社会理想转化为特殊的时代审美追求,赋予“逸气”更多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雄浑气质。相对于帖学之“散逸”和“淡逸”,“宕逸”以其横宕的霸气和开张的逸气,体现出中华民族参与世界竞争的壮伟豪情。
五、书论中神品与逸品之辨
帖学与碑学中多样风格的“逸”在品次上并非处于一个等级,虽然有些风格如“淡逸”、“散逸”曾经占据书坛话语中心,但也不能位列最高品第,因为书品论定不仅仅依据某一时代的趣味,而更仰赖具有内在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的审美共识和公论。书论中关于神品与逸品的高下之辨,集中反映了书论家评判“逸”风格的基本态度。这种评判与画论有较大差别,不能以画论的主导观点混淆书论自身的判断。
画论自宋代以来就有“神逸之争”,而论者多以“逸品”为高。文人画注重情兴挥洒或意境营造,其中“隐逸”之趣占据了主导,普遍流露出闲雅绝俗、清虚自守的气质。“虚静”和“旷放”成为逸品画的主要特点。其实书论领域也经历了由崇尚生命神气到关注主体心境和意韵的转移,这一点从“逸”的内涵由侧重“雄逸”、“奇逸”演化为欣赏“散逸”、“淡逸”可以看出。但书法在清代再次振拔“雄逸”的努力,说明书学内在涌动着阴阳两种抗衡力量,而阳刚雄强之气最终居于主导。历代列书品的书论家多已自觉到“逸”的双重品格,始终坚持以“神品”为主领,统摄“逸品”之内涵。当“逸”取雄俊天才和纵横飞动之义时,以“神逸”而归为神品;当“逸”取萧散态度和恬淡虚静之义时,以“逸韵”而划归“逸品”,居神品之下。例如董其昌的书法曾在晚明及清初风行,但在品第上无论如何也无法超越二王、米芾以至赵孟頫,他以散淡逸韵独开生面,但在神力和才华上不足,其书品居神品之下。这从清王室书法范本选择的转移可以看出。康、雍尚董书,乾隆开始转尚赵孟頫、二王,乾隆之子成亲王永瑆精工赵体,兼善米书、唐碑,成为此后王室书法学习的楷模。这种选择是对汉文化流传有序的书品定论的认同。
最早品列书家的庾肩吾在《书品》中将钟繇、张芝、王羲之列为上之上品,评曰:“烟华落纸将动,风彩带字欲飞。疑神化之所为,非人世之所学。”
虽未直接定义为“神品”,但确是“神逸”之谓。虽然李嗣真《书后品》在上上品之上专列钟、张、二王,评为“超然逸品”,但都是以“神”来诠释“逸”,比如“神合契匠,冥运天矩,皆可称旷代绝作也”、“然数公皆有神助”、“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及其不失,则神妙无方,可谓草圣也”.这些都是在气禀和才性之美的意义上运用“神”,因为气的良能和高级状态、神秘莫测的创造才能就是“神”.张怀瓘品评书法只用“神、妙、能”三品,并未单列出“逸品”.他将钟、张、蔡邕、二王等列为神品,评张芝草书“精熟神妙,冠绝古今”,蔡邕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王羲之“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王献之“雄武神纵,灵姿秀出”,“盖欲夺龙蛇之飞动,掩钟张之神气”,都体现出他以“风神骨气居上”的品评观。
朱长文《续书断》列“神、妙、能”三品评定唐代书家,认为“杰立特出,可谓之神”,杰立特出就是超拔的才能和创造。他把颜真卿、张旭和李阳冰列为神品,评颜真卿“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张旭草书“如神虬腾霄汉”,李阳冰篆书“其格峻,其气壮,其法备”,将雄壮遒健的神气视为最高。黄庭坚《跋法帖》曰“: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如左氏,大令似庄周也。由晋以来难得脱然都无风尘气似二王者,惟颜鲁公、杨少师仿佛大令尔。”
他把王献之、颜真卿和杨凝式均视为超尘拔俗的神品。
元明清以来,帖学为赵孟頫的书法笼罩,书品基本延续晋唐定论,以二王为宗、为神化至境的共识从未动摇。董其昌也认定:“右军《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
杨景曾《二十四书品》列“神韵”为第一品:“不知自来,莫测所住。变化无端,作非非想。威凤翱翔,神龙游荡。风起青艹频,露凝仙掌。凡骨久更,金丹竞爽。造化可通,难摹阙象。”
其品评依据还是二王书法,突出了天才创造的雄逸神奇。而“澹逸”位列“雄肆”、“遒炼”、“峭拔”、“浑含”诸品之后。
在碑学品评中,包世臣《艺舟双楫》将清代书家分为“神、妙、能、逸、佳”五品:“平和简净、遒丽天成,曰神品……楚调自歌、不谬风雅,曰逸品。”
他列邓石如的篆书为神品,“遒丽天成”即天才的神力与形式创造是“神品”的内核,而个性风雅的诸多清代行书家为“逸品”居次。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在“碑品”一节中分列神品、妙品、高品、精品、逸品和能品,也把“神品”列于“逸品”之上。他以《爨龙颜碑》、《灵庙碑阴》、《石门铭》为神品,评“《爨龙颜》为雄强茂美之宗,《灵庙碑阴》辅之”,“《石门铭》飞逸奇浑”,将雄强茂美和奇逸视为神品,而以清淡疏秀一路的《朱君山墓志》、《敬显俊刹前铭》、《李仲璇修孔子庙碑》等碑为“逸品”.
由此可见,书品始终标举汉魏晋唐经典的风神骨气,将其作为品评的最高标准。这与书法的审美特点及书家的身份、信仰等因素关系密切。书法在形式上以点画运动和线条的抽象变化为美,它不似绘画多取自然山林、花鸟虫鱼为题材,善写隐逸生活,以静态造型经营清虚空灵之境,而更属于动态之美,更强调笔力的劲健和才情的勃发,以雄势挟远韵,追求刚柔兼济、出神入化的境界。书家身份较画家多元,晚清以前很少单纯的职业书家,而杰出者多为士大夫,他们往往位于政权中心或思潮前沿,较之画家更多入世的复杂心绪,更能敏锐地表达时代精神的变化。“逸”自身的双重品格具有一种内在的制衡张力,当雄逸、奇逸滑向粗豪怪诞庸俗之时,散逸、淡逸起而治之;当散逸、淡逸流于疲弱空疏因循之时,雄逸、奇逸起而振之。它们在帖学与碑学中的更迭,不仅是书法审美趣味的选择,更受命于民族之精神运会,暗示出本土原生的道家、儒家精神与佛教空观之间相互颉颃、此起彼伏的态势。特别是“散逸”、“淡逸”的审美趣味,既是超越、纯净、虚灵的,也是柔弱、消极、狭隘的,魅力与不足同在。在后期文人身上,更表现为消极避世、沉湎于个人恬淡的审美生活,缺乏雄心壮志的弊端,这也是清代书法发生重大变革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