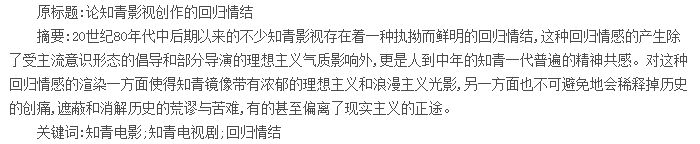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不少知青影视存在着一种固执而鲜明的回归情结,这种回归情感的产生除了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和部分导演的理想主义气质影响外,更是人到中年的知青一代普遍的精神共感。对这种回归情感的探寻不仅可以还原知青一代的心路历程,提供阅读知青镜像的一把钥匙,而且对于当下主要依靠网络和视频来阅读历史的年轻一代如何正确地理解上一代的精神世界提供启示。
一、精神原乡
知青影视创作一直受到政治意识形态、文学思潮和世纪末商业化大潮等因素的制约,“文革”及其以前的知青电影更多的是抒发扎根边疆和农村的豪情壮志,新时期初期的知青影视呼应当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思潮,以控诉反思为其主旨,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知青影视则逐渐淡化政治化叙事,向商业化和家庭伦理倾斜。而在这些后面横亘着一条固执而鲜明的情感箭头,那就是越到后来越表现出对曾插队农村、所生活过的兵团的回归倾向。其代表性的电影有《我们的田野》、《青春祭》、《南方的岸》、《小芳的故事》、《巴尔扎克与小裁缝》、《村路带我回家》、《幸福就在身边》等。电视剧有《山羊坡》、《几度菊花香》、《像兄妹一样手拉手》、《遭遇昨天》、《情满珠江》,甚至《孽债》、《哥们》等。
当然,仔细分析起来,这些影视中表现的回归倾向的比重分量不一,有的只是在开头结尾稍作点缀,有的则是浓墨重彩地抒写。它们的表现形式更不一样,有的是选择回到原来的地方工作,如《我们的田野》中的希南大学毕业后最终选择回北大荒。有的是返城后对城市生活不适应,找不到生活的位置,再次回到插队的农村,如电影《幸福就在身边》的女知青肖点点就说:“回到城市一切都陌生了,我一直感到不协调,几年了,我仍然不能适应。我想,在鄂西那个小村庄里,我也许还有点用,生活才有点意义”。同样的例子还有《南方的岸》中的易杰与暮珍决定重返他们曾下放的海南橡胶园。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实际上比较少见,尤其是《我们的田野》中家在北京的希南大学毕业仍回北大荒的情节更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第四代导演的理想主义气质和当时国家的政策提倡有关(下有详论,此处不赘述)。有的则是怀着忏悔、感恩之情重新回到爱情和青春的起点,典型的如电视剧《几度菊花香》,高红旗最后回到他始乱终弃的初恋、临终的菊香床头,拿出当年菊香送给他的野菊花向她忏悔和感恩。而作为菊香的丈夫、现已是外资老板的陆建国则注册了一家旅行社,专营天柱乡的旅游,这样既可以为天柱乡的经济发展出力,又能经常到菊香的墓前看看。实际上菊香是他们共同的青春记忆,天柱乡则是他们一去不返的青春的永久收藏地。而更多的表现形式则是重走一趟青春之旅,作为城市的观光客,拾起青春留下的脚印,去凭吊和追寻。如《巴尔扎克与小裁缝》、《青春祭》、《遭遇昨天》等。有的则是在都市找不到真情,重新去寻找青年时代那份纯真,那份失落的爱情与友情。如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于1994年的《小芳的故事》,影片根据红极一时、由李春波创作的歌曲《小芳》主题演绎而成。描写一个回到都市的老三届知青,事业无成,婚姻情感倦怠,决心去寻找当年插队时热恋的农村姑娘小芳……同样的作品还有《中国知青部落》。该剧是描写知青返城后的生活最为深刻也最为沉重的一部电视剧,去掉了知青影视常见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温情,裸露出生活最残酷的一面。起首的片头曲那种黯然感伤为全剧定下了情感的基调。剧中的主人公和核心人物不是沦为社会底层,就是事业不顺,婚姻亮红灯。唯一事业如日中天的饶一苇情感世界一片荒漠,婚姻失败,与前夫侯过的爱情破镜不能重圆,她选择再次回到下放的地方,去寻找那份遗失已久的纯真。有的是因为从前的战友、甚至恋人长埋在那个地方,如今去凭吊、缅怀,如《像兄妹一样手拉手》。还有一种是扶植资助所插队的农村,或对当地进行投资开发,前者如《哥们》中的肖志成一直留在内蒙草原,退休才返回他阔别30多年的城市。他干苦力,上下奔走只是为了给曾插队的农村建一所希望小学。后者如上面提到的《几度菊花香》中的陆建国。《山羊坡》是表现回归情感富有深度的一部知青电视剧,根据北京知青回到当年插队的农村扶贫的真人真事改编而成。女主人公蒲春雨首次回山羊坡是缘于参加30年前和她一起下乡插队、后来与当地农民结婚的女知青苗文秀的儿子的婚礼。回村后的所见所闻使她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
30年前她带领知青战天斗地、砍树开荒造梯田的壮举,如今成了山羊坡贫困的原因。她决定再次回到山羊坡,带领乡亲们绿化脱贫。影片主题设置虽然有当下保护环境的政策倡导的影子,但蔳春雨回乡植树有她内在的情感驱动:“都三十年了,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让我放不下。”“这个地方,我哭过,我醉过,甚至我还诅咒过,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最想的还是这个地方。”这段话其实道出了所有知青对曾下放地的共同情感。蒲春雨是想去弥补,甚至是赎罪,但说到底她还是想去寻梦,去重温、找回那段火热的青春岁月。保护环境,扶贫脱贫是表,寻找青春是里。
最后一种也是最大多数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回归情结,剧中人根本没有回到曾下放的农村或兵团,但在城与乡,今与惜的对比中,流露出对当下、对城市生活的厌弃,对曾下放地的怀念和向往。今不如昔,城不如乡。身没回,心已回。他们“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依恋回归之情,他们将不断讴歌农村,诉说乡愁,时时在渴望回归,事实上不曾回归,这是一代人特有的宿命感”①。改编自梁晓声原着的电视剧《雪城》中回城后被生活所迫抛弃初恋情人、与他人结婚的徐淑芳就说“那时候我把城市看作天堂,把北大荒看作地狱,回来以后我把它们颠倒了,我恨城市,回城以后我再也没笑过”。《中国知青部落》中的饶一苇:“说来奇怪,想起那段日子,倒并不觉得苦,相反倒有一种说不出的怀念。”林大川也说:“想想那些日子就莫名其妙地激动”。他们的话道出了所有知青的共同心声。
二、回归驱动
那么,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知青影视为何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曾下放的农村和兵团的回归情结呢?
首先,知青影视大多从知青文学改编而来,它们是一对孪生兄弟。早期的知青文学和知青电影主要是当时政治运动的宣传品,它们“巧妙而又隐蔽地寄生在政治体制上,为某种政治运动、政治统治进行合法化的文学表达”②。后来也一直随政治气候和文学思潮不断变换其主题。
20世纪80年代,知青影视的回归主题设置一方面是上山下乡运动“强弩之末”的思维惯性,一方面则是当时国家要求年轻人(尤其是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政策倡导,导演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添加上这样一个主旋律的尾巴,如80年代创作的电影《南方的岸》和《幸福就在身边》等就打下了这种烙印。甚至1984年上映的《今夜有暴风雪》中的曹铁强最后决定留在北大荒,也有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殉道情怀。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对“文革”派生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一直没有明确的定论,上层态度的暧昧和知青一代骨子里的英雄主义造就了影视剧中的强行驻守和回归的主题。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政治运动产物的早期知青电影所表现的对下放地的向往不属于本论文所讨论的范围,因而它们主要属于政治和政策范畴而不在心灵范畴。
其次是一部分导演的理想主义气质造就了知青影视的回归情结,为了暗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劝谕目的,不惜对情节和人性进行强行扭曲,实则是导演的一厢情愿。如谢飞导演的《我们的田野》本来表现的是青春在“文革”中被欺骗和蒙受屈辱的悔悟,但导演完全以赞美的笔触写那群年轻人的友情和献身北大荒的精神,流露出浓厚的温情色彩。实际上主人公希南回北大荒这个情节非常牵强和矫情,是导演“粘贴”上去的。回去又怎样?去寻梦?梦已破,人去楼空。即使回到那块伤心地不久也会逃回来,因为那块曾经温暖的土地已变冷。即使有余温,能温暖照亮一生吗?当然,并非所有第四代导演的知青电影都打上这种理想主义烙印,事实上,张暖忻的《青春祭》中主人公李纯重返旧地去凭吊缅怀就流露出难以掩抑的感伤与沉痛。
然而,我们把这一切外在的“釉彩”去掉,露出里面的内核,也可发现知青影视中执拗而清晰的回归情感指向,这种情感指向像一条鲜明的红线横亘贯穿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不少影视作品中。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整个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氛围逐渐冲淡,作家和编导们不必再为图解政策而创作,不必再绞尽脑汁将作品穿上各种“迷彩服”嫁接在政治意识形态上面,他们可以在创作上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表现真情实感为何就使其作品表现出回归情感呢?
从人的生理来看,少年时代的特点是“瞻前”,一味向未来挺进。人到中年便开始“顾后”,易沉湎于对过往生活的回忆和怀念。这批知青作家大都是20世纪50年代初生人,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20世纪90年代都是人到中年。而回忆不像电脑的硬盘存储,而是一种过滤器,带有很强的筛选功能,它会过滤掉其中的杂质,淡化甚至屏蔽掉从前的苦难、屈辱、甚至遭受的摧残,荒废的青春,破灭的理想等等,而选择那些美好的回忆:热血青春,豆蔻年华,火热的斗争生活,纯真的友情和爱情,哪怕他们曾对下放地恨之入骨。凤凰卫视的知青纪录片《红尘滚滚》中的被采访人许世辅说的话就准确地表现了知青一代的共同情感:“当年我们从那里逃离苦海,奔回了家,撒尿都不朝那个地方,太恨那个地方给我们带来的非人的折磨,炼狱般的生活,诅咒它。经过了若干年,但我们自己感觉,我们割舍不开它……剪不断理还乱”。不堪回首,却要回首,怎能不回首?!所以如此,是因为回忆是以当下的心境作为起点的。
若我们再回溯一下我国知青运动的发展历程,或许更能明了这一点。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就开始实行上山下乡运动,1955年8月、9月、11月北京、上海、天津青年志愿垦荒队分赴黑龙江、江西垦荒,揭开了这一运动的序幕①。但真正大规模上山下乡还是1968年,老三届,他们一下放就是十年,从十六七岁一直到二十六七岁,在“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接受再教育”,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都殡埋在此。知青一代生长于一个英雄主义精神被无穷放大的时代,父辈的光荣传奇,童年时代的英雄故事和对英雄的幻想对这一代人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塑造了他们基本的人格范型,使他们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风流人物,请看今朝。今天我们从潜意识里回首当年的红卫兵运动,那有时代的原因,但又何尝不是他们内心蓄积已久的英雄主义梦想过于漫溢所致,虽然扭曲却也是必然。在那个个人崇拜甚嚣尘上的年代,他们接受过伟大领袖的八次检阅,谁有这样的殊荣?!“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①。“伟大领袖”的这番赞许实际上是给了他们未来的预许劵,暗示他们将通过苦难抵达他们的英雄梦想,成为未来国家的主人。在领袖“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下,他们写血书,偷户口本,爬车,义无反顾地弃绝城市,满腔热血一路高歌地奔向“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
然而,当他们怀抱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梦想扎根边疆,扎根农村,面对着下放地艰苦单调的生活环境,枯燥繁重的体力劳动,专制主义的氛围,不少人的理想瞬间肥皂泡般地破灭了。他们本来就不属于这里,在经过长长的“炼狱”煎熬后,他们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渠道,逃也似地离开农村,离开这块埋葬着他们青春的放逐地,回到城市,有的女青年甚至拿她们宝贵的贞操去换得那一纸回城调令。新时期的不少知青影视就表达了这种控诉主题,如《天浴》、《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蹉跎岁月》等。然而,他们回到城市,城市却流露出冰冷、漠视甚至敌意。他们找不到工作,沦于社会底层,成为城市的多余人和零余者,返城成为了比下乡更为严峻的再度放逐。以《雪城》、《返城年代》为代表的知青影视就描写了这种回归后的失落感和挫败感。《雪城》中当年名震兵团的金嗓子刘大文回城后只能以倒卖黑市香烟为生。《返城年代》中的知青营长竟然沦落到站马路与民工抢活。《银杏飘落》中待业的詹华为加入环卫工行列而欣喜不已。《雪城》中有个被人忽视的细节:刘大文在兵团相识相爱的妻子的死表面上看是人为事故造成的,实际是返城知青梦想破灭的象征。这以后,他们终于在像螺丝般拧紧的社会阶梯上觅得了自己的位置,结婚生子,在平凡而世俗的生活中,打发走了剩余的青春以及附带在剩余青春之上的理想和热情。更有甚者,有的知青回城后,工作不顺,事业无成,婚姻破裂,友谊褪色,这更促使他们缅怀和反刍在“广阔天地”里那段火热的青春岁月,那种理想和激情,那份纯洁的爱情和友谊。于是出现了不少知青影视中的寻找和回归情结,如上面提到的《中国知青部落》中的饶一苇剧尾去曾插队的云南兵团;《小芳的故事》中的陈卫东去寻找初恋情人小芳的故事。
即使事业成功,志得意满,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事实上,这样的情况非常罕见),他们心里仍有一个空洞永远无法填补,仍有一种东西永远遗失在下放地,那就是:青春。人生有三件东西一旦失去便永远找不回来,这三件东西就是:故乡、青春和爱情,但越找不回来越要去寻找,在寻找中似乎得到,又在得到中永远失去,这就是人生的悖论!知青和知青作家、编导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20世纪90年代都是人到中年,不管是贫穷还是显达,有一种经历是他们共同的:青春一去不返。《银杏飘落》中已是大公司的董事长的潘梁玉感叹道:“想想现在什么都有了,钱,房子,车,可是我宁愿用手中的一切去换取我跟张萌的那段时间。”凤凰卫视的纪录片《红尘滚滚》中的老知青聚在一起忘情地唱知青时的歌曲,那何尝不是在白日梦中重走青春之旅,借助歌曲的翅膀在想象中重回到那火热的知青年代,沿着缺席走向在场,虽然他们“所能抵达的只是欲望自身———那个掏空了的现实的填充物”②。《青春祭》中的独白:“岁月流逝,人世变迁,那里永远是水长青,草长绿”。为何那里永远水长青,草长绿?因为青春和爱情永远留在了那里,那是一份永远搬不走的“不动产”。正如《像兄妹一样手拉手》中雷晓曼说的“这里有我流过的汗水,泪水,还有我的青春和梦想”。
20世纪90年代,各地知青举办了一次次以“青春无悔”为主题的回顾展览,受到一部分知青、社会名人以及年轻一代的猛烈批评,因为“青春无悔”的命名是与主流意识形态妥协的结果③。在成都举办的知青回顾展上,一位研究生尖锐诘问:如果无悔,你们干吗回城?既然回城,为什么又要喋喋不休地说“无悔”?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哪能理解这些人到中年的知青一代对下放地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呢?是的,“让大家再走一次,谁都不愿意”,但谁不怜惜自己的青春呢?“感谢那段生活,感谢并不意味着我会选择它”(《红尘滚滚》中邓贤受访)。正因为此,他们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去看看青年时代留下的脚印,看看那些曾经与青春朝夕相处的山山水水。
表现在创作上,后知青影视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回望过去”的姿态,“他们再次以想象的方式重返乡村,乡村生活审美价值一面被重新估量,进而乡村被虚构成一片美丽的净土、虚幻的乌托邦”。这种情感倾向正是大部分知青影视表现回归情感内在的心理驱动。
三、双面镜像
回归情感驱动给知青影视带来了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影。如上所述,知青下放的时代是一个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高扬的时代,不管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号召”下放,他们曾满腔豪情扎根边疆,扎根农村,《神奇的土地》中的李晓燕和《我们的田野》中“七月”在当年的知青一代中绝不在少数。知青那段生活虽然有苦难和不幸,但在那里他们战天斗地,挥洒青春和热血。在回归情感的驱使下,那段火热的生活回忆起来自然会充满理想和浪漫的光影。《我们的田野》片头那种进行曲般的抒情旋律,北大荒辽阔的田野,黝黑的沃土,灿烂的金秋,挺拔洁白的白桦树以及上面旋转的蓝天,赋予了画面浓重的抒情意味,而一代人为了理想献身北大荒的拓荒精神虽然也带有悲情意味,但其主导面是张扬青春与理想的力量,那何尝不是当时知青生活和当下知青一代心态的写真呢。同样的作品还有电视剧《兵团岁月》、《爱在冰雪纷飞时》,电影《神奇的土地》等。这种理想主义情怀,吃苦耐劳战天斗地的精神,禁欲主义氛围造就的心灵的纯真与洁白正是当下社会稀缺的,它们将煮沸一代代人的热血。如果再回头看看“第六代”电影中所透露出的焦虑、茫然、颓废、虚无等世纪末的情绪以及“第六代后”电影中赤裸裸地张扬物质主义的扭曲的“青春梦想”,更显得它们的可贵,作为一种正能量的精神遗产,它们永不过时。
回归情感的驱使也使得知青影视去掉了早期控诉鞭挞的主题设置,而表现出温情诗意的风格和明亮的影调。以梁晓声为例,早期作品不管是《神奇的土地》中为当时“膨胀的政治热情”献出了灵魂的副指导员李晓燕,还是《今夜有暴风雪》中那个出身不好最后被暴风雪吞噬的袁晓云,都是通过年轻美丽生命的夭折对上山下乡运动和“文革”血统论进行控诉。在《今夜有暴风雪》中还树立了一个被鞭挞的对象———极“左”路线的代表、专制蛮横的兵团团长马崇汉。但在近年拍摄的电视剧《知青》中,早期的那种批判鞭挞的力度弱化了,取而代之的则是知青生活温暖明亮的光影。黑龙江兵团的基层干部被描写得慈颜善目,外威内蔼,如再生父母,如大哥大姐。而陕北农民纯朴厚道,待知青如自己的儿女,赵曙光被描写成农民的儿子和主心骨。我们再看不到其他作者创作的《红颜的岁月》、《兵团岁月》、《天浴》和《原谅》中基层干部对女知青的引诱和胁迫,人格的践踏,也看不到《蹉跎岁月》对出身不好的知青的歧视和打击。唯一一个“恶”的代表、公社的牛主任最后也让他良心发现,没用道德的钢鞭将他往死里打(请注意,梁晓声的下放地是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没在陕北,陕北那段生活有很大的虚构和想象成份和先验理性痕迹)。而且剧中人物都有一个大团圆结局,不仅主人公赵天亮和周萍结婚生子,齐勇和孙曼玲喜结良缘,而且也让配角“小黄浦”和谢菲终成眷属。陕北的赵曙光与冯晓兰,武红兵与李君婷的爱情因为苦难而变得更加坚贞。知青生活的苦难,屈辱,摧残等等都省略掉了。仅以知青救火牺牲情节为例,好几部知青影视都提到这一点,但《知青》把知青扑救森林大火的悲剧结果省略了。表现在影像上,尤其是在北大荒兵团那一块,阳光永远灿烂,影调明亮柔和,人物脸上的光饱满,没有一丝阴影。成片的白桦林,清澈的河流及两岸碧绿的草甸,皑皑白雪,将知青生活渲染得青春洋溢,诗意盎然,与《今夜有暴风雪》中那种黑云压城,风雪怒吼的取景及对比强烈的影调形成鲜明的对比。从题材来看,《返城年代》(2014年)是《雪城》(1988年)的姊妹篇,但明显缺乏《雪城》那种批判的锋芒和鞭挞的力量,反倒是儿女情长的比重愈来愈多,主题位移。
这种对下放地的诗意言说,修复和美化记忆中的“精神原乡”,不可避免地会稀释掉历史的创痛,遮蔽和消解历史的荒谬与苦难。加之有些年轻演员由于生活阅历所限导致在表演上的戏谑、轻薄风格,淡化了知青生活的严肃性、残酷性和正剧风格,在知青历史“立此存照”的真实性上,这些知青镜像不可避免要出现倾斜和失真,对于当下或未来主要以影像来阅读历史的年轻一代,必然会造成对历史的误读。
这也是它们遭人们诘问和责难的原因。
当然,也有一些描写回归情感的知青影视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商业化大潮的夹裹下偏离了现实主义的正途,走入误区,不伦不类。典型的如《小芳的故事》中事业无成,婚姻冷漠的陈卫东去寻找插队时的农村姑娘小芳,没料想小芳已是华裔富商的遗孀,本来想去扮演拯救者的角色,倒成为了被拯救者。虽然最后在飞机场两人重新团聚,但因为整部剧是根据李春波的流行歌曲《小芳》改编而成,编造痕迹过于明显,强行地扭曲情节以吻合歌曲主题,缺少现实生活的依据,至少不具普遍性,没有表现出生活本质的真实。其实,更多的“小芳”应该是满面风尘的中年农村妇女,早已褪去了少女时代的温婉多情。然后,“陈卫东”们失望而归。假若描写这种“相见不如怀念”的失望和绝望,那种心灵落差,其力度也许更强,更真实更典型,更能表现出震撼心灵的深度。
最后一点要说的是,知青影视写出了不同的回归情感,然而却到此止步,未往深处开掘。实际上,当寻梦的知青们热扑扑地回访当年插队落户地,见到久别的乡亲,尤其是年轻时结识的农村朋友,在怀旧情感的发酵中,又恍惚置身于青年时代。但当最初迷醉的热情过后,他们会发现年轻时的朋友已不再是从前的朋友,二三十年的时空,城乡差距,文化落距使他们心灵的距离越拉越大,友谊会随时光流逝逐渐冲淡,而这一次则是永远的梦破。迄今为止,还没有知青影视描写到这一层次。
任何一代人,站在前台的“发声者”都是少数,更多的是失语者或者是屏蔽在“后台”的无照片图像,不可能要求艺术百科全书式地反映每个个体的遭遇。随着知青年代离人们愈来愈远,知青们年龄日增,青春远去,在回归情感的驱使下,在“追忆似水年华”的白日梦中,他们“轻易地与历史和解了,在回忆中圣化了苦难,大写了青春,以致不约而同地把对一个时代的批判,最后归结为对之的赞美”①。我们在阅读知青影像时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