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工业问题是一个既关乎现代市民社会又关乎国民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缺少相关考察的《巴黎手稿》无法妥善兑现其理论意图。1844年的文本群(包括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和《德法年鉴》文章,以及恩格斯和格奥尔格·韦伯的材料)中浮现的若干线索,一致指向工业问题。经过重构的《巴黎手稿》工业形象表明,马克思深知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特殊性,即工业相比农业来说具有远为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它既是生产力的广泛联合形式,也是社会关系的粘合剂;此外,工业最紧密地结合了自然科学技术的成就,其典型表现就是机器(特别是蒸汽机)的大量引入,工业由此得以充分彰显人的本质力量,并彻底重塑其生产空间和生产者。马克思同样深知工业劳动乃是异化劳动的发达形态。他凭借鲜明的历史意识并在法德学者的提示下发现,为英国带来繁荣与灾难的普遍工业劳动,是异化的当前极致形式和朝向异化扬弃阶段的转折点,而色诺芬笔下的农业劳动图景恰好构成非谋生活动的原型。与此相关,《巴黎手稿》中的黑格尔主义批判部分,是一种有意识但并非有计划的试探,旨在有助于理解和证成现代工业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地位。
关键词 : 马克思;《巴黎手稿》;工业问题,《德法年鉴》;恩格斯;黑格尔主义批判;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industry is a central issue that concerns both modern civil society and national economics, and the Paris Manuscripts cannot properly fulfill its theoretical intention without a relevant examination. Several clues that emerge from the 1844 set of texts, including Marx's Paris Manuscripts and Deutsch-Franz?sische Jahrbücher and the articles from Engels and Georg Weber, consistently point to industry. The reconstructed image of industry in the Paris Manuscripts shows that Marx was well aware of the specificity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the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namely, that industry has a far stronger social integrating power than agriculture, both as an extensive form of un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as the cement of social relations; moreover, industry most closely combines with the achievements of na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ypified by the massive introduction of machines(especially steam engines), which allows industry to fully manifest itself. Industry is thus able to give full expression to the essential power of human being and to completely reshape its own productive space and producers. Marx was equally aware that industrial labor is a developed form of alienated labor. With a clear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prompted by French and German scholars, he discovered that the widespread industrial labor that brought prosperity and disaster to England was the current extreme form of alienation and the turning point toward the stage of its sublation, and that Xenophon's picture of agricultural labor was the prototype of non-livelihood activities.Related to this, the section of the critique of Hegelianism in the Paris Manuscripts is a conscious yet not planned attempt to help understand and justify the logical status of modern industry and communism.
Keyword: Marx; Paris Manuscripts; the problem of industry; Deutsch-Franz?sische Jahrbücher; Engels; the critique of Hegelian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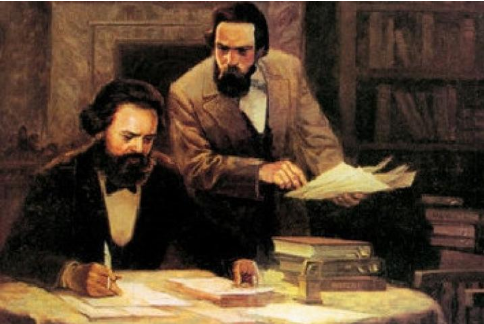
《巴黎手稿》因其残缺不全的外观、头绪纷繁的内容、跌宕起伏的出版史以及由此引发的激烈意识形态斗争,堪称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解读分歧最大、传奇色彩最浓的文本[1]66。有趣的是,恢宏且漫长的解释史总是或明确或隐含地运用德国哲学,更确切地说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作为测定《巴黎手稿》思想水准的参照系。于是,该手稿越是拘泥于或者杂糅着黑格尔历史神学框架和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成分,在基本路线或内在结构上就越不成熟,越是充斥着可见的矛盾,反过来讲,该手稿越能以历史且唯物的立场对待经济现象或经济事实,就越科学,越能为后来的思想体系奠定基础1。由于这种预先设定,研究者自然倾向于将异化论这一沾染着浓重哲学色彩的思想视为主线,着力弄清马克思的异化论及其不同阶段在多大程度上因循守旧,又在多大程度上推陈出新。因此《巴黎手稿》经常留给世人这样的印象:国民经济学是马克思批判工作的出发点,但也仅仅是出发点,有时甚至像是某种契机或者由头,而哲学才是其中根本重要的东西。这种印象的确立有其合理性,毕竟马克思此前已在黑格尔主义氛围中浸淫多年,他将这种前理解引入那时刚启动不久的经济学研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我们有没有可能建立其他的观测坐标呢?
现在或许是时候正视《巴黎手稿》序言草稿对读者提出的要求了。马克思这样写道:“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2]289-290这里有四个要点:1)读者应当预先充分了解国民经济学;2)分析工作的完全经验性;3)研究所抱持的认真态度;4)研究本身的批判性。前三点意味着有一些人,例如某些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和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也钻研国民经济学,甚至发表过相关主题的着作,但由于在这个领域涉猎有限,或由于没有掌握足够的实证材料,或由于不屑于细细推敲经济学的各种观点,故而难免不得要领。上述第四点意味着,马克思研究工作的宗旨不是去单纯否定国民经济学(这种做法尤其在空想社会主义者中并不罕见),而是要澄清其前提,划定其界限。既然国民经济学是对现代市民社会的解剖和科学反映,那么,现代市民社会就构成国民经济学的先决条件和适用范围——只有充分把握那从根本上规定着现代市民社会的事物或力量的实际面貌,才能准确评估国民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的相关批判研究。工业正是我们要找的这种事物或力量,工业问题也正是一个既关乎现代市民社会又关乎国民经济学的“核心问题”[3]67-68。若没有对工业问题的充分考察,《巴黎手稿》就无法妥善兑现其拟定的理论意图。现有研究文献大多仅仅对该问题一笔带过,未能洞悉它对于理解《巴黎手稿》的关键意义。实际上,在1844年,工业正在强有力地扫荡旧世界和开辟现代性的新尺度(不妨称之为“工业现代性”),这最典型地体现在英国和法国。马克思不仅在巴黎(1845年又有机会在布鲁塞尔和曼彻斯特)目睹了工业时代的降临,而且主要通过法语学者和德语学者的报道了解到工业问题在英国的最新情况。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认识,工业现代性与政治现代性(由法国大革命及其“人权宣言”所代表)、哲学现代性(由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法哲学所代表)一道,共同为人类(当然首先是欧洲人)定义了何为现代世界,或者说现代世界与前现代世界的根本分野。马克思作为一个如此重视站在原则高度谈论事情的思想家,不可能不知道唯有经由工业问题才能把握住现代社会巨变的主线,不可能不知道“劳动”“生产”或“制造”只是随着工业现代性的到来而上升为人类生活的主要关键词,不可能不知道经济维度只是在工业时代才从幕后走到前台、真正彰显自己的决定性力量,不可能不知道历史意识和时间规划(例如工厂作息表、铁路时刻表)只是通过工业世界的形成而全面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因此,笔者拟从工业问题的角度重新考察《巴黎手稿》,这种考察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梳理1844年文本群中浮现的若干线索,既涉及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和《德法年鉴》文章,也涉及马克思当时的密友恩格斯和格奥尔格·韦伯(Georg Weber,1816-1891)的材料。笔者认为,这些文本显示出某种协同性,一致指向工业问题这条主线,也就是说,该问题在《巴黎手稿》那里并非横空出世的东西。第二步是重构《巴黎手稿》中的工业形象,涉及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特殊性,和作为异化劳动发达形态的工业劳动。有必要在此指出的是,1983年,亦即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部分第2卷(MEGA2/I/2)出版的次年,在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坐拥手稿原件的罗扬先生凭借其令人肃然起敬的考证和推断,要求消除交叉形成的各种马克思文本之间被人为划定的界限[4]123-170。自此以来,无论人们是否接受罗扬的某些或多或少激进的判定,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置于广阔的文本群中加以考察,已逐步成为学术界努力的方向,本文也正是带着这种方法论意识进入《巴黎手稿》的。
一、1844年文本群中浮现的若干线索
我头脑中正酝酿着一个宏伟的题材,同这个题材相比,我以前所写的一切东西不过是儿戏。
——恩格斯
(一)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两处值得推敲的表述
第一处值得推敲的表述,在《巴黎手稿》笔记本对笔记本第页的第二次补充的开篇。笔记本(马克思以罗马数字标注的页码截止于第页)虽有或多或少的散佚,但却无疑构成整部手稿的核心内容。这次补充的意义很特别,因为:1)它是《巴黎手稿》最后一次补充,补入之处位于笔记本相当靠后的位置,按通常的写作习惯,此处应该出现笔记本的阶段性思想总结,创作意图应该渐趋明朗,文献的融会贯通亦应达到较为完善的程度;2)写在前面的第一次补充仅占四分之一页纸,马克思显然感到意犹未尽,经过一番酝酿之后再次补入,而这回补充的文字洋洋洒洒、篇幅悠长,事实上已经喧宾夺主。这次补充开宗明义地提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马克思紧接着按照逻辑的次序(而非历史的次序)叙述了这条道路从“最初”到“最后”的各个发展阶段,共产主义构成这里的“最后”阶段亦即自我异化的扬弃阶段(马克思随后同样按照逻辑次序叙述了共产主义本身的各个环节,在此不赘述)。这就意味着,共产主义之前的倒数第二个阶段,必定是异化状况臻于极致从而完全暴露的阶段(而且这个阶段本身也可以像共产主义那样,进一步在内部划分为若干环节)。该阶段的相应表述是:“圣西门则相反(即不像重农学派或傅立叶那样高扬农业劳动——笔者注),他把工业劳动本身说成本质,因此他渴望工业家独占统治,渴望改善工人状况。”[2]228马克思的意思简洁明了:圣西门为工业赋予优先性,工业劳动与农业劳动相对,工业家和工人在这个意义上具有利益连带性。但事情恰恰在这里变得有些蹊跷。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马克思这里将工业和农业设为对立范畴,从而对工业做了狭义理解,可一旦翻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者给出的材料依据,即圣西门的《实业家问答》,我们立刻发现书中的“实业家”(跟马克思的“工业家”是同一个词)明明包含农业劳动者。实业家或实业阶级的人员构成问题,是该书自问自答的第一个问题。圣西门明确指出:“实业家是从事生产(produire)或向各种社会成员提供一种或数种物质资料(moyens matériels)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或生活爱好的人。可见,播种谷物或繁殖家禽的农民是实业家;马车制造匠、马蹄铁匠、制锁匠、细木工是实业家;制造鞋帽、麻布、呢绒和开司米的工厂主也是实业家;商人、货运马车夫和商船的海员同样是实业家……他们构成三个大阶级(grandes classes),这三个阶级叫农民(cultivateurs)、工厂主(fabricants)和商人(négociants)。”2那么,我们必须追问:马克思为何在表述圣西门的观点时出现疏失?更确切地说,他究竟从何处意识到工业和农业的重要区分,并将工业优先性学说跟圣西门联系在一起?实际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注意到工业本身相对于农业的特殊性和应予优先发展的战略意义3,从而对工业问题变得极为敏感,另一方面,马克思又通过法国圣西门主义者,例如舍伐利埃(Michel Chevalier),注意到现代工业的成就和工人阶级的悲苦4,两种知识来源合力促成了最终的偏差5。马克思未必认同二人的学术立场和未来方案(比如舍伐利埃要求用时代的道德观念调整国民经济,李斯特要求建立贸易壁垒和关税同盟),但这丝毫不妨碍马克思受益于他们对事情的观察和评判——毕竟马克思深知蒲鲁东的如下教诲:“每一种谬误都有某种真正现实的东西作为自己的对象”,因而我们必定能在社会科学家的书里找出他们“不自觉地放在里面的真理。”6马克思写于1845年秋的《评李斯特》,有一段话或可巩固我在这里的判断:“圣西门学派狂热赞美工业的生产力。它把工业唤起的力量同工业本身即同工业给这种力量所提供的目前的生存条件混为一谈了。当然,我们决不能把圣西门主义者同李斯特这个人或德国庸人等量齐观。”[5]259圣西门主义者跟李斯特肯定不同,但正因为双方都高扬工业的意义,才会让读者误以为他们志同道合,马克思的提醒也才不致流于空穴来风。
另一处值得推敲的表述在《巴黎手稿》序言草稿。马克思在那里明确宣称,自己在《德法年鉴》上面“十分概括地提到过本着作的要点”[2]290。也就是说,《德法年鉴》构成理解《巴黎手稿》的关键先决条件,这是由马克思本人确认的事实。实际上,《德法年鉴》是这篇极为简短的序言(特别是其中保留下来的正文草稿部分)里面三度援引的作品。马克思没有在此具体指明《德法年鉴》中的篇目,不过我们有理由认为首先(但并不仅仅)指向《〈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第一,《巴黎手稿》序言草稿开篇首句即为“我在《德法年鉴》上曾预告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虽然该句引出的第一自然段的论证在笔者看来不甚明朗,但马克思显然在指示读者主要联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来理解《巴黎手稿》。第二,马克思在十五年之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中,同样暗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构成自己巴黎时期研究工作的主要前奏。如果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有什么地方直接论及作为《巴黎手稿》主题的国民经济学批判,那必定主要包括下面两段话:
“工业,一般而言的财富世界,对政治世界的关系,是现时代的主要问题之一(Das Verh?ltnis der Industrie,überhaupt der Welt des Reichtums,zu der politischen Welt ist ein Hauptproblem der modernen Zeit)。这个问题开始是以何种形式引起德国人的关注的呢?以保护关税、贸易限制制度、国民经济学的形式。”7
“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喷薄而出的工业运动,对德国来说才开始形成(Das Proletariat beginnt erst durch die hereinbrechende industrielle Bewegung für Deutschland zu werden),因为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工制造的贫民,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8
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文中一方面不得不囿于“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主题限制,另一方面又在努力揭示工业现代性的普遍原理,后者属于《巴黎手稿》序言草稿所说的“要点”,这是不会弄错的事情。相比之下,同样刊登于《德法年鉴》的《论犹太人问题》,旨在借助犹太人的解放这一契机,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分析封建制向现代的转型,其中的客观维度指向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分结构(文章第一部分),主观维度指向所谓“犹太精神”(文章第二部分),亦即“商人的民族”的那种利己主义和金钱崇拜的心态。在本人看来,《论犹太人问题》对应着18世纪的尺度(18世纪既是完成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世纪,也是“商业的世纪”,尽管商业在之后的世纪依然举足轻重),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对应着19世纪的尺度(19世纪是工业的世纪和社会革命的世纪),于是,两篇文章在《德法年鉴》中的实际排印顺序就不难理解了,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优先于《论犹太人问题》,尽管这跟成稿顺序无关,甚至可能恰好与之相反9。
(二)马克思密友方面的一些需要留意的情况
再来看看马克思巴黎时期密友方面的一些情况。我们在此暂不讨论卢格和赫斯。马克思和卢格虽在巴黎比邻而居,但二人在1844年3月即已决裂。也是在这个月,赫斯从巴黎回到科隆,他和马克思当年似未保持书信往来,而且他所撰写的得到《巴黎手稿》首肯的几篇文章均已在此前发表或成稿。更何况无论卢格还是赫斯,都没有表现出深入探究工业经济事实的兴趣。有鉴于此,我们不便根据他们的情况推断马克思在1844年夏天的最新思想动向。这里重点谈谈恩格斯的情况,然后简要谈谈韦伯的情况,他们在此具有更明显的优先性。
按马克思的回忆,从《德法年鉴》刊发恩格斯的文章之后(即1844年2月),他便同恩格斯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但由于某些令人遗憾的缘故,马克思1844年致恩格斯的书信一封都没有保存下来,而恩格斯1844年10月之前致马克思的当年书信也未流传下来,这就是说,我们无法得知当年二人之间的讨论或者争论。但恩格斯的《德法年鉴》文章无疑有助于我们间接捕捉马克思的思考新动向。事实上,正是恩格斯那种明显能够弥补青年黑格尔派知识结构盲区的探讨,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并强化了马克思那里已经隐约预感到的一些基本问题意识(但不能由此认为马克思先前并不在意政治经济学,只是因为受到恩格斯先行工作的刺激才决意开展相关研究)。恩格斯的《德法年鉴》文章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此处研究的切入点,以便打通去往《巴黎手稿》思想世界的道路。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1)《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约写于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至1844年1月中旬)以及同样发表于《德法年鉴》的恩格斯另一篇文章《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约写于1843年10月至1844年1月中旬,本文简称《评卡莱尔》),在何种意义上符合《德法年鉴》的办刊宗旨?2)恩格斯不仅跟马克思保持通信,而且在1844年8月27日至9月6日旅居巴黎期间拜访马克思(实际上就在马克思那里下榻),当时马克思《巴黎手稿》笔记本的写作已经接近尾声,因此值得追问的是:恩格斯在同马克思会晤之后有何非同寻常的转变?
就本文的论证而言,可用工业问题一并作答。对照卢格分别用德文和法文撰写的办刊方案以及马克思用法文撰写的办刊方案,可以看到,恩格斯的两篇文章既不是在评介莱茵河两岸(主要指德法两国)出版的书籍(《过去和现在》是在伦敦出版的英文着作),也不是在议论各类反动报刊或进步报刊的倾向、态度或公共影响。如果说恩格斯的文章符合《德法年鉴》的宗旨(创刊号发表“跑题”文章是难以想象的事情),那必定是因为其中讨论了“具有有益的或危险的影响的人物和学说,以及当前的政治问题,不论它们涉及的是宪法、政治经济学还是国家机构和道德风尚”(马克思的提法),或者说“有影响和有重要意义的人物和学说……目前大众关注的问题……宪法、立法、政治经济学、道德风尚和教育”(卢格德文版方案的提法)或“对社会的未来具有有益的或危险的影响的政治、宗教或社会学说”(卢格法文版方案的提法),并且契合“对震撼整个欧洲社会的各种问题作出哲学和政治的回答”(卢格法文版方案的提法)这个总目标。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者已经注意到,马克思和卢格在方案的表述上并不一致(这主要涉及方案的第2项、第3项),但在恩格斯文章所符合的方案第1项上恰恰比较一致[6]215,662-663。此外,在我看来,恩格斯的文章尤其符合卢格法文版方案的表述,即指向那些不仅震撼整个欧洲而且昭示德国和法国社会前途的事情,也就是说,恩格斯所考察的当前英国事务和产生重大影响的英国学说并不专属于英国,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德国社会和法国社会的未来。
我们先谈谈恩格斯的《评卡莱尔》,因为这篇文章与《德法年鉴》办刊宗旨的关联更加暧昧,也因为它在发表之初赢得了超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声誉[7]18-19。《过去和现在》至少就其中为恩格斯看重的部分而言,其研究对象是英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作者卡莱尔试图对比英国的12世纪和19世纪,这种对比即便不是严格恪守、至少也是比较趋近托利党人的立场的,也就是说,卡莱尔敌视工业“这个英国社会的中枢”、这个为辉格党赋予财富和权力从而成为辉格党唯一立法目标的手段,顶多退而求其次地谴责工业是“不可避免的祸害”,“以维护工厂工人反对工厂主为己任”。在恩格斯译出的书中“令人惊叹的精彩段落中最精彩的地方”,卡莱尔表示,卓有成效的英国工业虽然创造了“充裕的财富”,却在本国的1500万工人中间造就了庞大数量的赤贫者(卡莱尔提供了令人发指的佐证材料),与此同时,资本家(“劳动的先生”“工业海盗”)和土地占有者(“寄生的先生”)“也没有更幸福”。最后结果是,“在过剩的充盈中人民却死于饥饿”。于是,终于爆发了作为《过去和现在》写作契机的1842年8月曼彻斯特工人的大规模反抗行动,英国人再也无法回避“工人阶级的最后命运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的叙述是有所取舍的,他跳过了《过去和现在》第一篇的后面几章和整个第二篇,直接切入题为“现代的工人”的第三篇。卡莱尔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惊人的工业生产过剩,这一点导致“到处是混乱,没有秩序,无政府状态,旧的社会联系瓦解,到处是精神空虚,思想贫乏和意志衰退。——这就是英国状况”。由此可见,卡莱尔至少“正视事实”并且“正确地理解了眼前的现状”,这种事态正在为包括德国和法国在内的欧洲列国开辟新的纪元[6]495-525。我们知道,无论是恩格斯还是马克思,后来都没有为这篇文章赋予像《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那样的显赫地位,但我们不能就此认定前者的主题不如后者的主题来得重要。造成这种际遇差别的关键原因在于:第一,前者关于工业灾难的讨论只是对卡莱尔观点的翻译或述评,恩格斯自己的正面论述较少,而卡莱尔的着作本身又不那么值得推崇,至少法国学者比雷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更加出色;第二,恩格斯次年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同一主题上完全超越了卡莱尔,从而使那篇评论降格为单纯的历史材料。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无论在《巴黎手稿》序言草稿中,还是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都颇为赞赏恩格斯这篇文章:前者同时对恩格斯的名字及其作品的标题做出强调(仅恩格斯一人有此殊荣),后者称这篇文章是“天才大纲”。这篇文章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真正发轫,它在批判经济学范畴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是无论如何不能被低估的。但其中为当代学者所看重的对于私有制和商业竞争的抨击与分析,在同时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中不难找到,只是恩格斯的文笔更加明快犀利,比较符合他所理解的生动而犀利的“现代风格”。他在写作中充分结合了自己的从商经验,这当然是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不具备的优势,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也过多拘泥于商业的视野。文中指出,国民经济学产生于“商人的彼此妒忌和贪婪”,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取代了原先那套既简单又不科学的“生意经”;商业是私有制“最直接的结果”;价值是由商业设定的首个范畴;作为中心研究对象的竞争现象及其与垄断之间的辩证运动,被视为围绕供求关系相互适应过程而形成的商业事实,由此引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也被称为“商业危机”[6]442,446,449,461。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们不妨看看马克思1844年对这篇文章的反应。据考证,马克思在《巴黎手稿》笔记本和笔记本之间摘录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也就是说在初次阅读这篇文章的半年之后,马克思即意识到恩格斯那里存在有待挖掘的元素。这次摘录行为在性质上类似于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绝对知识”的摘录,旨在唤醒记忆和深化理解。这份摘要将恩格斯原文以分割线划定的15节内容(共计62个自然段),浓缩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比较长,主线是商业。马克思在开篇即对“商业”(Handel)一词做了强调,并通过整份摘要仅有的三个冒号,将商业摆在私有制统治下的经济运动过程的枢纽位置。第二部分比较短,主题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部分没有强调任何地方,而且较少使用完整的句子,写下的多是短语型的索引,它们似乎暗示恩格斯这方面的讨论对马克思来说只具有一般的方向提示作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摘要所在笔记本的封面左下方,有恩格斯纵向手书的下萨克森谚语“有人死就有人生”(Den einen zyn’blood/Is den anderen brood),可能写于1844年旅居巴黎期间(那时马克思向他出示过自己的笔记本)。这句谚语仿佛一则预言,昭示着马克思对恩格斯既有认识水平的超越(以及恩格斯正在酝酿的自我超越)[4]138-139[5]3-4[8]57,396-397,400,406。那么,对这个阶段的马克思来说,《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有没有留下什么易被当代学者忽视的发展线索?请留意,这篇文章的倒数第二自然段强调了“尤尔博士”(Dr.Ure),此人着有《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如果考虑到全文(《德法年鉴》上的排版共占29页)在长达26页的篇幅内只强调过两个人的名字,这处强调的分量可见一斑。正是在尤尔的启发下,恩格斯在结语处向读者预告:“考虑到机器的作用,我有了另一个比较远的题目即工厂制度;但是,现在我既不想也没有时间来讨论这个题目。”10这则预告跟《评卡莱尔》末尾的以下预告相得益彰,并且在我看来共同支撑着马克思与之不断通信的兴致,即“写完这篇总的绪论以后,我还打算在本杂志的最近几期比较详细地谈一谈英国状况及其核心问题工人阶级的状况”[6]524。不消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正是恩格斯兑现自己理论承诺的阶段性成果。与此相关,颇能说明问题的是,恩格斯在结束巴黎之行的当月(1844年9月)立即着手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须知,该着作的准备期接近两年(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恩格斯花了半年多(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才在德国巴门完成这部中等篇幅且重在经验描述的书稿,说明他此前并未真正动笔。可是,恩格斯本该早就动笔了(事务缠身似乎不构成充分理由),毕竟在曼彻斯特工作期间已有多篇堪称铺垫的文章问世,毕竟在英国写作这类主题的书籍显然具有随时补充当地素材的巨大便利。恩格斯的实际动笔时间紧跟在马恩巴黎会晤之后,出版时间(1845年5月,亦即3月杀青后没有立即付印)紧跟在马恩布鲁塞尔会晤(1845年4月)之后,这恐怕不是巧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写作出版一定受到了马克思当面的强烈敦促和热情勉励(不难想象,恩格斯曾向马克思分享自己搜集的材料和完成的初稿)。
我们知道,《德法年鉴》在1844年2月出版第1期、第2期合订本之后,即因经费困难、刊物遭罚没、撰稿人遭通缉、两位主编之间的分歧甚至决裂等原因而停办。恩格斯没有机会在《德法年鉴》发表“英国状况”系列研究的续篇,但他确实在1月初至2月初紧接着一鼓作气地完成了《英国状况十八世纪》。这篇文章属于恩格斯在1844-1847年构思的“英国社会史”研究的一部分,其核心内容就是描述现代工业在英国的降临及其社会后果。他这样总结道:“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6]546有趣的是,这篇文章在压了半年之后,在恩格斯赴巴黎造访马克思期间突然发表于巴黎的《前进报》(马克思从1844年夏天开始参与操办),在8月31日和9月4日、7日、11日分四期连载。根据马克思的《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从投稿到用稿的间隔可以推知,《前进报》的用稿周期不长,这就意味着恩格斯的文章可能是在他抵达巴黎前后才由马克思牵线提交的(访问该报编辑部也是恩格斯巴黎之行的目的之一)。此外,相比1843年和1844年早期,恩格斯在1844年5月下旬和6月份(《巴黎手稿》笔记本I的动笔时间)的作品呈现出关注焦点的某种偏转,这或许亦可反映正在与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的马克思方面的思想进展情况。我们看到,恩格斯原先更加关注的是英国的政治事务(集会和游行)、法律事务(议会法案的审议)、教育事务(社会主义者的工人宣传和书刊印行)、英国社会主义者的欧陆同道思想发展史。相反,恩格斯在1844年5月25日、6月15日、6月29日陆续发表的通讯报道,明显更多关注工业状况和工人问题(包括巴伐利亚啤酒因税涨价引发的四日工人骚乱、里昂附近矿区的矿业工人罢工、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并且经常出现一期报纸上发表两篇这类报道的情况(这显然不能用当时没有其他事情可以报道来解释),足见恩格斯的热切心境,其中恩格斯尤为详细地报道了西里西亚事件(德国无产者的首次阶级暴动)的过程和起因,而我们知道,该事件是影响《巴黎手稿》写作的最重要外部动因之一11。
为进一步巩固本文的推测,我们不妨再看看格奥尔格·韦伯的情况。韦伯在1844年6月或7月跻身《前进报》的撰稿人行列,与马克思过从甚密。韦伯在《前进报》发表了四篇谈论经济问题的文章,即《黑奴和自由奴》(1844年7月20日)、《普鲁士官方的慈善活动》(1844年8月3日)、《阿尔萨斯奥斯特瓦尔德移民区》(1844年8月10日)和《货币》(1844年8月28日)。前三篇文章主要在讨论现代工业和工人状况的问题,《货币》则不失为有关工业运行条件的考察(跟“货币片断”和“穆勒评注”类似)。我们知道,这批文章不仅吸收了马克思在《前进报》编辑部会议上的意见,而且直接利用了马克思的手稿和笔记。例如,韦伯把“整个工厂—工业”视为“财富的主要来源”。他看到:“不幸的工业奴隶,不单是由于身边有同他竞争的工人,不单是抗拒劳动,而且由于自己的劳动,正在走向死亡。”他发现:“工厂主之所以也决不希望有奴隶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所谓的自由人更廉价地进行生产,是因为他们必须将奴隶喂饱,但是他们可以让自由的工人挨饿!”他呼吁消除“主要因工厂—工业的进步而引起的”赤贫现象[6]625,627,636-637。笔者同样要说,韦伯抛出这些论断恐怕也不是巧合,至少从韦伯自身的特殊兴趣那里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不消说,马克思深深影响着韦伯的观察角度和构思方向。
二、重构《巴黎手稿》中的工业形象
旧的科学没有教导我们去了解和预防新的灾难。
——西斯蒙第
现在,我们如果再次翻阅《巴黎手稿》,会更容易觉察那些被异化概念或德国哲学批判的普照光芒掩盖了生动色彩的细节。下面我们试图结合马克思在1844年夏天业已掌握的思想资源和业已具备的生活经验,从两个角度重构《巴黎手稿》本身在工业问题方面详细讨论或者至少有所提示的内容,从而凸显该问题在这部手稿中的重要地位。虽然马克思此时在工业运转的实际细节方面的知识不及恩格斯,但诸多迹象表明,马克思正在酝酿着有关工业世界的更具气象的理论洞察。
在进入正题之前,应当首先说明《巴黎手稿》里面与工业问题相关的若干概念。“Industrie”既可以指严格意义上的工业,从而与农业和商业相并列且相区分,也可译为广义上的“产业”或“实业”。直接由该概念构成的一组词汇包括“industriell”(工业的)、“Industrielle”(工业家)、“Industrialismus”(工业主义)、“Industrieherrschaft”(工业统治)、“Industrieherr”(工厂主,宜改译“工业主”)、“die produktive Macht der Industrie”(工业生产力)、“industrielle Bürger”(工业资产者)、“industriellen Unternehmer”(工业企业家)、“industrielle Capital”(工业资本)、“Industriearbeit”(工业劳动)、“Fabrikindustrie”(工厂工业)、“Industrieschacher”(以产业形式牟利的行为,宜改译“工业牟利”)等。“Manufactur”常与“Industrie”混用,但严格说来应该译作“工场手工业”,中译者有时不加区分地译为“工业”或“制造业”。按照《巴黎手稿》援引的威廉·舒尔茨1843年着作中的描述,“Manufactur”位于劳动发展的第三个阶段,高于“手的劳动”(Handarbeit)和“手工”(Handwerk),但尚未达到“机器方式”(Maschinenwesen)的水准,算是初步发达阶段的工业[9]39。由它构成的词汇例如:“Manufacturkraft”(工业力)、“Manufacturproduktion”(工业生产)、“Manufacturnation”(工业国)、“Manufacturherr”(工场主)。此外,“Fabrik”(工厂)与工业问题密切相关,它在19世纪是工业的主导组织形式,经常成为时人争议的焦点。它有别于传统的手工工场,正如《巴黎手稿》曾出现“工场和工厂”(Manufactur und Fabrik)的表述。由它构成的词汇例如:“grossen Fabrik”(大工厂)、“Fabrikwesen”(工厂制度)、“Fabrikarbeit”(工厂劳动)、“Fabrikarbeiter”(工厂工人)、“Fabrikant”或“Fabrikherr”(工厂主)。需要说明的是,农业(Agrikultur)也可以作为广义“Industrie”的一种12,但不可归入“Manufactur”的行列。总的来看,能够恰当表示工业现代性的词汇显然是“Industrie”及其派生词(例如“工业革命”)。但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因为外延宽泛而引发的不必要混淆,人们(包括马克思)往往使用“现代工业”“自由工业”“工厂工业”“机器大工业”之类的术语,本文以下讨论的工业也主要指这层意思。同样有必要说明的是,在19世纪上半叶,西方工业的门类已蔚为大观,包括纺织业(丝、麻、毛、棉等)、皮革制造业、瓷器制造业、玻璃制造业、酿造业、建筑业、船舶业、冶炼业、机器制造业、采矿业等,但其典型代表是作为轻工业的棉纺织工业(作为重工业的钢铁工业在19世纪下半叶逐渐取而代之),棉纺织工业也是青年马克思工业思想的主要经验原型。
(一)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特殊性
我们看到,《巴黎手稿》在谈及工业部门的特殊性时,主要以农业部门为参照系(当然这里首先指尚未经过工业方式洗礼的传统农业)。二者都是物质生产运动的主要分支,但彼此有着根本的差别,这些根本差别只是到了工业革命之后才极为真切地显示出来。
1. 社会整合力。
在英国那种通过原始积累阶段的圈地运动而令大地产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农业人口相对于土地面积来说星星点点、微不足道;在法国,地产析分(尤其在大革命之后)愈演愈烈,小土地所有者多如牛毛(据说里程不长的圣日耳曼铁路在修建过程中需同近千名土地所有者谈判),一个人拥有的地块常常相隔甚远,而且所有权移转速度极快(从法国当地火热的地产销售广告可见一斑)[9]29-33。无论是在哪一种情况下,农业都是一种分散的、孤立的、沉闷的生产活动,它对人口的需求并不旺盛,一般不会随着劳动力密集而等比例地提高生产。农民之间的社交联系(相对工厂工人而言)本就淡薄,加之相邻的农民在产品种类和消费需求方面大同小异,精神交流和物质交换更显得没有必要。相反,按照马克思的“萨伊《实用政治经济学全教程》摘要”,工业“使人与人的关系不可或缺”(rend indispensables les relations d’hommeàhomme),它是“社会的粘合剂”(ciment de la société)[10]331。这首先是由于工业为了“共同的生产目的”,将大宗物质财富跟多样化的技艺(因而庞大数量的工业人口)“广泛结合”,或者说,将“无理智的自然力”和“生产性的人力”在相当大的规模上“联合起来”[2]178,186[9]27。工业的这种结构既是分工高度发达的产物,又力求在一定范围内克服分工。其次,工业具有高度的内部相互依存性,任何一种工业的成功发展都需要其他众多工业门类的密切配合(即所谓上下游产业链)。某种工业若是稍稍停顿,机器便不啻于一堆废铁,先期投资遭受难以挽回的重创不说,等待着它的还有难以承受的违约风险,于是人们常常看到企业家宁愿亏损也会继续挣扎着生产;至于某个工业部门发生倾覆的情况,那更会严重动摇整个国家工业体系的根基。这样的事情在农业领域是无法想象的。最后,工业在现代所汇聚的资本体量和调集的社会资源是农业难以望其项背的,工业力量和农业力量决不可同日而语。工业为了自身的顺畅运转,必定到处大力推动交通运输状况的改善、通商路线的开辟、殖民地的建立和信用业(其完成形式正如“穆勒评注”所言是银行业)的更新,从而在国内各个城市之间以及世界各个商埠之间建立极为紧密的纽带,这些都是农业国在所谓自然趋势下不可能迅速取得的成就[11]45,140,150,176,196,283-284。有鉴于此,工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所占比重,以及劳动人口在工业中的分布状况,就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现代化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等于工业化。
2. 科技结合度。
自然科学的变革和新兴技术的应用,无疑有利于农业设施的改进,从而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科技跟工业的结合程度远为紧密。“工业是科学与技术的成果,也是科学与技术的支持者和保护者。”[11]195英国的例子已经表明,对于工业的大踏步前进而言,正确的商业政策自是不可或缺,但关键在于科技进步。工业国家必然流行和信奉科学。科技与工业的历史性结合,召唤出机械力量这一强悍的物质力量,它让残疾人、妇女或者孩童能够轻易完成远超最强壮人力的工作量,棉纺织工厂之所以能够雇佣极高比例的女工和童工,主要原因就在这里。作为机械力量的代表,蒸汽机的出现是划时代的,采用蒸汽机的工业乃是工业的工业。遗憾的是,德国的哲学和历史编纂学,对科技要么不闻不问(或者没有真正的能力去过问),要么轻描淡写。相比之下,马克思在圣西门学派的影响下激动地发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2]238人的本质力量在艺术、哲学等那里还是隐微的东西,而在采用蒸汽机的工业那里则得到“显白的展示”(exoterische Enthüllung)。由此,对自然的人化改造在加速进行,“人本学的自然”(anthropologische Natur)在加速形成。但是,马克思没有被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冲昏头脑。他知道,并以两处“尽管以异化的形式”这样的提法表明:科技虽然通过工业而日益渗透到人类的生活实践之中,给人类带来解放的福音,但它不得不把“非人化”(Entmenschung)的加剧作为自己的直接效果。这意味着工业在充当社会粘合剂的同时,并未塑造众志成城的团结状态,一旦危机降临,社会随时有解体的风险。人类既苦于工业科技的不发展,又苦于工业科技的发展。伟大而多难的19世纪,不得不比先前任何时代更加深陷于“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激烈对抗[2]239[12]580。不过,蒸汽机的作用不仅是提高工业生产力,它还大大改变了工业的地理分布。农业的地理分布取决于土地的肥沃程度和析分状况,但总是集中在农村,毕竟农业离不开土地这个主要物质载体。工厂比土地灵活得多,工厂的位置首先取决于能源供应,因而也可以说,工业史同时也是能源史。早期工业主要利用水力,因此工厂选址必须靠近能够提供相当规模稳定水流的河川(为此有时需要配套建设水坝等基础设施),这种工厂经常位于旷野,那里虽然地价低廉,但往往很快遭遇劳动力供给的瓶颈。正是蒸汽机拓展了工业生产的空间选择自由,从此,工厂纷纷转入城市(这样也更容易找到充足的雇佣劳动者),迅速在此汇聚的劳动者和财富为人类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城市形态,这就是马克思在“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摘要”中关注的大型工业城市(die grossen Industriest?dte),那时最典型的当属恩格斯正在考察的曼彻斯特13。
马克思借以理解工业特殊性的进路,实际上这意味着他此时隐藏的问题意识之一是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历史转型(从国民经济指标可知,这对英国来说是完成时,对他旅居的法国来说是正在进行时,对普鲁士来说还只是初露端倪)。这实际上还意味着,《巴黎手稿》的主题首先是生产领域而非交换领域。可以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工业生产的特征问题,促使马克思认真考虑前人使用的“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以及由工业生产所决定的相关劳动者的生活方式问题。
(二)工业劳动作为异化劳动的发达形态
由于1932年以来围绕异化问题的漫长争论史,今天我们一谈起《巴黎手稿》,最先想到的多半就是笔记本的第-Ⅶ页,马克思在那里尽管保留三分栏的外观,却从左向右贯通书写,后来编者将这部分命名为“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其中关于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尤为振聋发聩。学术界对异化劳动问题的讨论汗牛充栋,在此无庸赘述,但如果我们从工业问题的角度重新阅读这段文本,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1. 历史意识之下的异化劳动。
马克思是带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切入这个主题的。这种历史意识当然要求马克思或早或晚转入经济学说史的探究(《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已提供一种预演),但正如他的“李斯特摘要”所表明的那样(即只摘录《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一、二编,未摘录第三、四编),本阶段的关注点不在于单纯的学说史知识(更不在于实用的经济政策),而在于洞悉抽象政治经济学原理本身的历史性。如果他此时看重经济学说史,本应从重商主义或重农学派甚至更早的经济学着作入手。我们看到,马克思很快判定,国民经济学试图用“一般的、抽象的公式”抹煞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于是,原本作为历史性事实的那个出发点就蜕变为一种不可动摇的、自然而然的、理所应当的东西。那么,马克思是不是要去考察私有财产的起源和演变的过程,从而戳穿国民经济学的虚伪呢?他没有这样做。他明明知道地产就是私有财产的“最初形式”和“根源”,却没有进一步考察地产的早期情况,反而向读者郑重提议“我们且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之所以说郑重提议,是因为这寥寥数语独占一个自然段,而且马克思对“当前的”(gegenw?rtigen)这个字眼做了强调。这种思路的理据何在?原来,私有财产唯有发展到“最后的顶点”(lezten Culminationspunkt),才“重新”暴露出自己的“秘密”,即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因果关系和内在互动。马克思兴奋地宣布,这种思路“使至今没有解决的各种矛盾立刻得到阐明”[2]193,199,210,227。如果说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是一体两面的东西,那么异化劳动概念就只是对私有财产这个古已有之的事物的一般解释(同理,人化自然也只是一般解释),而无法具体解释它在工业时代的独特命运,就此来说,异化劳动概念有蜕变为“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的嫌疑。马克思要求我们认识到私有财产的历史运动,就是要求我们认识到异化劳动的历史运动,更确切地说,就是要求我们秉持历史意识对待作为异化劳动发达形态的工业劳动,这才是“最后的顶点”,这才是“当前的事实”。正是在作为典型的棉纺织工厂劳动这里,原先只不过是片断、因素或预兆的东西,才呈现出容易识别的充分且完整的轮廓。马克思在十几年后把这种思路凝练为一句箴言:“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12]29但我们在掌握这种回溯方法(或者从后观看法)的力量的同时,决不能用工业劳动的考察直接取代早期劳动的考察,不能用工业劳动抹平一切时代劳动的差别,否则就背离了历史意识。
2. 色诺芬提供的劳动参照系。
《巴黎手稿》的思路表明,马克思最想要理解他所置身的19世纪及其中由工业彰显的现代性,早期情况对他来说只是参照系(因而只有次要的、辅助的意义)。马克思在巴黎时期确实摘录过一位古人的着作(仅此一位),即雅典的色诺芬。夹在一众18和19世纪的着作家中间,“色诺芬摘要”的存在乍看之下有些突兀,甚至有点滑稽。它位于编号B23的巴黎笔记本的开端,没有页码,“李嘉图摘要”和“穆勒摘要(前半部分)”紧随其后且有罗马数字编码。“色诺芬摘要”的写作时间问题,以及它究竟属于《巴黎笔记》序列抑或《布鲁塞尔笔记》序列的问题,曾经引起争议,后经考证得到澄清[13]147-149。“色诺芬摘要”的部分内容跟马克思在巴黎时期阅读的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具有相关性(当然这并不等于说马克思是因为受到西斯蒙第的启发而去摘录色诺芬的),后者专门提纲挈领地讨论过色诺芬的经济思想,其中最重要的元素都在“色诺芬摘要”第4篇“《齐家术》(德译标题是Von der Haushaltungskunst)摘要”中得到反映。西斯蒙第指出(可惜马克思巴黎时期的“西斯蒙第摘要”没有流传下来),希腊人留给我们少许研究经济问题的着作,其中列在首位的就是色诺芬的小册子《齐家术》(Oeconomicus,中译本将其译为《经济论》或《经济学》,这是不太确切的,马克思所摘录的德译本的译名更接近该词的希腊本义)。这部对话录借苏格拉底之口,申明古人的正统见解,从哲学的观点宣称农业劳动是最高贵的生产活动,并认为各个城邦对手工艺的普遍轻视是正确的。手工艺是粗鄙的事情,它损害人的身体健康,进而败坏人的灵魂和勇毅气概。相反,农业作为像战争那样直接由神掌握的事情,堪称高贵者(自由民)的最佳职业,是其他一切技艺的源泉和保障——农业不牢,地动山摇。农业劳动不仅提供某种享乐或者情趣,熏陶某种美德,还能增益财富和锻炼身体,从而使人民更有意愿和能力去保卫家园。书中最终得出结论:以农业为生是最光荣、最卓越、最愉悦的事情[14]26-27[15]13-14,18-22,53[10]391。如果说“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Erwerbsth?tigkeit)的形式出现”14,那么,色诺芬这番田园牧歌式的叙述,就为马克思树立了作为非谋生活动的劳动的原型,这种劳动既无关乎亦不计较收入和利益,反而成为体育、德育和美育的有效方式。一个人若是据此反观现代工业劳动的景象,必定感到触目惊心。
3. 工业劳动现象及其典范国度。
当马克思要求“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去追问“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对人类发展有何意味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要求直面工业劳动的现象,澄清其本质和意义。这一工作,马克思是借别人的生动文字完成的。我们看到,从工资栏第Ⅷ页开始,马克思的摘录完全是成段成段、原原本本进行的,整个过程近乎处于失语状态(可以想象,这是由极度悲悯引起的)15,最后落脚于一句很有冲击力的宣告,即“工业直到现在还处于掠夺战争的状态”16。摘录对象均为最新出版物且基本上出自马克思的巴黎藏书,包括舒尔茨的《生产运动》(1843年)、贝魁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或关于社会组织的探讨》(1842年)、劳顿的《人口和生计问题的解决办法》(1842年)和比雷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1840年)。这些人(尤其是法国人)的事实描述,涉及工人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及其可持续性、被平均计算所掩盖的劳动阶级状况的实际恶化、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分野、机器的引入或改进及其后续影响、奴隶式劳动的时间、纺织厂雇佣劳动者的性别比例和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童工数量的迅速攀升、劳动者身心状况的严重败坏、卖淫者(“马路天使”)的惊人规模、赤贫人口的相对增长和相对短寿,等等。凡此种种均以不容置疑的方式告诉马克思:工业劳动打破了“人借助机器来劳动”和“人作为机器来劳动(或者人像机器那样劳动)”之间的天然分界线,也碾碎了穷人和无产者之间的历史同一性,重新将无产者界定为完全依靠“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而这种全面商品化甚至动物化的劳动显然并不来自一般意义上的分工,只能是现代工业分工的必然产物,正如劳动阶级的贫困化不再主要源于机能、天赋、运气等偶然因素,而是产生自“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17。
当时的法语学者和德语学者一致认为,上述工业劳动景象的典范国度是英国。不过,德语学者,例如李斯特,似乎更愿意同时探寻英国工业兴起的各种历史的、偶然的和非经济的成因。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一编历史”专门讨论了英国经济(在“李斯特摘要”的范围内),认为英国几个世纪以来的主导性商业政策十分合理,国际贸易条约和专利法高瞻远瞩,世界主要航线尽在掌控,排除罗马法传统而发展出基于普通法传统的立宪自由,贵族制度尽善尽美,偏安一岛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其避开欧陆灾祸甚至每每从中渔利(比如欧陆的宗教迫害导致大量工业家和资本流入英国),等等[11]41-62。法语学者,例如西斯蒙第,则更倾向于按照工业经济的本质性规定,去把握英国工业的正面和负面因素。他指出:英国是一个“有极丰富的经验可供世界其他各国参考的国家”,“我特别为了使我的读者注意英国,我想通过英国所遭受的危机,根据全世界各种工业之间的联系,来说明我们目前的灾难的原因;我也指明,如果我们继续奉行它所遵循的原则,那我们自己未来的历史会是怎样的”[14]7,13。在英国的乡村,农夫近乎绝迹,全面让位于短工;在英国的城市,手工业者和独立的小工场主同样近乎绝迹,全面让位于大工厂主;手工织工到处被轰鸣的蒸汽动力织机取代,只得奄奄待毙。英国的今天,特别是它那极为活跃且不可抗拒的工业发展和远超其他国家的频繁破产现象,很可能成为欧陆国家明天的繁荣和浩劫的预演。按照马克思的常规思想取向(即更看重事情中的普遍性而非特殊性),西斯蒙第的这种进路比李斯特的进路更富教益。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在1845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实际采取的也是类似西斯蒙第的那种思路,他主张,之所以要把目光投向英国,是因为工业问题只有在英国才“具有典型的形式”,才“表现得最完备”[16]385。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巴黎手稿》对待工业劳动者的那种广为称引的人本主义情怀,实际上主要来自西斯蒙第,以及西斯蒙第的门徒比雷。马克思对李嘉图的那处纲领性的批判,即“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连同作为其文本佐证的那段李嘉图着作法译本摘录,正是比雷照搬自西斯蒙第而又由马克思完全承继下来的[2]183[14]457。
4. 黑格尔主义批判在手稿论证中的角色。
在此简要评价黑格尔主义批判在手稿论证中的角色,或许不是不合适的。安启念教授正确地指出:“探讨文本结构,是《手稿》研究的当务之急。”[17]然而,笔记本里面被编者命名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那个着名部分(为讨论之便,本文简称“黑格尔主义批判”),以及现存手稿本身(尤其是笔记本)客观上或长或短的残缺,始终在挑战学术界关于手稿整体构思或主线存在与否的肯定判断。《巴黎手稿》的早期编辑版本,实际上多多少少强化了黑格尔主义批判的显赫地位甚或独立意义。1927年,梁赞诺夫将笔记本的大部分内容以俄文形式率先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3卷,题为“《〈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而《神圣家族》就是直接针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性着作。1932年,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部分第3卷(MEGA1/I/3)虽然刊发了手稿的三个笔记本(此外还收录了一部分摘录笔记),但却是按逻辑结构而非写作顺序进行编排的,编者把主题相近的片断重组在一起并精心添加了各种标题(黑格尔主义批判放在最后一部分),不了解情况的读者容易误以为那些标题出自马克思之手。MEGA1版本后来直接或间接地成为1974年俄文第2版《全集》、1974年德文版《全集》(MEW)和1974年英文版《全集》(MECW)的相应底本。同在1932年,坐拥手稿原件的朗兹胡特和迈尔所发表的版本,竟然排除了笔记本,并且按照笔记本、笔记本、笔记本(即四页纸的“黑格尔《现象学》摘要”)的次序编排,于是,黑格尔主义批判得到有力凸显。尽管有MEGA1这一更准确版本,或许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手稿的1937年法文版、1949年意文版和1950年意文版皆译自朗兹胡特—迈尔版。书稿最初传入中国时也存在类似问题,无论是1935年柳若水的节译本还是1955年贺麟的节译本,都把黑格尔主义批判独立出来,并仿照1932年的先例单独命名。直到1982年MEGA2推出写作顺序版的手稿(又辅以相应“资料卷”的异文表),国际范围内的相关研究才终于有了根本转机,然而,半世纪以来确立的强大解释传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撼动的。合并重组甚至予以单行编排的做法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因为手稿序言草稿透露过类似的意图,更何况这部分内容的确看起来跟正经的国民经济学批判格格不入,给人的印象是马克思“跑题”了。我想指出的是,先前的各种逻辑结构编排版,总是多多少少遮蔽了黑格尔主义批判的写作契机和修改过程,从而影响研究者的判断。下面我想首先简单梳理一下黑格尔主义批判的文献学信息。
黑格尔主义批判部分其实是在笔记本里面分三次写成的。第一次批判始于第页,马克思在论述了共产主义的逻辑—历史地位之后,以分隔符表示这处论述告一段落,然后另起一行写道:“(6)在这一部分,为了便于理解和论证,对黑格尔的整个辩证法,特别是《现象学》和《逻辑学》中有关辩证法的叙述,以及最后对现代批判运动同黑格尔的关系略作说明,也许是恰当的。”[2]243请注意,这句话中的“(6)”“和论证”“和《逻辑学》”都是临时或随后补入的成分,而且马克思几乎是小心翼翼地提出,这里“也许”是从事该项批判工作的适当地方(der Ort)。这一工作据称同时指向“理解”和“证成”(sowohl zu Verst?ndigung und Berechtigung)。第二次黑格尔主义批判的起笔句是“黑格尔有双重错误”,该句自成一个自然段。这次批判是在第-页的经济学批判暂告结束之后,回到第页右栏留白处开始写的(该页已经几乎被关于《现象学》和《逻辑学》的讨论填满),然后在第
页右栏留白处续写,一直到第页右栏中部才结束。接下来,马克思重新回到经济学问题,从第页写到第页。第三次黑格尔主义批判从第页登场,起笔句是“因此,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一直写到第页左栏下三分之一处,篇幅相当长,分解补充之中嵌套着分解补充。“黑格尔《现象学》摘要”想必作于这一时期。马克思通过在第二次批判的结尾标注“(下接第页)”和在第三次批判的开头标注“(见第页)”,将这两次批判的文字连缀一体。鉴于第二次批判本身就始于第一次批判的页面留白处,因此三次批判的内容事实上具有直接相关性和内在连续性,尽管实际书写过程是有间隔的[2]256,258,263-264,283。
可以认为,手稿中的黑格尔主义批判部分,乃是马克思的一种有意识但并非有计划的试探,更确切地说,他在试探如何有效地理解并证成“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此为黑格尔主义批判所属整个补入内容的开场白和总纲)。马克思已经看到了症结所在,也有了许多灵感和领悟,但他还缺少一套能把众多元素和头绪组织协调起来的理论框架。把握这条二合一的“道路”的任务实在太刺激、太富有挑战性了,以至于这位年轻的试探者几乎按捺不住自己的躁动情绪——我们看到,每当临近“跑题”的时候,文本中总会出现他用红棕色铅笔做出的密密麻麻的勾画(中译本里以双斜线“//”表示起讫),这表明,有一股反复斟酌但未及渲泄的思想冲动在胸中奔涌。那么,黑格尔哲学,特别是作为其“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现象学》,何以有助于理解和证成工业劳动语境中的异化过程和异化扬弃过程?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要知道,黑格尔《现象学》的主体和主题是“精神”。答案是,马克思重构了黑格尔《现象学》,将其改造为一种方法论模型(为此他似乎一直不愿完整地拼写《精神现象学》这个标题)。他在进行第一次黑格尔主义批判时,最开始只是隐约预感到这可能是一条有前景的路径,所以显得拿捏不准,显得小心谨慎。他必须通过某种解释为这种改造找到正当理由。他很快想起,青年黑格尔派曾经尝试过一种原理相似但方向不同的改造性批判(例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卢格学说为中介而吸收的费尔巴哈式“主谓倒转”)。因此我们看到,马克思在第一次黑格尔主义批判中,认真讨论了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哲学的关系,特别是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释”(erkl?rt),并将该解释与黑格尔体系的本来面貌做比对。我们还看到,马克思其实已经通过两处不很起眼的解释(更确切地说是过度解释)而向前迈进:1)他把费尔巴哈学说解释为使得“社会关系”成为基本理论原则;2)他还把黑格尔逻辑学解释为“精神的货币”(das Geld des Geistes)、“思想上的价值”(Gedankenwerth)[18]。到第二次批判的时候,马克思更加胸有成竹,取得了重大突破:“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思维的生产史。异化……是……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其他一切对立及其运动,不过是这些唯一有意义的对立的外观、外壳、公开形式,这些唯一有意义的对立构成其他世俗对立的含义。”[2]256这里,他对“生产史”(Productionsgeschichte)做了强调,而且这个地方本来写的是“产生史”(Entstehungsgeschichte),更考究的新用词显然有双关语的意味。此外,整个第三句话是后来补入的,是对前进方向的进一步明确。可以说,这些改动预示着一种更加激进的改造工作。于是我们看到,马克思很快学会在措辞中塞进一些修饰语,比如“以一种潜在的方法”(事后补入的)、“作为萌芽、潜能和秘密”(即时添加的),借以强化改造工作的合法性。在第页,马克思终于找到一种稳妥的方式准确表述自己的总体思路:“因为《现象学》紧紧抓住人的异化不放——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所以它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2]257请注意这里的“尽管”“潜在地包含”“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准备好”等措辞。这就是第二次黑格尔主义批判的主要成果。从此以后,马克思就坚定不移地把《现象学》当作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模型。考虑到问题在于从异化的最激烈状况到异化的扬弃,就是说,问题在于从工业劳动到共产主义,或者说从现有条件下的发达工业劳动到共产主义,马克思在第三次批判中顺理成章地诉诸《现象学》的最后一章“绝对知识”。这一章包含着《现象学》精义的总结,其在总体逻辑序列中的出场位置恰好对应着发达工业劳动向共产主义转换的环节,亦即所谓“最后的顶点”,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这一章涉及的对象之复归或对象之克服的八个环节,直接有助于理解和证成整个异化过程(从原初农业劳动到现代工业劳动)和异化扬弃过程(共产主义的分化和发展)的具体步骤,以及各步骤的意义和规定。就在行将切入“绝对知识”章之际,马克思仿佛担心读者依然质疑自己的改造工作的合法性(他本人已经不再犹疑),暂停下来继续夯实既有思路:“且让我们先指出一点: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2]264这话听起来莫名其妙,马克思当然也心知肚明,所以他马上给出解释:现代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更准确地说是抽象劳动(工业劳动)视为人的本质,黑格尔也持这种立场,只不过他仅仅知道并且承认的是精神的抽象劳动罢了。终于,马克思得以坦然地把“绝对知识”章称为“我们的本题”,并提请读者跟随自己从中寻求灵感[2]265。这样,一旦明确黑格尔主义批判在论证中被赋予的这种从属角色(这是一切相关讨论首先应予正视的事情),我们就只能换用另一种视角看待如下论断,即该部分是《巴黎手稿》的一种理论的溢出18。
三、结语
工业问题是地地道道的现代问题,是现代问题的缩影和典范。工业问题贯穿着19世纪的国民经济学着作和社会主义着作,构成双方争论的共同前提和核心议题,并且为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批判赋予了特定的逻辑角色。该问题有资格成为《巴黎手稿》研究视角的一个重要的竞争备选项。一旦抓住这条线索重新看待《巴黎手稿》,我们将在1844年的马克思那里发现一条近乎直通《资本论》的道路,西方学界一度盛行的那种基于异化论本位解释框架而制造的“两个马克思”命题将被根除。如果说马克思主要是通过在法国巴黎的一般生活观察和学术阅读来把握工业问题的,那么恩格斯主要是通过在英国曼彻斯特深入工业区的实地调查来把握工业问题的,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副标题“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所表明的那样——实际上,大家如果仔细品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措辞就会发现,代表着恩格斯得出跟马克思“一样的结果”而走过的所谓“不同道路”,正是涉及工业现代性之诊断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并不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使马克思从此以后能够自豪地谈起“我们”这个字眼。
作为马克思借以理解现代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主要背景,对工业问题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宏观把握毫不意外地继续出现在《神圣家族》《评李斯特》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里且以1844年9月初开始创作的《神圣家族》为例略作说明。该书谈到“英国工业史”,谈到正在形成中的工业世界“根本不同于基督教和道德、家庭幸福和小市民福利所建立的包罗万象的王国”,谈到真正的工业活动只在行会特权被消灭之后才能发展起来,谈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是工业社会,而工业的活跃乃是资产阶级社会生命力的表征,谈到关乎工业意义的唯物主义学说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具有本质性联系,还谈到对工业问题的认识乃是真正认识某一历史时期的法门,等等[19]13,88,148,156-157,166,191。可以想见,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这种原则高度上重新审视事情的时候——这种共同达到的原则高度当然构成二人终生合作的前提条件,他们知道,共产主义学说首先是工业世界的意识形态——不仅唯物史观的轮廓逐渐明朗起来,而且德国哲学界某些学术讨论(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性质也变得极为昭彰。与这一阶段的马克思恩格斯密切相关的刊物《威斯特伐里亚汽船》[20],其刊名中的“汽船”即为颇具工业时代气息的隐喻(实际上,机器隐喻的流行正是这个时代的修辞征兆):汽船亦即19世纪初试航成功的蒸汽动力船舶,它是工业现代性的重要象征,在此喻指乘风破浪的人民力量。
习近平同志指出:“工业化是现代化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21]当前,我国已经建立“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跃升为“制造业第一大国”[22],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工业化进程远未结束。一方面,过早地出现去工业化的态势,容易使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于是我们看到,“十四五”规划纲要在位置显赫的第八章“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里面,首次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23]。另一方面,如何同时直面工业化所催生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24],如何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落实新型工业化战略,如何依靠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防范和克服西方在工业化浪潮中经历过的社会危机,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对工业现代性的观察和反思,正构成马克思始于巴黎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的一条主线,就此而言,他依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参考文献
[1]薛晓源,刘宁宁,汪海燕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读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附有按照手稿写作顺序编排的文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
[3]周嘉昕,编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导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
[4]罗扬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历史学-以所谓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赵玉兰,译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7(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8]鲁:克俭走向文本研究的深处:基于MEGA2的马克思文献学清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9]舒尔茨.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 李乾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10]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MEGA),Vierte Abteilung,Band 2 Berlin:Dietz Verlag, 1981.
[11]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13]卢姆扬策娃.论在《梅佳》2第四部分第二卷中卡尔马克思的巴黎笔记的发展1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译文集熊子云,张向东,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3.
[14]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财富同人口的关系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
[15]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张伯健, 陆大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17]安启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基本内容及全书文本结构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8(1):54.
[18]姚远马克思的治学方法澳门法学。20203)-115-116.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
[20]葛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3(1):144-160.
[21]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118.
[22]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18-12-19(2).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日报, 2021-03-13(6).
[24]习近平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在二O-九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19-04-29(2).
注释
1比如我们可以追问:《巴黎手稿》的黑格尔主义色彩看起来强于《论犹太人问题》,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在《巴黎手稿》阶段出现了思想的后退?
2(1)(法)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2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1页;Saint-Simon, Catéchisme des industriels, Paris,1823, p. 2。对实业家的这种界定,乃是圣西门的一贯态度,读者可以参阅他的《给一个美国人的信》(1817年)、《加强实业的政治力量和增加法国的财富的制宪措施》(1818年)、《论蜜蜂与胡蜂的不和或生产者与不事生产的消费者的彼此地位》(1819年)、《以促进欧洲社会改组为目的的哲学、科学和诗学研究》(1822年)等作品。有趣的是,“实业阶级”看起来等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资产阶级/资产者”,但圣西门却给“资产者”(又称“中间阶级”)下了特殊定义:没有贵族血统的军人(产生于热兵器时代的军队成分改组)、非出名门的法律人(产生于司法制度的专业化)、无特权的食利者(产生于地产分割造就的平民新贵)。在法国大革命时代,据说“资产者”因势利导地鼓动实业阶级反对贵族,成功晋升为第一阶级,并且“为了自己的利益恢复了封建制度”。圣西门由此顺理成章地表示,实业阶级的当前任务就是同时推翻贵族和资产者的统治。参见上书,第55页、67-69页。如果我们从圣西门的立场看待法国大革命的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定性,那么历史整个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了。
3(2)笔者的推断理由如下:(1)在现存《巴黎笔记》所摘录的着作中,只有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重点讨论过工业和农业的本质差别问题,尽管李斯特主要是在“Manufactur”的范畴下展开讨论的;(2)为便于理解李斯特学说,马克思在摘录时专门将其与欧西安德尔(Heinrich Friedrich Osiander)的《公众对商业、工业和农业利益的失望,或对李斯特博士工业力哲学的阐释》并列两栏对照书写,这样的待遇在《巴黎笔记》中绝无仅有,足见重视程度;(3)《〈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曾在唯一一处论及工业发展问题的地方,以双关语“listige”(狡猾的)调侃李斯特(List)为振兴德国工业提出的经济设想,这种调侃其实从另一层面反映出马克思对他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的直接后续结果就是,《巴黎手稿》结束之后的下一份经济学手稿便是《评李斯特》,而且这一次马克思利用的是他专程购置的原着(耗资8法郎),而非《巴黎笔记》中的相关摘录,参见鲁克俭:《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评李斯特〉写作时间的文献学考证》,载《哲学动态》 2012年第7期。
4(3)参见(德)罗扬《理论的诞生——以1844年笔记为例》,赵玉兰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2年第2期,第15页。赫斯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文中,把舍伐利埃称为圣西门“最忠实的弟子”,参见(德)赫斯《赫斯精粹》,邓习议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页。这层关系马克思不会不清楚,因为《巴黎手稿》序言草稿曾向《二十一印张》文集中的赫斯文章表达谢忱,其中就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5(1)这类偏差在《巴黎手稿》中还有实例,比如马克思在笔记本的第页“资本的利润”一栏写着“李嘉图在他的书(地租)中说”,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附有按照手稿写作顺序编排的文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3页。这可能表明马克思此时尚未阅读李嘉图的原着(他强调“李嘉图”的名字或许就是为了提醒自己抓紧查阅),仅仅读过他人对李嘉图学说的讨论,由于地租学说在李嘉图那里占有显要地位,马克思似乎误以为李嘉图的着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一部关于地租的书。
6(2)参见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这句话之所以给马克思留下较深印象,除了它出现在《什么是所有权》交代自身方法论的第一章之外,还因为马克思跟埃德加尔·鲍威尔(Edgar Bauer)论战时专门论及此处的含义。
7(3)中译本的相应表述是:“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页。我倾向于认为“工业”和“一般而言的财富世界”是同位语。
8(4)中译本的相应表述是:“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页。这种表述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即已经存在所谓的“德国无产阶级”,实际上,它在德国的形成情况还不完全明确,至少在1844年6月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之前远不如在英国和法国那里明确。
9(1)林进平教授指出:“不同文章在刊物中的排序,主要是依照逻辑顺序,而不是依照作者的写作时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排在《论犹太人问题》之前,可能说明前者在马克思看来在重要性上要优于后者,或如一些学者所说的,前者在思想上对后者有‘指导作用’。”参见林进平《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59-61页。笔者需要对此做出补充说明。查阅《德法年鉴》的原始篇目可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构成一组文章,都属于“朝向”(“zur”或“zu”)流行思想体系批判的某种先行准备或总体定向;《论犹太人问题》和《评卡莱尔》构成另一组文章,在形式上都属于书评,封面目录上也在对应文章下方另起一行排印了所评书籍的原文信息,而按照《德法年鉴》的办刊方案,书评理应置后排印。以上说法似乎否定了关于文章排印的逻辑次序判断,但我们应当进一步注意到,前一组文章里马克思的文章在先,后一组文章里恩格斯的文章在先,于是笔者的判断仍可得到印证,即工业和工人的主题优先于商业和商人的主题。
10(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3页。马克思后来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写道:尤尔的《工厂哲学》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无疑都是关于工厂制度的着作中最好的”,它们内容相同,但立场有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7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62页。
11(1)参见杨金海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1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517、531、548页。如果我们把时间轴回拨到1842年11月底到12月底,同样会有奇妙的发现。恩格斯在11月24日前后拜访了马克思主持的《莱茵报》编辑部,当月底即为该报撰稿。他寄自伦敦和兰开夏郡的几篇通讯,把作为“工业国”的英国的竞争困境、发展出路、阶级关系和社会革命等问题摆在核心位置,甚至有一篇简讯就叫《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5-422页。如果意识到恩格斯此前几乎没有讨论过工业经济问题,只有1839年初的《伍珀河谷来信》构成不甚明显的例外(文章主要谈宗教事务),那么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在早期阶段,每当恩格斯靠近马克思的时候,工业现代性的相关问题就立刻成为其首要关注点,而且这也成为恩格斯超越青年黑格尔派视野的重要机缘。
12(1)《巴黎手稿》曾有“Industrie(Agrikultur)”和“sie die Agricultur für die einzige Industrie erkl?rt”的表述。中译者大概感到这里把“Industrie”译成“工业”十分别扭,就改译为“生产”,于是把这两处文字表述为“生产(农业)”和“他们宣布农业是唯一的生产”。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附有按照手稿写作顺序编排的文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6页。
13(1)参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MEGA), Vierte Abteilung, Band 2, Dietz Verlag, 1981, S. 574, 578。法国学者比雷这部西斯蒙第式的社会主义着作,强有力地参与构成了马克思国民经济学批判工作的思想基质。它对巴黎时期马克思的特殊意义,可从以下事实得到说明:1)马克思不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从私人藏书中的1840年巴黎版比雷着作大量援引(因为援引内容皆未出现在“比雷摘要”中,故有此推断),还专门对它做了完整的摘录笔记,同期援引的劳顿、贝魁尔和舒尔茨无此待遇。2)在整套《巴黎笔记》中,像“比雷摘要”这样单人单书独占一册的情况极为罕见。3)“比雷摘要”中的勾销标记比较特别,用的是黑色铅笔,而其他《巴黎笔记》用的是浅褐色铅笔或墨水笔。4)由于在巴黎时期未及完成全书的摘录,马克思抵达布鲁塞尔之后,就从当地找到的另一版本继续摘录该着作,摘录内容前后衔接。这也同时意味着,“比雷摘要”构成巴黎时期和布鲁塞尔时期的重要连接点。
14(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附有按照手稿写作顺序编排的文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9页。出现在笔记本工资栏第页最后一行的这句话是马克思后来补入的,或许正由于他突然忆起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教诲。凡涉及马克思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原稿改动情况的信息,本文主要依据鲁克俭教授《走向文本研究的深处》第9章,以下不再专门说明。
15(2)笔记本中此前关于斯密和萨伊的摘录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马克思经常不是直接引用,而采取转述甚或重组的方式,突出原着者有时只是在犄角旮旯里不经意间透露的事情,例如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 1817年第3版第1卷第136页的注释中透露的历史真相,即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源自掠夺。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附有按照手稿写作顺序编排的文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5页。
16(3)这句话是从比雷的“工业成了战争,而商业成了赌博”演绎出来的,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关注点在工业而非商业,尽管这两个经济部门在实际运行中是唇齿相依的。
17(1)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附有按照手稿写作顺序编排的文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9页。在笔者看来,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之所以招致马克思的专门批判(须知马克思对《什么是财产》的更高评价主要涉及风格而非内容),一个重要原因是:蒲鲁东明明抓住了贫困这个工业时代的本质性症结,却由于在逻辑方法上异想天开(即深陷“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而损害了自身的理论分析力,因此尤为令人痛惜,尤为需要指正。《哲学的贫困》这个标题颇耐人寻味,它既点明蒲鲁东哲学功底的薄弱,同时也暗示蒲鲁东在实证材料的掌握上并不贫困。
18(1)当马克思一再深化和扩展他的黑格尔主义批判时,他发现,像这样把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和对思辨的批判直接缠绕起来固然十分有效,故而是“完全必要的”,但毕竟会冲击国民经济学批判工作的主体地位,因此应当放在“另一个场合加以详细的介绍”,这便是马克思在1844年8月底9月初开始与恩格斯合作撰写的《神圣家族》。《巴黎手稿》序言草稿里面大段删除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字,就是马克思不想在本阶段喧宾夺主的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