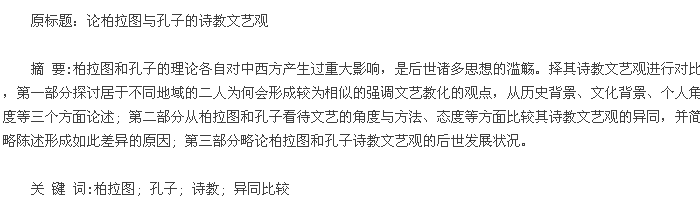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过“轴心时代”的说法,他指出,在公元前 800 到公元前 200 年之间,中国、印度和希腊等几大主要文明区域内,几乎同时出现了自己的文化先知,他们奠定了人类精神存在的基础,以及所谓的真正的人类的历史[1]。此时期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中国的孔子出生年代相距不到一百年,他们都对伦理学和政治极感兴趣,在一系列问题上表达过相似或相近的观点。他们都是见解精到的教育家,都注意文艺对人的感化作用,由此形成的诗教文艺观也有一些值得相提并论之处。
一、柏拉图和孔子重视诗教的原因
( 一) 从历史背景看,二人同处乱世,都有着强烈的救世观念,看重文艺对人的感化作用
公元前 431 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与公元前 429 年白里克里斯的逝世,就开始了雅典历史上的阴暗时期[2]115。出生于公元前 428 年的柏拉图生逢其时。旷时二十多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给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接着是“三十僭主”横出,取消民主制,复行暴政,不到一年即被民众推翻,其后吵吵闹闹的激进民主又把雅典推入风风雨雨的多事之秋。政治斗争中的尔虞我诈愈演愈烈,道德观的败坏已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害死。这些震撼了柏拉图的心灵,使他沉思民主的真实含义,考虑政体的改革,潜心公正、合法的理想邦国的建立。善恶不分的现状使他想到人的素质,混乱的政局使他想到理性的作用、哲学的制约。他认识到: “只有正确的哲学才能为我们分辨什么东西对社会和个人是正义的,除非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力,或者出于某种神迹政治家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就不会有好日子过。”[3]他深信哲学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的生活,效力于良好的政治体制的建立,而文艺亦是如此。
出生于公元前 551 年的孔子,也是处在古代中国社会秩序变动最激烈的时期。春秋末期,奴隶制日益走向崩溃,而代表封建制的新兴力量开始壮大,政治结构变幻无常。“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礼崩乐坏,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载: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因此,孔子对秩序的问题有着深切的感受,这成为他哲学思考的出发点。他认识到两种类型的统治原则,一种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一种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前者用刑来治国,“民免而无耻”,后者以德来治国,民“有耻且格”[4]。而“德”的表现,就是礼乐制度。按照孔子的看法,礼乐是尧、舜、禹三代就有的东西,至周公制作而大备,只不过在春秋时期遭到破坏而已,因此重要的工作就是“复礼”,通过礼乐教化来恢复社会的秩序与和谐。与柏拉图的“哲人王”相似的是,孔子也坚信少数贤明的君子注定要具有才能和治世的责任感,他们使得战争和社会冲突被置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而这种人是由后天的训练和教育造就的。文学艺术自然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次西西里之行的失败破灭了柏拉图在苏拉库塞建立由哲人王管理的邦国体制的愿望,他转而潜心于学园的教育和研究工作。孔子花费大半生的时间周游列国,然而未能找到一个理想的君主为之服务,也未能获得重用而去实现他的构想,他只有退而教学。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因此,孔子和柏拉图都可算是教育家,而特定的时代背景又使得他们的教育与政治关系密切,对文艺的看法,即诗教的观念,也不免过多看重社会现实的一面。
( 二) 从文化背景上看,文学艺术在他们的时代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柏拉图处在希腊文化由文艺高峰转到哲学高峰的时代,在此前几百年中统治着希腊精神文化的是古老的神话,荷马的史诗,较晚起的悲剧喜剧以及与诗歌密切联系的音乐[5]。在古希腊人心目中,诗人( 尤其是荷马和赫西俄德) 是他们孩提时代就懂得尊敬与爱慕的偶像。诗人是民众信服的老师,诗是民众学习的起点,认识世界的依据,是他们解释生活的参考。
因而,诗歌在古希腊是重要的教育手段。而到柏拉图时代,希腊文艺的鼎盛时代已过去,随着民主势力的开展,智者学派兴起,没有衡量标准的诡辩之风也日益兴盛。此时的智者“不是沿以前哲学家或哲学学派的活动方式,而是继承和发展了荷马以来吟游诗人的活动”,他们成了由“创造者”或“作家”以及“言谈举止的规劝者即教师”组成的群体[6]。他们惑乱人心,随意解释古代文艺作品,随意瓦解神话,认为神是为着人的自然需要而设的,这势必削弱文学在表达真理方面的作用,而仅仅成为一种语言技巧对人的迷惑,不能为城邦提供永恒的价值目标。而作为当时主要消遣方式的戏剧和史诗,被柏拉图认为是伤风败俗的,诗人们扮演了与政治家和智者同样的角色,他们不懂装懂,误导他人。“诗乃哲学危险的对手,诗有吸引力,可以给人灌输错误的信念与理想,又极难消除。”[7]因此柏拉图要重新设定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
柏拉图对文艺的看法主要植根于史诗与戏剧,而孔子的论述对象则主要是诗歌。在西周,诗歌特别是颂诗和二雅的一部分原本是在各种祭祀仪式中用来“告于神明”的乐舞歌辞,负载着强化既定社会秩序,使贵族等级制度获得合法性的重要使命,因而,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在孔子的时代,这种功能随着贵族制的没落而随之消失,但它仍有一个独特的“赋诗明志”的作用。班固《汉书·艺文志》云: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惑,当揖让之时,以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从《左传》等书的记载来看,《诗经》在政治、外交活动中的作用确是十分突出的。当时人们在政治、外交活动中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图,体现一定的礼节,都需要借助于赋诗来实现。赋诗的恰当与否有时竟成为活动成功与否的关键。这样实际存在的特殊功能使孔子不得不重视诗歌。同时,孔子想要重新建立一种理想的政治秩序,就要在原有的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建构。他继续阐述了诗歌的重要性并赋予其新功能———修身。在孔子看来,西周时期的礼乐文明之所以伟大主要在于它是一种美善人性的表现,而不在于其外在形式,所以他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论语·阳货》) 按这样的逻辑,诗歌的意义亦不在于文辞的美妙,而在于其蕴涵的道德价值。孔子意在利用诗歌建构起一种理想化的圣贤人格,那么,如何利用以达到这一目的,便成为他的诗教文艺观。
( 三) 从个人角度看,二人都对文艺有一定的喜好,了解文艺对人的巨大影响
对于柏拉图而言,诗和优美动听的讲诵几乎是难以抗拒的魅力,他承认“从小就对于荷马养成了一种热爱”,也认为“荷马的确是悲剧诗人的领袖”[8]76—77。
在他看来,诗人从缪斯那里得到像磁石一样的灵感,经过诵诗人,传到听众那里,听众的面孔都表现出哀怜、惊奇、严厉等种种不同的神情,深深地沉浸于诗歌的情节之中。而孔子亦喜爱音乐,优美的乐曲( 《韶》乐) 使他“三月不知肉味,曰: ‘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 《论语·述而》) 正是基于这种切身体验,他们都意识到文学艺术对世道人心的影响,对理想政制建构可能起消极作用,因而要对文艺导之以正道,发挥在他们心目中所应起的教化作用。
二、柏拉图和孔子诗教文艺观之异同
首先要说明的是,此处的“文艺”,不管是在古希腊还是中国,都是同时包括诗歌和音乐。因为文学在古代社会中主要是诗歌,和音乐分不开。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指出,诗歌都包含三个主要组成部分:语言、音调和节奏。语言是诗歌的第一要素,音乐和节奏必须配合语言组成诗歌。“运动的秩序称作节奏,声音中的秩序———锐音和抑音之混合———称作音调,二者的结合就叫歌舞艺术。”
[9]414在中国上古时代的文艺实践中,诗、乐、舞三者也是紧密结合而不可分割的。周代盛行礼乐制,其“乐”亦包括诗歌和音乐。
孔子曾提过诗乐并举的思想,在《论语》里,诗、礼、乐是相提并论的词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 。这些情况决定了希腊与先秦论乐的内容实际也就是论诗的内容。
( 一) 从柏拉图和孔子看待文艺的角度与方法上看
1. 二人的相同之处在于,柏拉图与孔子立足于伦理道德,都认为不少诗歌是大有邪处的
柏拉图提出要将诗人逐出理想国,他申明: “你心里要有把握,除掉颂神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8]93有研究者认为,柏拉图提到艺术的时候,很少涉及美[10]。他更多地是在下道德判断。孔子说过: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论语·为政》) 从一个侧面亦可看出,孔子认为不少诗歌是有邪性的。在论及诗的正负功效时,他们都认为诗人必须有强烈的道德心和责任感,不是把艺术当作一种独立的存在,而是认为艺术品必然表现人的伦理观念。柏拉图认为诗人生活在城邦之中,应服务于一个目标,那就是培养合格的公民。为了灵魂的和谐与美好,国家宁可请用严肃有余而娱乐不足的诗家和说书人,他说: “此外,他不应只是通晓文字,谙熟音乐的诗人,而从未做过高尚和卓着的事情。相反,人们应该唱诵那些个编诗者的作品,他们人品可靠,行为高尚,受到公众的尊敬,哪怕诗才差些,作品缺乏音乐的魅力。”[9]587这样,“柏拉图其实是在强迫悲剧诗人和他们的祖师爷荷马为哲学这一新兴力量腾出位置。诗和诗人必须交出教育领导权。”[11]《论语》中也说“骥不称力,称其德也”( 《论语·宪问》) ,在“有德无才”和“有才无德”之间,孔子和柏拉图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2. 二人根本差异在于,柏拉图是以审美感动的眼光看待诗,认为诗能够眩惑、摇荡人心; 孔子则以理性演绎的方法对待诗,认为诗有益于修身
柏拉图在抓住“实用”,强调诗人要为政治教化服务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浪漫的向往。“诗化”一直是他用以表达哲学观点和宇宙观的重要手法。柏拉图的全部哲学着作( 除《申辩篇》) 都是用对话体写成的,结合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说理生动透彻,素有“哲学戏剧”之称,因此,柏拉图算是一个文学家,对文艺也应该更有深刻切近的理解。他很看重诗和艺术,认为“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12],从诗神缪斯那里得到灵感,吸引听众的心,而且“凭着神灵的恩典和缪斯们的帮助,他们往往会道出真实的历史事实”[9]434,某种程度上,这为诗人的灵感提供了神的担保,对诗歌表现真理的有效性予以了肯定,而且从文学创作论的角度揭示了诗人们在诗兴大发时文思泉涌,如痴如醉,如有神附的创作心理状态。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诗人们的创作既谈不上表现主体的情感,更谈不上表现真理,它完成不了“理想国”中的重大任务,即教育“保卫者”或统治者,而且还可能放纵和滋养人性中的低劣部分。诗人们凭借自己的“天才”,用想象力和追求快乐的欲望,打破哀歌与颂歌等敬天事神的诗歌规范,任意变乱诗乐的秩序,扰乱灵魂的秩序,迎合“邪恶”的听众的趣味[9]458。
因而,柏拉图对文艺大加清洗,诗人们“作品须对于我们有益; 须只摹仿好人的言语,并且遵守我们替保卫们设计教育时所定的那些规范”[8]67。至于戏剧,好人不应该愿意摹仿坏人、女人和奴隶,因此戏里只能包括无疵无瑕的、良家出生的男性角色。这些想法基本不具备现实可行性,所以他决定把诗人和戏剧家都从他的城邦中驱逐出去。他的表达也相当有诗意,“我们应该像情人发现爱人无益有害一样,就要忍痛和她脱离关系了”。“免得童年的爱情又被她的魔力煽动起来,像许多人被她煽动一样。”[8]94然而柏拉图又留了余地,“告诉逢迎快感的以摹仿为业的诗,如果她能找到理由,证明她在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度里有合法的地位,我们还是很乐意欢迎她回来,因为我们也很感觉到她的魔力,但是违背真理是在所不许的”[8]94。柏拉图正是太看重文艺了,对它要求太高,以至于寄托了太多不切实际的浪漫的幻想,因而忍受不了它的任何瑕疵,才会如此忍痛割爱。
孔子的诗教文论远不如柏拉图系统,层次分明。
柏拉图经过一系列论证,最终否定了绝大多数文艺,而孔子则是从多方面肯定了文艺的现实功能。第一,实践功能。“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 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论语·子路》) “不学诗,无以言。”( 《论语·季氏》) 这反映了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普遍现象,因此孔子对文艺在政治外交中的作用给予了很高评价。第二,认识功能。“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 此处时又具备了儿童识字课本的意义。《诗经》中有不少篇章关联到动植物名称,如《秦风·蒹葭》《曹风·蜉蝣》,可以帮助读者认识自然界。第三,修身功能。“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 ,诗是人们加强道德修养的第一阶段。“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论语·阳货》) 也是说如果不利用诗来提高自己的修养,就会寸步难行。修身应是孔子基于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赋予诗歌的新的价值。他的修身理论的主要目的是要将人改造成为能够自觉承担沟通上下,整合社会,使天下有序化的意识形态的人。在君主,要做到仁民爱物,博施济众; 在士君子,要做到对上匡正君主,对下教化百姓; 在百姓,则要做到安分守己,敬畏师长。第四,政治功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 《论语·阳货》) 诗歌可以激发人的思想情感,举一反三,即“兴”; 对于执政者,可以从诗歌中观察民风民俗和人们对时政的态度,即“观”; 对于人民,可以通过诗歌干预现实,批评社会,即“怨”。正因为这些,诗可以调节人际关系,加强社会的和睦、团结。所有的这些功能全以功用的观点立论,孔子的诗论更多地是利用诗而不是欣赏诗。子夏问《卫风·硕人》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 绘事后素,曰: 礼后乎? 子曰: 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论语·学而》) 。本来是描写女子美貌的《卫风·硕人》一诗,孔子却从中引出了“先仁后礼”的道理。综上几点,孔子是从现实功用出发,把文艺作为了修身之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忽略了其作为艺术的审美特征。
3. 相比之下,孔子对诗的态度始终比柏拉图现实
有几个原因值得探讨。首先,与个人气质有一定的关系。孔子是致力于救世的哲学家,而不像柏拉图有抒写性情的文学家的一面①。他说: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学而》,从这点上看,柏拉图更应该是文艺的知己,因为他曾亲自参与文学创作,对文艺的魅力也有更深的体会。其次,文艺在两个社会中地位不同。先秦用诗,无论是外交场上的赋诗言志,官学、私学中的教诗修身,抑或言论、着作中引诗明理,皆立足于实用。孔子受此影响,也很自然地认为诗歌与音乐之所以具有存在价值就在于它们对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向上匡正君主,向下教化百姓,使社会整一有序,这样就形成了工具主义文艺观。而在古希腊,戏剧和史诗是要用来在公共场合表演和朗诵的,它们更多地被用来审美,而非对人的教化作用,因而柏拉图才会在审美的眼光下,观照诗歌的教化功能。再次,《诗经》之后,正是中国先秦诸子百家蜂起的时代,这种从商周巫史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理性,走向了执着的人世间的实用探求,往往将有用性作为真理的标准,认定真理在于其功用,正是李泽厚所谓的“实用理性”,孔子亦不免把诗歌同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而柏拉图的时代,依前所述,是一个由文艺高峰向哲学高峰过渡的时代,诗与哲学的官司已经打了很久了。柏拉图认为,理想国应由“哲人王”来统治,只有他们从正义、节制等社会理念出发的“爱美”智能才能为无意识的诗人之智能提供规范。柏拉图从自己的哲学出发,把诗上升到一种理念的高度,看上去会带上一些不切实际,不如孔子现实。最后,雅典是一个较为民主的商业城邦,海洋文明的发展使其自有一种热烈开放的气氛,表现在柏拉图身上,有一种开拓思维、驰骋想象的浪漫气质。
而先秦时的中国,则完全属于农业文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耕作方式使得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哲人更为恪守传统,崇尚实际。
( 二) 从柏拉图和孔子对待文学的态度上看
1. 孔子曾修删《诗经》,柏拉图亦主张剔除传统
文学中的“糟粕”,二人对文艺都是有批判地继承柏拉图和孔子批评诗和诗人,矛头通常并非直指诗文本身。因为诗或音乐本身只具有中性的含义,是具体的编组和运用给它添加了表示道德倾向的内容[13]146。诗人可能说讲好的故事,也可能散布不好的传闻,关键在于他的取向和选择。接触诗歌的人们应该有所选择,不要来者不拒,一视同仁。据说孔子曾删诗,《论语》中记载: “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论语·子罕》) 《史记·孔子世家》亦载: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后人对孔子是否删诗曾有怀疑,但孔子对诗作过正乐工作以及对诗的内容和文字有些加工整理应是可信的。柏拉图也主张删去《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写,并申明查禁的原因: “并不是由于这些诗句不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好诗,有大量的听众,而是因为它们越是好诗,就越不适合这些儿童和成年人听。这些人注定要成为自由人,他们做奴隶胜过害怕死亡。”[14]348诗歌中强烈的渎神和反知识倾向的,使得柏拉图无法与诗人达成真正的谅解。
之于音乐,二人也有相似的做法。孔子要“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论语·卫灵公》) 。因为他“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论语·阳货》) ,对于曲调强烈的郑声新乐,孔子是极力贬斥的,只有《韶》乐那样的古乐才应提倡。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吕底亚和伊俄尼亚式的音乐是被禁止的,前者是因为它表现了悲哀,后者则因为它是靡靡之音。只有多利斯( 因为它勇敢) 和佛律癸亚式( 因为它有节制) 的音乐才可以允许。所能允许的节奏必须是简单的,并且必须是能够表现勇敢而又和谐的生活的。
2. 不同在于,柏拉图是极端而激烈的,孔子较为平和、中庸
总的来说,柏拉图的态度更为决绝,对文艺大清洗的决心也更为坚定,以致于在审查完之后,发现他的理想国中已不会有什么文艺了,哲学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孔子则宽容得多,他认为: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论语·为政》) 甚至《关雎》那样表现男女爱情的篇章他也称赞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实际上《诗经》的内容还是相当复杂的,既有歌功颂德之作,也有暴露批判之作,既有天真朴素的爱情歌唱,也有严肃庄重的祭祀乐辞,既有下层官吏牢骚不满的发泄,也有王公贵族享乐生活的写照。因此,在孔子这里,文学艺术依然有自己的自足性。
究其原因,主要是二人的思想根源不同。柏拉图首先是一个哲学家,构思了一个由“哲人王”统治的理想国,在这里,文艺不能上升到理念的高度,代表不了真理,必须让位于哲学。按照柏拉图的观点,诗歌没有哲学所拥有的那种深厚的本体基础,它就像漂在水面上的浮萍,没有深厚的根基[13]53。文艺很难与哲学的思辨结缘,诗人没有明确的政治意识,缺少从宏观上把握和运用道德原则的能力。对于他来说,哲学的失败意味着一种政治理想的破灭,这关系到城邦的兴亡,公共生活的繁荣,军队的建设以及民众的根本利益。而孔子是立足于实际的思想家,他希望通过“克己复礼”来达到天下大治。文艺是“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本来就有重视诗乐与政治关系的传统,人们认为礼乐的紊乱是邦国政治失序的现行,“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礼记·乐记》) 即是此义。那么,孔子需要利用文艺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不能像柏拉图那样对其弃置不用。其次,柏拉图谈论文艺,主要依据荷马史诗,悲剧或喜剧以及与诗歌相关的音乐,这些都是叙事性质的,适合在公共场合表演或朗诵,因而对观众潜移默化的作用也更大; 孔子的文艺批评是以对《诗经》的评价为主而展开的,《诗经》中的风雅颂都是以抒情为主,且大多表达含蓄,对人心智的影响要平和得多。从这一点上,也大略可见为什么柏拉图对诗及诗人的态度远比孔子极端。最后一点与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有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倡中庸之道,所谓中正、中和,无过无不及,“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 《论语·雍也》) 这是孔子观察、研究、评价一切事物的基本态度和方法,对于文艺,自然也不会采取太过激烈和极端的态度。
三、两种诗教文艺观的后世发展状况
柏拉图极力规范文艺以达到理想邦国的建构,孔子一心利用文艺来辅助圣贤人格的形成。他们都立足于政治,从道德感和责任心出发,在文艺上寄托了太多重负,再加上当时动荡的社会背景,其文艺观念也只能停留在思想层面上。
柏拉图的理想国始终未能建立。“不幸的是机缘把柏拉图带到了叙拉古,而这个伟大的商业城邦又正在和迦太基进行着决死的战争,在这样一种气氛之下,任何哲学家都不能有什么成就的。”[2]160哲人王的统治无法实现,而诗人们依然在四处吟咏,戏剧家们依旧要演出。孔子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乌托邦的建构者,他天真地以为,只要西周的文化典籍得以真正传承,那么西周的政治制度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恢复。实际上,即使这些典籍曾经就是现实的政治制度,可是到了孔子时代早已经成为纯粹的文化文本了。当礼乐的权威性和有效性都成了昔日的回忆,孔子还在为它教化功能的实现而四处奔走,然而除了儒家士人内部以外他再也没有倾听者了,他的价值观念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同,因而也无法付诸实施。
虽然他们分别建构了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在后世得到了最广泛、最长久的认同,但具体到诗教文艺观这里,二人的命运可谓是大相径庭。
柏拉图对诗的评价尤其是把诗人逐出理想国的做法,只存在于他哲学的论证和语言的建构之中,但前提是已经没有人相信这种只存在于思想中的论证了,因此也就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首先,因为这种思想太极端,不近情理,因而基本上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柏拉图对诗歌的审查似乎表现出一个纯理智主义者的道德成见,因为这里给了诗歌一个它不可能负担也不需要负担的包袱[15]55。而且,这种诗教“根本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想组织基础上的权威性教育,真正说来,它的生机只是在于怀疑和探索”[15]58。
其次,古希腊罗马文化后来被基督教文化侵入,受到实际上的分流和某种程度上的弱化,柏拉图的整个思想体系尚且不能一统天下,更何况是只在他整个体系中占一小部分的诗教文艺观。再次,西方文学向后发展,越来越脱离宗教神学、历史、哲学而获得了自足性,审美成为它的重要功能,人们不再苛求它的政治教化作用。因此,在西方人心目中,柏拉图首先是一个哲学家,而从来不是教师。
孔子受到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推崇,逐渐取得了在古希腊由诗人占据的民众之师的地位,成为千古师表。他的“兴观群怨”说成为中国几千年来评价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他提倡的中和之美经汉代大儒们演化,建立了以“温柔敦厚”为基本内容的“诗教”观念。究其原因,首先,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历代统治思想的主流,人才选拔的科举考试也是以它为基准,知识分子评诗作文的标准深深地受到的孔子的影响。其次,西方叙事文学兴盛,而中国很长时间内都是以抒情为主的诗赋占主流,这样的文体更与个人情感密切相关。在思想控制严密的中国封建社会,抒情当然要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与孔子的教导是相合的。即便到了元代,杂剧这种叙事文学兴起,依然是要提倡“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再次,自先秦始,中国的知识界一直与政治密不可分,为政治服务。“任何知识与事业,不过为达到整个人文理想之一工具,一途径。”至如文艺之类,“在中国学者亦只当作一种人文修养,期求达到一种内心与人格上理想境界之一种工具”[16]122。这样的状况,也促成了孔子诗教观念的流行。
结语
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内,在相似的时代背景下,柏拉图和孔子都提出了要重视文艺教化作用的诗教文艺观。在弥漫着浓厚的哲学优越意识的氛围里,诗歌很难在柏拉图的体系中找到一席体面的位子,而孔子尽管尊诗,重视的也是诗歌的道德内涵和认知功能而已,换言之,诗歌要有用。归根结底,他们的文艺观都走向了一种政治诉求,以期文艺有益于管理妥善的政府和人民的生活,并有效地引导规范公民的认知倾向和道德意识。对他们而言,政治和道德的要求必然要高于艺术的标准,而差别仅在于程度的轻重而已。后世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在他们看来只会是不可思议的奇谈。由于中西文化自源头至现代都存在着巨大差异,如政治体制、宗教神学背景、思维方式等,导致这种文艺观在后世的发展大相径庭。但是作为各自文明传统的代表,他们对后世的文学思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对二者的诗教文艺观进行廓清和比较,是可行且必须的。
参考文献:
[1][德]卡尔·雅斯贝斯.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 魏楚雄,俞新天,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1989: 8.
[2][美]罗素. 西方哲学史[M]. 何兆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3.
[3]第七封信[M]/ /柏拉图全集: 第4 卷.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80.
[4]中华文明史: 第 1 卷[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63.
[5]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 朱光潜,译.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281.
[6]汪子嵩. 希腊哲学史: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