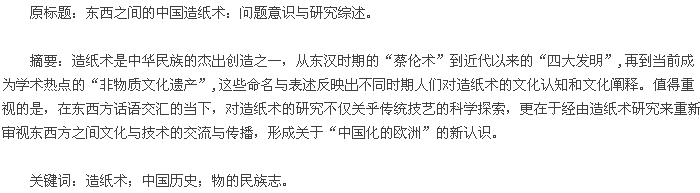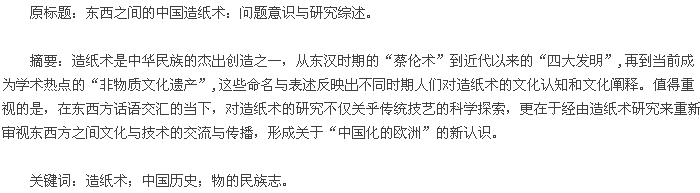
在关于中国历史、中国文明的叙述中,造纸术与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被视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性成就-“四大发明”虽然在标榜中华民族文化贡献的话语中造纸术作为四大发明的组成部分而得到表述,但关于造纸术本身的研究,却在文化研究中被长期搁置。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四大发明”作为非中国原生的表述方式,呈现着从欧洲中心的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价值判断,而在现代以来主动接受的西方话语中,“四大发明”似乎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自表述”的重要根基性内容,近代以来,这一观念经由中小学教材而成为现代中国的“一般知识与思想”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四大发明”这一提法之所以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就进人当代中国的“一般知识与思想”,与其产生于欧洲不无关联。正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指出的那样,“在亚洲内部发现欧洲的、乃至拟似欧洲的事物,一直就被视为亚洲的‘近代’之发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包括造纸术在内的“四大发明”被视为按照欧洲价值“重估”中国文化的重要结论。
进人21世纪以后,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勃兴,“遗产”成为重要的文化表征。由此,“四大发明”在遗产语境中被重新言说、表述和建构。在2006年以来颁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造纸术”类的遗产样式多达15项;在各省颁布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造纸术”类遗产样式多达30余项。特别是2009年中国宣纸制作技艺人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这标志着造纸术在“遗产”语境中获得了新的表述。
一、问题意识:在中国发现历史。
在遗产时代研究造纸术,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复杂立场。造纸术作为公元1世纪左右出现的技术,在经历一千多年的发展之后,其技术层面的基本原理本身并没有出现大的变革,但从其具体的技术构成来看,从一开始,则因为地域、环境、生态、资源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技术范型,呈现出参差多态的技术样貌和产品。在当今现代造纸产业虽然已经如此发达,却依然难以完全取代传统造纸。特别是在当前工业化造纸面临环境、生态质疑的语境下,传统造纸将在可持续发展的议题下提供新的启示。与现代工业批量化生产的廉价纸品相对应,手工纸作为蕴含人的身体创造的物,具有工业品难以取代的文化意涵。
前现代一现代成为划分人类历史的重要界限,在诸多层面和领域,都因为这一界限而呈现出二元对立的格局。而纸和造纸术则成为其中的异类。按照欧洲中心的逻辑,纸和印刷的发明,成为欧洲文化启蒙的关键技术。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以及与之相关的纸)-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如果造纸以及与之相关的印刷术对文明演进如此重要,竟是欧洲现代性兴起的重要技术基础;而在欧洲之前一千年就发明造纸术的中国,却又在近代以来的文化表述中被欧洲置于“野蛮、黑暗”的“非文明社会”的境地。这其间的悖谬,是否存在一个因为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力量悬殊而导致的话语改写呢?正如艾田蒲(又译艾田伯)所说,在中国长期向欧洲保持文化输出之后的近代,是中国走向全面欧化的20世纪。是否因为这个欧化的世纪的遮蔽,使得今天的研究者难以看到曾经中化的欧洲呢?由此反观,以欧洲中心出发的前现代一现代的世界图式,是否在中国存在重新书写的可能?
以上述问题为起点,将形成一个从造纸术出发,归结于“中国”而形成的“问题域”,其间“历史”将成为问题展开的第一个关键词。
在关于中国文化的自我认知中,“历史”,是一大关键。传统认为,“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中国史之繁富,并世各民族,莫能与比。我民族文化之惟一足以自骄者,正在其历史。足以证明吾民族文化之深厚与伟大,而可以推想吾民族前途之无限”.而且即便在考虑学术“现代化”的过程中,“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即便如此,西学话语在中国现代学术中全面取得霸权之后,史学也同样面临着沦丧的境地。正如陈寅悟在给北大毕业生的赠诗中所言,“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正如史学界自身的反思一样,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学科体制”,不但主宰了20世纪学术发展的主要形式,同时也彻底摧毁了我们对传统知识结构的认知,以致身处20世纪末的我们,往往不自觉地就会以“学科”的角度来理解史学这门古老的“学问”.
史学如此,历史本身的写作更是如此。在20世纪以来的学术话语中,在中国之外,以“汉学”、“中国学”为名的研究成为关于中国的学术话语的核心来源。“在西方,很多由中国学家表述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在支持着各种各样关于‘世界’的理论,只要这些理论家希望他们的论述是关于‘世界’的,他们就只好凿壁偷光式地向中国学家挪借关于中国的知识”.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关于中国的表述,在西方学术界,被“汉学”“中国学”所代言。在这样的表述格局下,西方学术话语中关于中国的论述,就难免出现“变形”、甚至改写,而对中国内部研究者而言,旧有的史学传统在西学的冲击下,不免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由是观之,在所谓“现代”学术话语构建的评判体系中,传统中国没有历史。正如埃里克·沃尔夫在书名中所揭示的那样,世界,不过是由掌握话语权的欧洲和被表述的“没有历史”的人民所构成。在西方学术界对自我中心的表述格局的反思中,对中国历史书写所表现出来的西方中心也进行了批判。
柯文指出,在美国学术界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书写中的三种思想框架-冲击一回应框架,近代化框架与帝国主义框架,“这些模式都把中国历史的起点放在西方,并采用了西方衡量历史重要性的准绳。”随即,他提出应当“以中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历史,这种研究将体现四个特征:(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柯文的着作及其在中国研究上的“中国中心论”对国内人文社科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却并非没有值得质疑之处。首先,柯文着作的预期读者并非中国本土的研究者,而是美国的中国研究者,在中国历史研究者身上,“中国中心”本不应该成为学术议题。其次,柯文自身也承认,要完全消除西方学者在中国研究上的种族中心的歪曲是不可能的,只能够希望将这种影响降低到最低的限度;再次,柯文所提出的具有四个特点的“中国中心”的研究范式,其本质同样与此前他批评的“西方中心”的中国研究一样,也是一个来自西方的对中国的表述体系的建构。
“在中国发现历史”,其逻辑前提要么是中国本身没有历史,要么是中国自己没有作出历史表述。
无论是哪一种,中国都还是作为被表述的“没有历史的人民”而存在。当代研究者应当清晰认识到,“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观念其实套不到中国历史上面,中国关于民族国家的历史应当自己书写”.中国的历史,首先需要中国的研究者作为局内人作出“自表述”
造纸术作为诞生于中国的一项与人类文明密切相关的基础性技术,在近代以来的关于其价值的判断乃是基于“四大发明”这一源出于欧洲的认知,同样体现出明显的“西方中心”倾向。同时,与西方影响密切相关,对造纸术的认知和研究同样停留在技术层面,对纸和造纸术与中国文化传统、地方性知识等方面却没有足够重视。因此,纸和造纸术同样面临“自表述”的问题。在此意义上,重建关于造纸术的历史话语,就是面对以欧洲为中心的“西学”进行中国本位的“自我言说”与“自我书写”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在道、术、法、器构成的中国传统思想世界中,“术”往往成为连结虚无缥缈的“道”和现实存在的“器”的纽带。在最早记载造纸术的文献《东观汉记》中,造纸术被命名为“蔡伦术”在其后的历史演进中,蔡伦被作为纸的发明者而一再表述,成为与仓领造字、蒙恬造笔相类似的具有传说性质的“文化记忆”与此同时,正因为是“术”,所以在追求“道”的“大传统”话语体系中,关于造纸技术的记载在历史进程中付之胭如。反而在关于农时月令、农业生产的着作中偶有记载。直到蔡伦发明纸之后一千余年的宋应星着((天工开物》,才明确指出“万卷百家,基从此起”,而造纸的技术过程也才得到完整记录。所以,才可以理解为何今天各地在表述自己地域的造纸术时,一方面强调自身渊源久远,是“蔡伦术”传承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在技术描述上又只能把技术流程与《天工开物》相关联。
关于纸的汉文史料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论,如历史典籍、方志、文集、别集、杂着、类书等其中有关纸的记载。如关于纸的起源,可以从《东观汉记》(公元120年前后)以及班固所撰《后汉书》中可以找到记载。纸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可以从历代史书和政典中读到。如《唐六典》、《元和郡县图志》、《嘉泰会稽志》、《江西省大志》等。在文集、笔记中也可以找到关于纸的记录,如《东京梦华录》、《咳余丛考》等。另外在历代类书中,也可以找到关于纸的记录,如《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等。
另一类文献为论纸的专着或专文。最早的是苏易简(953^“996)编写的《文房四谱》,是关于文人书房用具的综合论述,其中一卷专门谈纸,保存着一部分业已亡佚的关于纸的早期史料特别是唐代史料。
另一部关于纸的专着是14世纪费着所写的《蜀笺谱》,介绍了四川地区明代造纸的有关情况。而最重要也是早期唯一记录造纸工艺的专文是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的《杀青》一卷,对用竹和褚皮造纸的技术做出了详细的记录。
与其它关于”道“的汗牛充栋的文献相比,纸和造纸术的文献史料显得数量稀少。同时,在中国传统学术框架中,纸和造纸术并没有进人主流研究视野,只是作为文人雅致或博学多闻的对象而存在,直至19世纪末。
1884年,沿袭培根和马克思关于”三大发明“的说法,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最先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人造纸术,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这是将所谓”四大发明“与中国直接关联的第一次。同时,也是开启了将文明贡献的西方中心论引人对中国传统技术价值评判的思想进路。在西学影响下,纸和造纸术获得了新的研究和阐释空间。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围绕中国的纸和造纸术,中外学者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从研究主题来看,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造纸技术史研究;(2)中国造纸术传播研究;(3)造纸工艺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4)人类学技术史和物的民族志研究。下面分而述之。
(一)造纸技术史研究。
在现代以来的学术话语中,造纸术首先是作为一门传统技术而存在,而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是造纸术研究最传统的视角。在将近百年的时间里,这一领域的学术话语竞争主要集中在两个核心问题:
(1)纸的定义;(2)造纸术是否由蔡伦发明。
在造纸技术史研究方面,由李约瑟主编、钱存训着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卷《造纸与印刷》和潘吉星着《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以及张秉伦、方晓阳、樊嘉禄着,《中国传统工艺全集·造纸与印刷》等全景式着作堪称代表。
对纸的定义,研究者从《说文解字》对”纸“的”絮一苫也“定义出发,将纸与中国传统丝绸生产过程中的”漂絮“相联系,进而推测造纸术的发明过程。
通过对字义的考据,劳斡认为古人漂絮之后在竹席上残留的薄片,就是《说文》所说之”纸“钱存训认为絮即纤维体,苫即帘模,”至今仍是造纸的最基本原料“.戴家璋则认为这一说法没有事实依据,不足为训。对从《说文》出发的关于”纸“的定义引发的争论,凌纯声认为”纸“在蔡伦之前早已存在,”蔡伦不过利用古代丝纸和栽补纸的两种方法合拼,原料方面本来用动物纤维之丝,代以植物纤维而1论也“颇为可疑”潘吉星也认为树皮布“与纸的起源没有任何关系”潘吉星通过对现代发掘出的古纸的考察,结合现代以来的纸的定义,认为“絮”只能是植物纤维,进而在融合古今的基础上,提出“纸”的定义,“传统上所谓的纸,指植物纤维原料经机械、化学作用制成纯度较大的分散纤维,与水配成浆液,使浆液流经多空模具帘滤去水,纤维在帘的表面形成湿的薄层,干燥后形成具有一定强度的片状物”.
蔡伦发明造纸术,这一说法源出于《东观汉记》,这是关于蔡伦以及造纸术的最早文献记载,同时也是后世关于蔡伦发明造纸术的直接文献支持。围绕这则史料的真实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是否由蔡伦发明造纸术、最早的纸产生于何时等问题,引发了长久不息的学术纷争。
虽然对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质疑从苏易简《文房四谱》就开始了,但由于没有实物证据,仅是猜测而已。美国人卡特(1925)也认为,“究竟蔡伦是否是真正躬与其事、发明造纸的人,还是大力赞助发明造纸的人,现在已无法确定。”他同时指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他和造纸已经成为不可分的。后来他甚至被奉为造纸之神。”20世纪人文研究方法最重要的突破应当从“二重证据法”开始。对造纸史研究而言,真正的冲击也在考古发现之后。从1933年开始,累计有7次考古活动报告发现了西汉时期的纸张。考古检测和断代结果表明这些纸张的年代远在文献记录的东汉蔡伦发明纸的年代之前,因此,部分研究者据此提出蔡伦并非造纸术的发明者而是完善者“文革”期间,“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观点被认为是“帝王将相史观”的延续,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造纸术也同样如此“文革”结束后,并非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观点继续有人提出,不过支持的论据从“文革”期间的所谓“儒法斗争”、“群众史观”,转变为以考古发现为支撑在对“文革”否定的过程中,并非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学术观点也同样被列人否定之列。同样的学术观点,甚至是同一个人,在“文革”中和“文革”后,其论据和论证路径完全不同,由此导致对这一观点的讨论陷入尴尬的境地。进而前后两种不同基础的学术观点都被归结为“左”的影响下的非学术结论。
19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风气的正常化,关于是否是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论争进一步展开。支持者的论据主要包括:历代文献记载、国际会议结论以及后世祭祀蔡伦的习俗等更进一步,以王菊华、李玉华等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考古发现的所谓西汉时期的纸并不是纸,更不能否定蔡伦发明造纸术的结论。而以潘吉星为代表的研究者则坚持认为考古发现支持西汉时期就有纸的观点。这两种观点最后集中到对同一批考古出土实物的不同鉴定和断代结论,一直延续到当下都没有定论。
(二)中国造纸术传播研究。
无论是否认为是蔡伦发明造纸术,包括认为造纸术应当与树皮布相关联的凌纯声,也都认同造纸术是中国的发明这一观点。造纸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也成为支持中国发明造纸术的重要学术路径。
认为欧洲造纸术是由中国传人的观点由卡特首倡,经美国纸史专家DardHunter详细考证,成为在纸史研究中的一个常识性结论。李约瑟在罗列中国传人欧洲的最重要的26项技术中,造纸术名列其中。季羡林对中国纸张和造纸术传人印度的时间及过程进行了详细考证。张文德对中国造纸术通过阿拉伯地区传人欧洲的路径进行了梳理和考证。盖双以阿拉伯古籍文献考据为基础,对造纸术西传过程中女性起到的作用进行了深人研究。
王珊对中国造纸术从东汉到明清在包括日本、朝鲜、越南在内东亚文化圈内的传播历程、路径进行了探讨苏荣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造纸术向东的高丽、日本;向南的东南亚;向西的西亚和中亚、阿拉伯地区以及远西的欧洲的传播进行了全景式的研究中国造纸术对外传播方面的集大成者以潘吉星为代表,所着《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是到目前为止从科技史的角度出发对四大发明的源流和传播进行探讨的权威着作。0在造纸术对外传播的研究中,从技术史的角度,以中国为中心向各个方向梳理传播脉络和流程,进而在更为深广的层面上支撑关于中国发明造纸术的论断,这一点已经基本上成为中外学界的共识。
(三)造纸工艺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
虽然文献记载中造纸术是由蔡伦发明,但其具体的工艺流程却没有相关记载,只有将近1000年以后《天工开物》才第一次完整而详细地记录了用竹、褚皮造纸的工艺流程。黄震河从史籍文献出发,介绍了传统古纸的分类,阐述了各朝代古籍用纸的特征以及古代手工造纸的方法在近来的研究中,以实地调查为基础,对地域性、族群性造纸工艺进行记录和描述,成为当前造纸术研究的主流范式。在针对造纸工艺的调查方面,《中国传统工艺全集·造纸印刷》完整收录了全国范围内近十处具有代表性的造纸工艺李晓岑对通过对云南丽江纳西族手工造纸工艺进行实地调查,认为纳西族的手工造纸既受到西藏固定式纸帘造纸方法的影响,也受到中国内地常见的活动式纸帘造纸方法的影响陈彪、张义忠实地考察了贵州普安县卡塘村手工皮纸的制作工艺,并对其工艺技术特点、销售状况及经济效益、传承与保护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朱霞从技术与民俗两个方面对广西大化县贡川乡壮族手工造纸进行调查,认为广西大化县贡川壮族造纸为一种传统的抄纸法造纸,生产的手工纸-“纱皮纸”具有较多的特点,在当地壮族的日常生活和人生礼仪习俗中具有重要价值,还对白族的造纸术进行了实地调查。许靖对福建山区传统造纸术的调查表明,手工造纸在闽西山区的发展过程中是重要的推动力量,给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罗茂斌、全艳锋、李忠峪对云南香格里拉尼西乡枪朵村传统藏纸制造工艺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将此工艺与纳西族造纸工艺进行了比较。邓文通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描述了瑶族造纸的工艺和生产过程,分析了造纸术在蓝靛瑶地区面临失传的原因。方晓阳等对江西铅山连史纸生产工艺进行了田野调查,并对连史纸中独具特色的多次弱碱蒸煮与天然漂白进行了重点探讨,认为这些传统技艺对于提高纸张耐久度有较好的作用,是具有科学价值的关键技术环节。关于造纸术的个案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兴起之后,受到项目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的影响,造纸术的地方性与族群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按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计算,项目化的造纸术技艺调查和描述就有将近30个。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资料。
(四)物的民族志和人类学技术研究。
“物”历来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面。摩尔根在人类学经典《原始社会》中就把物质及其生产水平作为划分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准,这一方式经过马克思的阐述,形成了以物质生产水平划分社会形态的历史叙事范式,这一范式对20世纪以来中国的人文表述产生了重大影响。从19世纪中叶开始,“物质文化”就是西方人眼中的古代文化或其他文明、其他生活方式和人种的文化。彭兆荣指出,人类学“物”的研究侧重于物质性,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作为标识、作为分类原则、“事物”的整体形貌、作为符号表述和交换的价值。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有两种方法,第一是以“物”为中心的生活研究,第二是对“物”进行科学的、有造型的技术方法研究。既然是文化行为所改变创造的物质形态,物质就有了近似于文字、象征、叙事乃至历史的性质让·鲍德里亚指出,在后现代社会,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在以往所有的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生产、完善和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正因如此,民族志研究对对象的描述即关注人类如何在物质上附加属于其独具特色的“文化叙事”,核心在于发现通过“器物象征”和“物质表达”而形成的专属性符号系统。技术是与物紧密相关的文化内容,工具被视为物质生产的重要手段,“工具是标志文化存在的指标”.在我们今天对于科学和技术之广义的理解中,可以说,在早期人类学者的作品中就已经出现了对它们的关注,如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
和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从知识谱系来看,人类学对技术的研究可以回溯到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涂尔干和马塞尔·莫斯。莫斯认为,人类使用的各种器具(工具、武器、衣服、器皿,等等)都是集体活动的产物。
各种工具通常表明了文明的既定状态,在文明和工具之间、社会本质与工具之间存在非常确定性的关系。这些决定关系从而构成了一种社会学的问题,从这个方面看,技术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他前瞻性地预见,“正如国家之间所共有的科学、工业、艺术,‘区别’本身正在慢慢退化成小部分群体的遗产,或者大民族的一种共有的专属;同样,这些文明的优秀特质都将成为越来越多社会群体的共同财产”在物的民族志方面,堪称经典的是美国人类学家西敏司(SidneyWMintz)的民族志《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史的地位》,人类学家基于对加勒比海地区和欧洲的观察,沿着“糖”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勾勒出一个视角独特的跨地域文化史。在中国研究方面,柯律格(CraigClunas)所着MaterialCultureandSocialStatusinEarlyModernChina(《明代物质文化与社会地位)})从文学、语言、文物等侧面,对明代的物质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梳理。白馥兰(FrancesaBray)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对明清时期的技术和性别的关系进行了1过对“食物”这一独特的“物”与中国文化诸方面关系的呈现,揭示出食物与传统、食物与礼仪、食物与资源利用的复杂关系,进而揭示出食物背后所蕴藏的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和世界观。与中国传统的物质文化和技术史研究相比,上述研究通过特定的物和技术与文化、社会、传统的关系梳理,展现了蕴藏在物和技术之中的复杂文化意涵。
延续这样的理路,中国传统技艺研究应超越技术范畴,进人更为深广的文化领域。“由中国原始造物艺术延续而来的工艺文化,从其伊始便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具体的器物所体现的技艺与尺度构成的物与物、人与物关系的和谐空间,不断地规范喝调整着人们生活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国民间的知识体系就是在这样的物质性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逐渐累积构筑起来的”对中国文明而言,(纸质的)印刷品是中国曾经制造的数量最为庞大的一宗产品。如果将一本书作为计量单位,那么中国印刷的书籍的数量超过青铜器与建筑物的总数。如果以书的一页为单位,再加上宗教护符、银行票据、邮票等等,其总数远远超过纺织品与瓷质餐具之和。从这个意义上讲,纸可以视为中国物质文化的最重要的类型。但问题在于,在过去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只重视以纸作为物质载体的文献内容,而对纸作为“物”本身少有顾及。即便在技术史研究中,研究者注重的是造纸的技术而非纸张本身。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学者雅各布·伊弗斯通过考察夹江手工造纸的生产工艺及其传承,认为在夹江造纸技艺传承中,工艺知识的再生产内嵌于特殊的自然、社会和象征环境,很难并且没有必要转化为书写知识,记载工艺知识的文本更关注道德价值的宣传而非技术传递。在此基础上,通过技艺本身的“具身性”在现代国家行政框架下遭遇的挑战与变迁,考察当地人在去技能化时期之后,重建手工造纸业的过程,以及在技术再生产的基础上修复社会组织的过程。肖坤冰、杨正文以四川夹江地区的纸的流动为切人点,通过对“物”(纸)的流动的表象的透视,来讨论隐藏于“物”(纸)的资源争夺背后的国家权力的地方化意义,从而对区域社会变迁之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进行地域化的理解和做出历史性的解释。三、初步的结论。
造纸术是中华民族在文明历程中的伟大发现和杰出创造,对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记录、传播和传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纸是中华民族文化最重要的物质载体,记录和保存着民族的记忆;它广泛应用于中华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生活方式的重要器物;它与中华民族的信仰世界密切相关,是文化象征的物质载体。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纸是中华民族文化最重要的“物”;而造纸术在其发展和演进中与各地域、各族群生活方式、资源状况的密切结合,形成了以“蔡伦术”为根基的多元化技术特点,进而成为理解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重要进路。
纸和造纸术作为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杰出创造,在中国传统中长期因道术法器的思维范式而被忽略,在因西方学术话语影响下,以西方价值为评判标准的“四大发明”又成为中国近代以来的“普通知识”之一,与炎黄子孙、黄河长江等符号一道,对当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和认同起着重要作用。
20世纪以来,关于纸和造纸术的研究长久纠结于“什么是纸”、“蔡伦是否发明造纸术”等问题,反而对为什么在中国形成如此这般的纸的定义、为什么在各地、各族群中形成如此这般的造纸术等更为重要的问题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将纸和造纸术纳人人类学的视界,对纸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和价值,以及纸在传统文化中作为连接“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物的载体的功能等问题的研究,才刚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