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示语翻译景观与全球化社会语言学
时间:2014-07-07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本文字数:8925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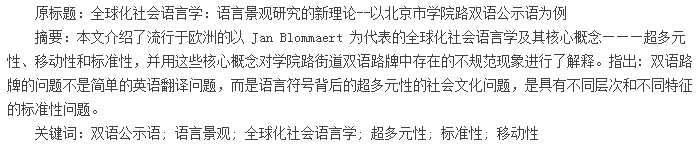
双语公示语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语言接触最典型的形式,过去学界对此总是从翻译的误差、跨文化交际行为角度来审视,往往以非错即对的简单判断来确定双语公示语的质量。其实,双语公示语是一种语言景观,其表现形式上的差异反映了制定者或阅读者内部不同文化的价值取向。对双语公示语的解释,以荷兰学者 Jan Blommaert 为首的欧洲学派的全球化社会语言学提出了新的视角,可供我们研究语言景观时借鉴。
一 公示语研究的几个角度
(一) 翻译视角
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良好的城市环境和城市形象。在此背景下,双语路牌的翻译备受关注,学术界为此也开始重视标识语翻译问题的研究。关于路牌翻译方法的文章很多,但这类文章大多限于挑错和改正,侧重于语言本身的问题。比如,王德庆等(2012) 分析了北京天坛公园公示语的翻译; 李克兴(2000) 调查了深圳的公示语翻译状况,指出深圳的英文垃圾和翻译谬误既有损于开放城市的声誉,又损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形象; 戴宗显、吕和发(2005) 以2012 年奥运主办城市伦敦为例,多方位探讨公示语的相关知识和汉英翻译; 罗选民、黎士旺(2006) 考察了北京“脏乱差”的语言环境,指出公示语翻译的治理和整顿已成为翻译界一个严峻的课题,呼吁翻译理论要更好地为现实服务。这些研究分别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公示语的语言文字错误进行了分类和分析,并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但由于对语言表层的侧重,导致对语言符号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关注不够。其实,双语标识,尤其是街名的英文部分,由于涉及文化差异和语言习惯等因素而很容易出错。不同的翻译理论,如目的论、等值论等,虽能解决一部分实际问题,但无法从宏观角度对路牌所联系的社会文化乃至政治因素进行描写和分析,更无法加深我们对于路牌所涉及的语言文化现象的理论研究。
(二) 跨文化视角
跨文化交际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胡文仲,2004) 。从跨文化角度研究路牌英译的学者认为,路牌上地名的英译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需要译者从跨文化角度去审视地名的文化内涵,从而将地名的文化信息准确地传递给外国游客。这方面的研究往往以某城市公共场所的英语标识为例,比如杨永林、丁韬、张彩霞(2008) 将北京地区的双语公共标识语在跨文化层面上存在的问题概括为语用失误、幼稚倾向、文化误读、促销倾向、语言禁忌等十大种类,并探讨了全球化语境中跨学科研究的视角对于语言学研究的意义。赵湘(2006) 详细描述了标识语的文化差异现象,探讨了文化差异在哪些方面对翻译产生影响。刘士祥(2012) 介绍了文化交际翻译的理论问题及其在教学中的应用。这些研究以丰富的例证揭示了跨文化问题在公示语翻译中的重要性,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但从本质上说,跨文化研究仍是翻译问题的延伸,是从不同角度对翻译中出现的错误或不规范现象进行的讨论。不过不是以翻译理论为背景,而是以跨文化理论为指导,强调地名的文化内涵以及如何在翻译中保留并传达这些内涵。所以,和“翻译视角”一样,跨文化研究也不能从宏观和理论高度对双语路牌所涉及的语言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描写和分析。
(三) 语言景观的社会语言学视角
语言景观的定义可参阅 Gorter(2006) ,他指出: 语言景观是指某个特定的国家里语言情况的描述与分析,也可以指某一个更大的地理区域内的语言现象和语言使用情况。简言之,语言景观研究所关心的是在公共领域里以书面形式表现的语言使用。对路牌、招牌、楹联、广告、标语等日常生活中所反映的多语现象进行拍照、录像等都属于语言景观的研究范围。Ben R afael(2006) 把语言景观的研究内容概括为 16 个变项: 标牌上有几种语言? 各用什么字体? 出现在什么位置? 几种语言是否按特定的顺序排列? 是否存在完全或部分翻译过的文本? 能否反映主流人群和非主流人群之间的权力关系? 等等。国内用语言景观分析法对公示语的研究并不多见,以李贻(2011) 对广州北京路语言景观的历时性调查以及杨永林、程绍霖、刘春霞(2007) 对北京地区公共标识语的研究为例,我们发现: 此类研究揭示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的语言景观特征,也从历时的角度证明了全球化的影响在日益增强。但因语言景观研究目前仍是一个较新的领域,还没有明确的理论核心(Sebba,2010) ,而且,尚不确定用何种理论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是社会语言学的语言接触理论还是社会学或心理语言学理论等。所以,这类研究只能尝试性地对多语现象进行分析,难以深入探讨语言符号背后隐藏的社会问题。
从目前国内刊物发表的文章来看,大多数关于路牌和公示语的研究是从翻译角度切入的,研究重点在于对路牌中英文翻译的错误进行分类并分析原因,同时也给出一些修改性建议。
相比而言,从社会文化角度,比如,用跨文化视角或语言景观的方法去探讨双语指示牌中不规范现象的研究较为少见。当前,全球化正在成为世界多样性文化发展的新的发展土壤,学术界也必须正视全球化进程中跨文化的语言问题,以新的视角关注诸如路牌和公示语等领域所反映出的社会语言学问题。
二 全球化社会语言学
全球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在全世界经济、政治、技术、文化整合的综合过程中,语言现象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和多元。而“全球化社会语言学”正是为了研究这种新现象而出现的新理论(Blommaert,2010) 。它以荷兰学者 Jan Blommaert 为代表,形成了欧洲社会语言学派。该学派把语言景观研究看作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认为它不仅是描写性的,同时也是解释性的。而且,语言景观研究还把社会语言学的描写对象从语言使用者延伸到了语言使用的空间。这里,“语言使用的空间”不仅指物理空间,同时也指社会文化空间和政治空间。
每个空间内部充满着标准、规范和传统,规定和制约着我们的语言行为(Blommaert,2012) 。因此,语言景观是社会语言学家在描写语言现象时的常用工具和有利武器。超多元性、标准性和移动性等是该学派的核心概念,这些概念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传统语言学及社会语言学发起了挑战,对语言现象的描写和解释,尤其是对语言同社会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 全球化和本土化
全球化是整个世界趋同的倾向。它对社会语言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因为它引起了社会语言学语境的总体重组; 而本土化则正好相反,它是个性和特色的代名词,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等紧密相联。“全球本土化”,顾名思义,就是试图超越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思维的局限性,使具体的语言文化形式呈现出二者之间的辩证平衡。
在全球化社会语言学学者看来,全球化是一个抽象的、不易觉察的过程。真正可感知的全球化发生在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即本土化) 的互动过程中,这一互动过程是二者互相竞争、互相妥协的过程,因此也是社会语言学家要关注的核心问题。具体的语言符号大多是全球化和本土化互动过程的结果(Blommaert & R ampton,2011) 。结合双语路牌,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
其语言是否呈现出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平衡? 如果不平衡,是全球化弱而本土化强,还是全球化强而本土化弱? 为什么? 这种强弱的不平衡性又如何影响着语言符号的“移动潜势”?其背后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心理动因?
(二) 超多元性
根据 Vertovecs (2007) ,“超多元性”就是“多元性中的多元性”,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以预测的复杂性。具体说来,“超多元性”是指城市居民的语言多样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这是由于全球化引起了社会、文化以及语言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很难用过去的理念来概括。语言使用、语言选择和语言混合都呈现出新的模式,共时、静态和同质的言语社区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新的言语社区是松散、动态和“去地域化”的。其成员不再共享一些传统特征,比如居住地的固定性、人种的相似性以及社会文化的同一性等(Blommaert & Backus,2012) 。另外,手机、网络等先进技术的使用,使人们之间的接触更加密切、更加新奇。语言各个层面的变异和社会范畴的联系更加复杂,不仅仅是拉波夫和米尔罗伊等人所关注的语音变异和社会范畴有联系,词汇和语法变异更是和社会因素密切相联。传统的多语格局在受到挑战,格局中每一种语言的社会地位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语言的异质性也更加明显,以往的语言保持和语言转换概念已不足以描述这样的复杂性。
更具体地说,我们对于“语言”的理解应该彻底地改变,因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每个人都是多语人,只不过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掌握多种语言的人,而是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使用各自所掌握的各种语言的片段性知识(比如,在一句话里使用严肃、正式的英文词汇,而语法却是非正式的中文特色,再时不时地夹杂一些更加异质的因素,如夏威夷语的某个流行词汇) ,并把这些语言片段糅合在一起来完成不同的交际功能和目的。这种现象不是传统的语码转换或语码混合所能解释的。全球化社会语言学家要描述的正是这种“移动”的语言资源,是每个人可资利用的由各种语言片段所构成的“语言资源库”。这样的复杂性只能用超多元性来概括。
(三) 标准性
所谓“标准性”,就是交际活动的双方都默认存在一套潜在的规则。否则,符号的意义就不能被正确理解。双语路牌属于一种官方标识,其重要性显而易见。它必须清楚明了,完全符合标准。它的语言文字必须没有歧义,不会被人误解。在语言学家看来,它们是语言规范的具体体现,语言符号应遵循的不同标准都被糅合于其中。比如,书写和拼写规范、语体规范以及特殊符号(比如箭头) 的使用规范等。正是这些规范使双语路牌成为一个个的符号行为体(semioticactor) ,路牌的意义只能在这些规范的合力作用下才能传达给受众。换句话说,每块路牌都是一个复杂的人为的符号行为体,我们要在“移动”的情境下对其特征进行分析,发掘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及功能。而不是想当然地、简单地把它归入英语问题或翻译问题。在社会语言学家看来,所谓的英语问题其实是符号所遵循的某个规范或标准出了问题,而这种“非标准”只是在某一层面上对标准的偏离,它遵守的是另一层面的标准和规范。另外,非标准和非常规的语言现象都可看作是向标准和规范的看齐和靠拢,因为语言使用者潜意识中都有这样那样的标准存在,但由于处在地域性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以及对语言资源掌握的不完整性等,决定了它们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标准,而永远是向标准的无限靠拢(Blommaert,2012) 。
往更抽象的层面说,不同路牌背后存在一个由各种规范和标准所构成的巨大的社会网络,这个社会规范网络制约着语言符号的变化与变异,使其超多元性或复杂性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每块路牌的实际功能的实现与否,也就是它的交际潜能,反映为语言符号对各种规范的不同程度的遵守和违反(kroon,Dong & Blommaert,2011) 。
(四) 移动性
“移动”是全球化的核心,而“移动性”是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的核心,因为它是引发超多元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对静态时空观的挑战。Blommaert(2012) 把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称作“关于分布的社会语言学”,而把自己的理论称作“关于移动的社会语言学”。他认为空间不是一个物理平面,而是垂直分层的抽象空间,语言和图像等符号本身可以跨越时空、言语库和社会指向而移动,并改变形态(Jan Blommaert,高一虹,Sjaak Kroon,2011) 。也就是说,包括人和语言符号在内的各种同语言有关的因素都可以在物理空间中移动,同时也在社会空间中移动。
移动性要研究的话题就是不同语言如何赋予人不同的移动潜势,人如何通过语言在社会空间中移动,人如何通过语言获得或丧失移动潜势。具体到双语路牌,我们一方面要考虑不同的语言符号,比如汉语拼音和英文拼写在特定情境下的移动潜势; 另一方面,还要考虑移动的人在看到双语路牌后的心理反应。在中国情境下,在北京、上海、广州等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哪种语言符号的移动潜势更大? 汉语拼音还是英文翻译,还是二者的混杂? 作为移动的人,外国游客在看到双语路牌后的心理反应是什么? 为什么? 诸如此类的问题是移动性所关注的核心。
三 公示语翻译景观与全球化社会语言学
为了解释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的几个核心概念,我们以北京市学院路及其周边地区的双语路牌(一种常见的公示牌) 为例。这个地区是中国高校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国家科技创新的聚集区,其双语路牌最能体现北京多元文化的全球化和本土化、标准性和移动性。这里我们将每一个单独的路牌作为一个分析单元,所有这些路牌把语言景观划分为抽象的区域,各个区域由其所遵循的不同规范或标准为代表,这些规范或标准是文中要讨论的焦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全球化社会语言学将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 双语路牌及其所构成的语言景观有什么特色? 2) 这些特色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动因?
(一) 双语路牌中的问题举例
清华东路地区有两个双语路牌,这两个路牌有两种译法: 完全拼音化的“QINGHUADONGLU”和英汉夹杂的“QINGHUA East R d”; 其中,汉语拼音(以下或简称“汉拼”) 的是大写,英文的只是首字母大写,“R d”是简写; 另外,“清华东路”如何分词? 它的拼音应该是字与字分开的“QING HUA DONG LU”,还是全部连写的“QINGHUADONGLU”? 还是词与词分开的“QINGHUA DONGKLU”? 北四环路也有两个路牌,究竟是“N. 4thR ing R d”还是“BEISIHUANLU”? 对于外国游客来说,“N. 4thR ing R d”和“BEISIHUAN LU”是不是同一条路? 另 外,“BEISIHUAN ZHONGLU”该如何分词? 是 “BEI SI HUAN ZHONG LU”,还是“BEISIHUANZHONGLU”,还是全部连写为“BWISIHUANZHONGLU”? 为了方便外国游客,按道理说,地铁和公交站牌应该提供英文标识,可北京市“地铁西土城站”只给出了“站”的对等词“station”。
“地铁”没有翻译,而“西土城”只提供了汉语拼音。奇怪的是,公交站牌全部使用汉语拼音,字母全部大写,而且不管是字与字还是词与词之间都没有间隔。这样的翻译是不是形同虚设?是仅仅为了向全球化看齐,为了看起来像英语,还是出于某种更深层次的考虑?
综上所述,这些路牌中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是“一路两名”,也就是完全汉拼和汉拼 + 英译两种译法。根据我们的调查,可以大胆地说: 只要路名中牵涉方位词,而这个方位词又没有和路名融为一体,它的英文标识就很可能存在完全汉拼和部分汉拼两种形式。杨永林(2012) 也指出,“街道名称标志一路两名的问题,广泛地存在于全国各地”。从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角度来看,学院路街道双语路牌的总体特色为汉拼和英译混杂。其中,汉拼因素又多于英译,也就是本土化趋势明显强于全球化。当然,完全、绝对的全球化是不可能的,如何达到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完美平衡才是我们的努力方向。由于街名问题牵涉复杂的文化差异和语言习惯等,很难实现完美的全球本土化。
(二) 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的解释
全球化社会语言学其实是一种语言社会学,它更强调对语言现象所引发的有关社会问题的思考,它是针对多语和多方言、侧重社会分析的语言理论。其核心概念———标准性和超多元性能从另一个角度更好地解释以上提到的双语路牌所反映的社会现象。
第一,双语路牌的标准性问题。双语路牌标准化、规范化的问题首先要从政策层面来看。我国的语言文字政策是推广普通话。地名的罗马化拼写方式完全符合这一国策的具体要求。
但实际操作中,拼音化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一个汉拼对应的不是一个汉字,单靠一个拼音符号很难区分所指对象。对于不懂汉语的外国游客来说,汉拼对他们更是毫无意义。公交站牌全部采用汉拼,这从一方面说完全遵守法规; 但另一方面则是与全球化相距甚远,甚至背道而驰,不符合与国际接轨的城市规划总精神。看来,由标准所构成的社会空间是分层的,在某一层面上对标准的遵守,就是在另一层面上对标准的偏离。
另外,既然这么多路牌都存在汉拼和英译两种形式,是否说明它们各有各的标准? 即两者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只是所依据的章法不一样。为此,我们仔细查阅了这方面的规章,结果发现,确实有两套不同部门制定的标准: 支持街名、路名用汉语拼音拼写的依据是 1986 年的《地名管理条例》和2000 年10 月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语言文字法》明确指出: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的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支持英译(更准确地说,是部分英译) 的依据是1999 年4 月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以及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北京市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2006) 。该《英文译法》的“道路交通”部分明确规定: “有指示方向含义的方位词译成英文; 而当方位词与地名固化成为一体时,方位词采用汉语拼音,如东直门(DONGZHIMENG) ; 序数词采用字母上标形式,名称中的数字直接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看来,有别于《语言文字法》的完全拼音化路线,这个标准是支持英译 +汉拼的部分拼音化路线的。同样是国家标准,却出现了不同的标识规定,所以,出现混乱的局面也就不足为怪了。
还有,从语言层面的标准来看,区别通名和专名的标准是什么? 是不是方位词、数目词等一律归通名? 但实际问题是,有的方位词已经和地名融为一体,很难区分什么是通名,什么是专名(谢俊英,2007) 。比如,“左安门”“右安门”中的“左”“右”; “西钓鱼台”中的“西”等; 是不是在专名和通名的划分上存在一个连续统? 从完全不可分(比如“中关村”) 到可分与不可分的两可之间(如“北京西站”) ,再到完全融为一体(如“西直门”) ? 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方位词到底应该采用汉拼还是英译?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单独撰文详加讨论。
最后,从体例标准来看,这些路牌是否符合书写的规范性? 汉语拼音的标准是什么? 大写还是小写? 如何分段? 比如,“长安街”应该是连写的“CHANGANJIE”? 还是按语义结构来分,即“长安”和“街”分开的“CHANGAN JIE”? 还是每个字之间都要隔开? 英语的书写标准又是什么? 首字母大写还是全部大写? 什么时候用简写? 用什么字体? 如何使用标点符号?总之,一块路牌所牵涉的标准之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可见标准性在研究语言景观时的重要性。如前所述,如果我们把每一块路牌都看作一个交际行为体,它所关联的整个交际活动中还有两个因素值得关注: 1) 路牌的官方制作者; 2) 看到路牌的行人。从制作者的角度来说,其所依据的标准以及这些标准所反映的社会心理动因是什么? 从普通行人的角度来说,看到某块路牌后,其心理反应是什么? 路牌是否真正实现了其应有的指路功能?
第二,双语路牌的超多元性问题。所谓超多元性,首先体现为双语路牌所依据的规章的多元性。其实,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管理部门条块划分和各自为政。道路交通管理部门采用“英译 + 汉拼”的形式,而地方公安管理部门则主张全部拼音化的形式。于是,“北四环路”就有了“N. 4thR ing R d”和“BEISIHUAN LU”两种标志方式。其次,不同规章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和心理认同存在差异。在官方层面,以城市交通管理者和英语学者为代表,认为路名的通名部分应该英译,因为这是国际化的做法; 而以地名学家和语言规划专家为代表,认为路名的拼写应该使用汉语拼音,只有这样才符合地名拼写的单一罗马化原则。而这背后强调的是文化认同,也是民族尊严问题,即采用汉语拼音是我国政府行使国家主权的一种象征。总之,命名的正确与否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事关国家主权、民族形象、经济发展、资源战略的宏大问题(杨永林 2012) 。
在非官方层面,普通行人往往觉得汉语拼音的存在是一种“多余”。他们认为,制作者这样做仅仅是为了看起来像英语。他们主张完全英译,因为他们眼中的国际化就是英语化,而英语化是一种时尚和潮流,和民族尊严没有多大关系。另外一些人则支持完全汉拼,他们认为:采用汉语拼音并没有对外国游客造成多大不便。外国游客既然来到中国,就不妨客随主便。
况且,他们在来中国之前就多少学过一点汉语,很多人更是不认汉字只认拼音的。所以,汉拼路牌的存在无可厚非。还有一些人,特别是对英语了解不多的人,对汉拼和英译相混杂的双语路牌感到很亲切,因为他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就经常使用这种土洋结合、半土不洋的英语。他们的语言资源库是超多元的,既有普通话和汉语方言,也有英语和其他语言的片段知识,汉拼+ 英译的双语路牌和他们的语言资源库性质不谋而合。或者说,这种语言混杂形式已经进入了他们的“集体无意识”,对于由语言混杂而引起的“一路两名”问题也就见怪不怪了。
四、 结论
双语路牌是一种语言符号,这种语言符号的背后存在一个复杂的规范网络,对不同规范的遵守与违反构成了某个路牌的交际潜能。同时,双语路牌也是一个交际行为者,对整个交际行为的分析与理解是全球化社会语言学和以往的研究分道扬镳的地方。以往的研究大多只侧重翻译问题和语言问题,没有把整个交际活动中的相关因素都考虑在内,对社会语言现象进行从宏观到微观的全面的分析和描写。相反,全球化社会语言学不再满足于“某个路牌传达某个特定意义”这样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把路牌看作交际行为者。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对交际活动中所参与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并把它们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以更好地解释语言符号背后的社会现象。
全球化带给我们一个研究语言与社会关系的良好契机,也展示给我们一个异常复杂的社会语言空间。在这个体系中,每个人都有极其复杂的语言背景和语言经历。由于各自的社会环境所限,每个人可资利用的语言资源的种类和数量又不尽相同,造成每个人的“言语资源库”的超多元性。这种超多元性由移动性所引发,也只有在“移动”的情境下去分析和描写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参考文献:
[1] 戴宗显,吕和发. 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2005,(6) .
[2] 胡文仲.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3] 李克兴. 试析深圳的英语弊病及翻译谬误[J]. 上海科技翻译,2000,(1) .
[4] 李 贻. 语言景观研究法: 对广州北京路的历史性调查[J]. 海外英语,(13) .
[5] 刘士祥,尚志强,朱兵艳. 海南公共场所汉英标识语现状剖析与规范化研究[J].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6) .
[6] 罗选民,黎士旺. 关于公示语翻译的几点思考[J]. 中国翻译,2006,(4) .
[7] 王德庆,郭嘉曦,左静宜. 北京旅游景点公示语英译状况管窥[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3) .
[8] 谢俊英. 北京奥运语言环境建设研究[J]. 山东体育科技,2007,(6) .
[9] 杨·布鲁马特,高一虹,沙克·克霍恩. 探索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 中国情境的“移动性”[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6) .
[10] 杨永林. 中文标识英文译法手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
- 相关内容推荐
- 西方影视作品翻译中美学意识的表达2014-09-15
- 翻译交流中模糊语言学的运用2014-05-17
- 俗语翻译中的中外文化差异现象、成因及其消解2014-10-24
- 语言景观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困境2014-10-17
- 四六级翻译新测试题型的社会语言学特征2015-06-09
- 社会语言学在旅游语言景观研究的深入的研究2018-08-01
- 上一篇: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内容和切入点
- 下一篇:日语网络语言变异的形式及其网络语言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