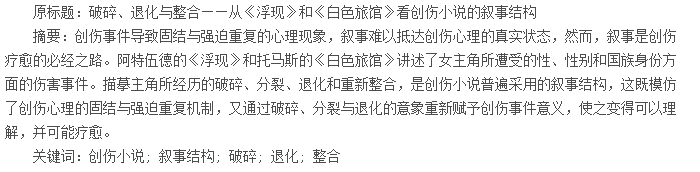
创伤小说( Trauma Fiction) 指的是描述精神创伤受害者的体验与经历的小说。据精神分析理论,主体遭受到意外或残酷的事件( 如暴力、战争或政治迫害) ,精神心理无法承受其冲击则会造成创伤。创伤小说勃兴于 20 世纪,是对充满战争与暴力的历史的回应。作为小说的亚文类,创伤小说擅长于再现受创伤主体的精神世界和心路历程,勇于探问创伤主体与社会历史的创伤关系; 它既援引精神心理的专业知识,又紧扣个体的生命故事展开叙述。
精神创伤所损害的是主体对创伤事件记忆的准确性,语言往往难以回叙创伤的经验,由此,创伤小说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寻找叙述的语言与形式。基于这一根本矛盾,探讨创伤小说的叙事结构,有助于理解精神创伤与语言、叙事的复杂关系,深入探究其叙事形式与内容、主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创伤小说在叙事上共同的结构特征,有助于深入理解创伤小说作为一个亚文类的特质。
本文选择两部重要的创伤小说为分析对象。
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浮现》( Surfacing,1972) 记述女主角返回魁北克的家乡寻找失踪的父亲,为疗治创伤而独自留在孤岛。
英国的 D. M. 托马斯的《白色旅馆》( The WhiteHotel,1981) ,女主角丽莎因歇斯底里症而向弗洛伊德求医,后来在赞比亚大屠杀中丧生。这两部小说都从女主角遭遇的暴力出发,透视社会历史的灾难事件,描述创伤事件导致的破碎与退化的心路历程。它们风格各异,却有着类似的叙事结构。
一、精神创伤与叙事
在精神创伤领域,弗洛伊德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固结( fixation) 和强迫重复( compul-sive repetition) 。这两个概念也是理解创伤与叙事关系的关键。弗洛伊德认为,“对于创伤性神经症来说,其病根就在于对创伤发生的那一刻的执着……‘创伤的’一词具有的正是一种经济意义。”[1]( P. 240)后来,弗洛伊德在《超越唯乐原则》描述了创伤与强迫重复的关系。患者会反复梦见所遭遇过的事故情境,然而,这些梦不能解释为满足愿望的文本。“强迫重复仿佛是一种比它所压倒的那个唯乐原则更原始、更基本、更富于本能的东西。”[2]( P. 23)创伤导致的幻觉与梦境强迫重复出现,超越了唯乐原则。主体把过去压抑的记忆和感受看作当下的体验来重复,而不愿视之为往事。
强迫重复与固置会相互强化,导致症状加剧。
精神创伤抗拒叙事。创伤事件对心理产生强大的冲击力,导致受害者产生失落、麻木、无意义的感受,却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哲学家齐泽克( Slavoj ?i?ek) 认为: “创伤的本质恰恰是因为事件太可怕乃至无法记忆,无法整合到象征的世界。”[3]( P. 272 -273)主体寻求一吐为快,但所言说的已经不是事件本身。鲁斯( Cathy Caruth) 在《沉默的经验: 创伤、叙事与历史》一书阐释了叙述与创伤之间的悖论: 个体在经历重大创伤后不愿意面对创伤的事件。然而,创伤永远是一个“伤口的故事”
[4]( P. 2 -3),不断地爆发和重复,形成有自身结构脉络的文本,主体在不断重复的叙述中积累面对创伤的力量。这些学者均强调,强迫重复的已经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经过心理机制过滤和转换之后的语言、意象和故事。由此,文学创作的挑战在于如何表现这种难以整合到象征世界的、无以言说的创伤记忆。
创伤伤害的是精神心理,损害的是语言的能力,疗治的方式恰是要从言说和书写中寻找。弗洛伊德针对歇斯底里病人的治疗,就开创性地采用了谈话治疗的方式,鼓励病人说出她们的梦、创伤与记忆。创伤者需要以叙事来宣泄,尝试重建与断裂损毁的过往的联系。精神分析学家简纳特( Pierre Janet) 认为,“创伤记忆无意识地重复过去,叙述记忆则认识到所述的是过去的事情……把创伤记忆转变为叙事记忆,才可能得以疗愈。”[5]( P. 140)拉凯布拉( Dominick LaCapra) 在《再现大屠杀》中归纳暴力幸存者的叙述文本: “创伤病征的重复展演以及压抑的强制回返,无非是幻想的愿望,希望身心获得统一和重新整合,以治疗创伤、获得救赎”[6]( P. 193)。
针对中国在 20 世纪数度遭受的战争与暴力创伤,张志扬强调文字的重要作用[7]( P. 70)。叶舒宪认为“故事讲述行为本身蕴涵着对听者的身心的巨大治疗能量”,“叙事治疗的基本医学原理在于,叙事本身的心理学动力因素具有意识的引导和潜意识的激活之双重作用。”[8]
可见,叙事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只有透过语言、文字和叙事的反复清算与消解,才可能克服创伤。
确实,故事具有疗愈的作用。二战之后童话书销量大增,其疗愈创伤的功能备受关注。《一千零一夜》就表明了故事具有化解矛盾与拯救性命的作用。相对而言,创伤小说的优势在于理解与表达,把难以理喻和难以言说的创伤经验转化为言说,它们透视创伤的症状,通过叙事抵达创伤者的精神心理深层。基于此,风格各异的创伤小说类似的叙事结构,着力表现创伤主体精神心理发展的四个阶段: 固置与强迫重复、破碎与分裂、麻木与退化、重新整合。它们摹仿精神创伤的形式与症候,重新建构灾难事件中那些不可理喻的细节,使之变得可以理解、表达和接受。
以下将通过分析两篇小说的叙事结构,展示创伤小说如何围绕固置与强迫重复、破碎与分裂、麻木与退化、重新整合这四个阶段,用不同的象征意象与故事来展示精神创伤者的世界。
二、《浮现》:破碎、退化与回归大地
阿特伍德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浮现》在中国的译介走过一些弯路。赵雅华和李英垣翻译的版本名为《假象》( 中国文联出版社,1991 年版) ,后来蒋立珠译为《浮现》,都是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假象”这一书名虽然不准确,却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主题: 无名的叙事者“我”关于丈夫、婚姻和孩子的回忆都是假象。事实上,“我”从未结婚生子,而是与有妇之夫恋爱、怀孕,被迫做了人流。翻阅国内相关研究,这部小说先是被解读为女性寻求精神解放的历程,后来被解读为生态主义小说。主人公的幻象与谎言的心理机制却没有得到深入分析。
“我”的幻象与谎言突显了其创伤体验。创伤导致强迫重复,“我”固置于被背叛和被迫人流的时刻,以梦、幻觉和回忆的形式不断重现,如卡鲁斯所描述的: “受到创伤,精确地说就是被一个意象或一桩事件所控制”[4]( P. 4 -5)。为了抵御创伤的冲击,“我”试图以忘记来疗愈创伤: “就像一个连体双胞胎婴儿那样被人从我身上扯掉,我自己的肉便失去了……我必须忘却。”[9]( P. 53 -54)。理智是想要忘记,但创伤的心理运作却顽固地重现往事,逼迫主体回到创伤现场,往事与当下相互交错,繁衍出一系列谎言。谎言是“我”创造出来抵御创伤冲击的,但它的控制力度并未比创伤事件本身更弱。
回乡寻找父亲的旅程中,叙事者描述沿途正在枯萎的白桦树、已经枯死的榆树林、炸药炸开的路段、展览驼鹿招徕客人、被打死挂在树上的苍鹭、大妈的断臂; 她回忆战争、纳粹、哥哥差点被淹死、母亲的死亡、自己的丈夫与孩子。叙事者内心的破碎投射到外在的世界,家乡在她眼里充斥着残缺、破败、冲突、死亡与毁坏的景象。旅程之初,她没意识到这是她内在意识的投射,亦无力反省自己的谎言。她的叙述前后矛盾,是不可靠叙事者。随着对家乡、土地和自我的接纳,她体验到身心的破碎与痛苦: “我被掏走了什么,我被切掉了什么……他们把死亡像种子一样种在了我身上。”[9]( P. 178)真相也陆续揭示出来。
精神创伤导致主体把世界体验为破碎的图景,进一步把世界看成割裂的。被劈开的河狸、肢体分离的士兵、被剖开的洋娃娃,杀戮无处不在。“我”被割裂为二,自己是麻木和死亡的那一半,“那声音不是我的,它发自一个穿着我的衣服的人。”[9]( P. 131)分裂的自我以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方式看待问题。《浮现》出现的二元对立难以完全穷尽,主要有: 生/死、乡村/城市、加拿大/美国、魁北克/加拿大、英语/法语、女人/男人、农业/商业、健全/残缺、原始/文明、世俗/宗教、和平/战争。熟悉与令人舒适的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坏的。“我”无法以整全的生命去感受世界。讽刺的是,“我”的三位朋友也一样,现代都市的生活让人麻木和分裂。
叙事者难以面对创伤,她采取的办法就是躲到客观、理性和麻木的背后,不投入情感,试图与创伤事件保持距离,以逃避痛苦。这也是现代人普遍采取的心理机制,“我”的朋友沿途拍摄“随意取样( random sample) ”的影片,没有明确的主题与故事,只收集机械的、破碎的影像片断。同理,叙事者在虚假与真实相混杂的记忆库里编辑她的“随意样本”,以她的见闻、回忆和幻觉来“展示”她的精神世界。然而,逃避无法真正疗愈或减缓创伤的症状。在第 12 章的结局,“我”对自我有了新的认识: “我真的被锯为两半……我是错误的一半,是分离的,是末端的。”[9]( P. 133)正是透过这个痛苦的认识,她获得了直面创伤的勇气,认同死亡的胎儿———我就是那个被杀害的胎儿。
胎儿是生命,而非一团细胞组织。“我”意识到,正是人类长久形成的对生命的漠视,才会以“它”来称呼胎儿,轻易扼杀它,并找借口说它不是人,不过一团细胞或一个动物。“我”的情人“谈论着那件事,好像那样做是合法的,就如同割掉一个疣那样简单随意。”[9]( P. 179)然而,阿特伍德尖锐地指出,暴力和虐杀的根源是同样的。人类只有学会爱惜动物与植物的生命,认同并尊重一切生命,才会彻底根除虐杀的本性。阿特伍德在宗教上认同泛灵论,相信万物有灵,她的小说也贯穿这一理念。《浮现》借助一位敏感而渴求找回自我的创伤者的叙述,反复谴责钓鱼、宰鱼、打猎、砍树、开路等毁坏大自然的行为,展示了人与万物共鸣、相同、和应的可能。
“我”对胎儿被杀害这一事实的接纳,是疗愈的转折点,这意味着她有了面对创伤真相的勇气。
阿特伍德探讨了一种彻底的认同,没有借口,没有退路,“我”要像被杀害的胎儿一样,脱离人类社会,回归原始的生活方式。她烧毁了文明社会制造的便利工具与舒适设施,放弃了语言、名字、熟食和住房。她感受到神力的召唤与驱动,渴望潜回到动物、植物的世界。她潜行在森林与湖泊之间,与大地亲密无间,原来二元对立的界线被消解、抹平; 她与( 一度拒绝认同的) 祖先、大地重新融合,过着“返祖”的生活。最终,她从深湖中浮出来,回到木屋,重新面对爱人和邻居的呼唤,选择未来,而非逃避现实。她拒绝成为无能的受害者。
《浮现》围绕“我”的身体与情感所遭受的创伤,把个体、族群和环境所遭受的创伤联系起来。阿特伍德认为,受害者可以从三个角度去定位:“你是否属于一个受伤害的国家,一个受伤害的群体,是否是受伤害的个人。”[10]( P. 36)造成这些伤害的根源是类似的,彼此同构的。确实,“创伤记忆既是个人的,也是家庭的、社会的。”
[11]《浮现》写出受伤害的个体,在破碎与分裂的世界里遭受梦魇的反复折磨,变得麻木和迟钝,最终以潜入深湖、回归大地而获得重新整合的力量。这位无名女性的经历,同时道出了女性群体、加拿大人、现代人共同遭遇的暴力、入侵与生态破坏等的创伤,探讨了疗治的可能。
三、《白色旅馆》:分裂、婴儿化与伊甸园
D. M. 托马斯和阿特伍德一样,以诗歌闻名于文坛,小说创作亦屡有佳作。《白色旅馆》糅合了诗歌、病历、书信与记叙文,试图逼近创伤者的精神世界,展现那难以用言语描述的大屠杀悲剧。
女主角丽莎极具音乐天赋,后因患上歇斯底里病而中断音乐事业,并放弃了婚姻。1934 年,她回到乌克兰开始新生活,却遭遇大屠杀。
如果说阿特伍德的《浮现》透过女主角的回乡之旅,把精神创伤与环境恶化、民族身份危机等议题连结起来,那么,《白色旅馆》透过丽莎的歇斯底里病把个人创伤与精神分析学科、大屠杀事件等联系起来。已有研究主要是从历史叙事和后现代叙事的角度来解读《白色旅馆》的叙事结构,而忽略了它独具的创伤叙事结构特征。
面对创伤,丽莎也“创造”了各种文本。她向弗洛伊德求医时,讲述的都是谎言,或者是自己都相信了的幻觉。根据她的陈述,她五岁时,母亲死于旅馆的火灾,她因此非常害怕成为母亲,最终离了婚。母亲、姨父、姨母都善良且关爱她,她的初恋也纯真美好。1931 年,她写信给弗洛伊德,修正了之前的叙述,透露了一系列有关家庭乱伦、犹太身世、未婚怀孕的事件: 她三岁时,母亲与姨父偷情被她撞见,两年后母亲和姨父双双死于旅馆的大火; 初恋情人 A 让她怀孕,她为此而终止了舞蹈事业。这一版本充满背叛和伤害,透露了她早年经历的创伤事件。
创伤导致丽莎陷入强迫重复的梦境与幻觉之中。托马斯并不认为现实主义的手法能够触及精神层面的真实,他深切明白,“人的灵魂是一个遥远的国度,无法接近、无法探访”[12]( P. 222),于是,他把现实与幻觉拼接起来,用诗歌、病历与书信等体裁来描写破碎精神世界的某个侧面; 用变幻不定的身体感受与幻觉来折射内在心理。丽莎在诗歌中写道: “如今我成了一个破碎的女人,辗转回家来,破碎不堪。”[12]( P. 4)“准是体内的器官被撕裂”[12]( P. 10)、“乳房被割下”、“将我的子宫全部割去”[12]( P. 11)。她分裂的身体表征了内心与外在环境的溃败和灾难,她的幻觉引导读者游历了曾经埋葬她母亲的白色旅馆。旅馆遭受大火、燧石和洪水的肆虐,死亡无数,这折射了丽莎精神心理所经历的煎熬、冲突、恐惧与挣扎。
丽莎所经历的创伤导致了人格分裂。丽莎的分裂可以从她的六个命名看出来: 年轻女人、厄尔德曼、伯恩斯坦、莫罗佐娃、克诺普尼卡、安娜。厄尔德曼是她父亲的姓氏,代表了犹太身份,这一身份导致她遭受水手的侮辱和丈夫的痛恨。于是,她把姨父看作生父,“这样就可以问心无愧地跟丈夫继续一起生活,并且怀孕。”[12]( P. 168)矛盾的是,想到母亲与姨父通奸,她又无法忍受。丽莎无论分裂出多少个自我,依然无法逃脱困境,人格分裂使得她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白色旅馆》的二元对立包括生/死、善/恶、饱/饿、欢愉/悲剧、生育/不孕等等。D. M. 托马斯擅长写分裂的人格,他的第二部小说《诞生石》( Birthstone,1980) 的女主角就分裂成三个人格。女主角说: “人格分裂是由于一个人独立无法处理那些不可承受的现实,然而,有什么现实是可以忍受的吗?”[13]( P. 25)破碎的幻觉、分裂的人格和死亡的恐惧困扰着丽莎,她的生活陷入倒退和婴儿化的状态,她的性幻想中活跃着婴儿般的想象。她写的《唐璜》诗歌描述了吸奶的场景,这意象一直贯穿到小说最后。吸奶是婴儿维持生命的方式,小说中的弗洛伊德把这归结为“婴儿幸福的自恋心理”[12]( P. 101)和“女孩到了俄狄浦斯阶段都会滋长对母亲的破坏性冲动……为她父亲生一个孩子。”
[12]( P. 121)在琳达·哈琴( Linda Hutcheon) 看来,“她的性幻想显现在表层,更符合( 女性的) 克莱因的分析( 从母亲、乳房的角度) ,而不是( 男性的) 弗洛伊德分析( 从阳具或阳具缺失的角度) ”[14]( P. 233)。丽莎对母亲的病态依恋,并非普遍的俄狄浦斯阶段的挫败,而是具体的创伤事件的冲击,导致她倒退回到婴儿的状态。
“营地”一章描述了乌托邦式的美好乐园,在那里,丽莎得以和母亲团聚,与父亲通了电话,杀人凶手人性复归,与小孩子们一起玩耍。这个结尾备受争议,哈琴认为这是“挑战了人文主义叙事中所固有的界限。”[14]( P. 239)罗伯森( Mary F. Ro-bertson) 认为这个结局是个败笔,因为它选择美学意义,却放弃了伦理追问,没有起到道德劝喻的作用[15]。
《白色旅馆》的大团圆结局所招致的批评,在创伤小说中并非特例。托尼·莫里森的《宠儿》以大团圆结局来收束杀女悲剧,被批评为软肋和败笔;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别名格雷斯》末章是“天堂之树”,格蕾丝获得赦免并组成家庭,悲剧的史实被改写; 徐小斌的《羽蛇》以母亲对女儿的完全接纳和 M 国天使男孩的引渡结篇,被认为是美化了女性的牺牲。
对创伤小说大团圆结局的解读,需要放在暴力与创伤叙事两个维度去理解。极端的暴力挑战叙事的可能性,丽莎在巴比亚所经历的大屠杀,战俘在被烧死之前被迫去焚烧尸体,明知死亡在即,他们也无法抵御烤肉味的诱惑,“伸手到烈火中去取一块肉吃”[12]( P. 224)。在人吃人、人杀人的情境中,人性被彻底泯灭,只剩下求生的本能。创伤叙事知难而上,叙写难以言表的、不可思议的震惊事件。很多作家擅长描写暴力与伤痛,但未必会深入探究创伤之机制。如莫言,他以人物的超然意志去战胜伤痛,而不是 “反思和安抚创伤”[16]( P. 94)。
“营地”一节是为死者立的界碑,以伊甸园的美好告慰亡灵。这结局并没有抵消或粉饰杀戮者的罪恶,因其语言风格与前面的叙述完全不同,并置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展示超越的可能性。它不是暴力描述的延续,而是断裂,是全新的想象视界。这个结局就像一个悠长而美好的乐章,它许诺了复活、爱、宽容和幸福。它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和虚幻的时间与地点暗示了伊甸园般的幸福。
创伤叙事的大团圆结局,不是喜剧,而是以超现实的、魔幻的方式展示另一时空的整合与团圆。创伤小说想象的重新整合与团圆,是核心价值的重建,是在反省创伤根源之后的重新认知,是治愈创伤之后的新生,是超越怨恨之后的团圆。
四、创伤叙事结构及其深层意义
创伤小说的叙事形式并非封闭而独家所有,叙事者、情节、互文、重复等的形式在其他小说也随处可见,然而,创伤小说令人震撼的是形式与主题结合,从而形成了一个植根于“创伤及其后果”的叙事结构: 本文归纳为固置与强迫重复、破碎与分裂、麻木与退化、重新整合四个阶段。
叙事从开始朝向结局,重复是控制、阻碍情节走向结局的方式。创伤精神的重复是控制、阻止心理刺激突破防线、走向崩溃的替代机制。叙事情节的推进带来阅读快感,但重复却超越快感原则。这与弗洛伊德洞察到的“超越唯乐原则”逻辑一样,另有痛苦的、朝向死亡的冲动在暗中使劲。
布鲁克斯在《情节阅读》中勾连两者指出: 叙述中的重复是“再次检查那个被遮蔽了的原因……就像侦探重新追踪罪犯的踪迹。”[17]( P. 97)叙事所启动的“侦探”,与创伤心理所启动的回访,都是受反向力量的支配。
故事情节的重复与迈向结局所产生的张力,与创伤的强迫重复与渴望遗忘的冲突类似,创伤小说在双重的意义上采用“重复”机制。《浮现》中的“我”在回乡途中又渴望逃离,回忆浮现与想要忘记彼此反复缠斗,妥协唯有出现在重新整合的时刻: “我”不再逃离故乡/创伤源起,真正融入土地/面对人流与暴力的伤痛。《白色旅馆》开篇即引入弗洛伊德,并把丽莎设置为他的病人,但精神分析亦未能治愈她的创伤,病历、病人叙述、写作诸文本都是强迫重复,以回到创伤固置之源起,托马斯设置的语言与叙事迷宫,结构上与丽莎的创伤吻合。精神创伤的重复是为了理解那些可怕的事件,叙事的重复是反复制造陌生与距离,迫使主体从不同角度审视与理解事件。
创伤小说常常采用破碎叙事的方式,在主体上对应受创主体的心理结构。《浮现》采取第一人称叙事,《白色旅馆》多种人称混合叙事。当女主角说“我”的时候,所指已经不再是意识一致的主体,而是充满裂痕、冲突和矛盾的主体。受创伤的“我”碎裂为多个主体,真实与幻觉的界限不再清晰,所指也不再那么稳定; 一如她们的意识无法操控,故事情节也不是由叙事者所主控的。理解到精神创伤的这一特点,作家才可能直面那极端残酷的现实,深入到受害者那破碎、麻木、逃避和婴儿化的内心世界。创伤叙事的真实因而必然是心理的真实,而非传统的现实主义的真实; 创伤小说对现实的表现,其价值不在于精确细腻地描摹外部世界,而是在于对主体内在精神世界复杂性的把握。
退化是摹仿或无限接近死亡的状态。弗洛伊德通过创伤心理机制提出死亡本能: “这种本能就是要求回归到无生命的状态中”,且性本能与死亡本能都意味着无数细胞的灭亡。弗洛伊德这一分析有违我们普遍的经验,文学想象也很少触及这一层面。创伤小说追根究底,探测了人类面对暴力所启动的复杂迂回的机制。《白色旅馆》以丽莎的婴儿幻觉与死亡幻想具象呈现死亡本能; 《浮现》以“我”回归野人的生活来模拟死亡。直面这种退化和麻木,需要新的语言与象征符号。如精神分析师利夫顿( Robert J. Lifton) 所言,当代普遍的精神麻木导致“去象征化”( Desymbolization) ,麻木的心灵让文学也患上失语症。而创造象征意象成为抵抗精神麻木和治疗创伤的重要方式。敢于触及灵魂的神秘领域的艺术家是勇敢的,因为“只有通过创造、保持、打破并再创造,我们才能找到足以体验生命力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形式等同于生命。”[18]( P. 70)阿特伍德和托马斯对创伤叙事形式的探索,就是通过摹仿创伤精神心理结构,寻找到一种可以言说创伤者的生命故事的叙事形式。
创伤小说采取不可靠叙事、多角度叙事、多文体融合等艺术形式,但它与现代及后现代的各种先锋叙事有所不同。创伤小说不仅关注受创主体所经历的事件背景,还关注疗愈创伤的可能性。
《浮现》和《白色旅馆》的女主角都是艺术家,她们在经历了逃避与退化的历程中,获得超常的能力。这赋予小说一种神秘、超脱的氛围,得以呈现超越人类感官与灵界的维度。从结局来看,这两部小说都想象超现实的结局,畅想恢复与疗愈的可能。阿特伍德把女主角的回归与大自然的疗伤合二为一,描画完全脱离文明的自然图景; 托马斯创造了一个家人团聚、误会尽消、欢悦自如的美好乐园。
这两部小说在想象重新整合的图景时,都浓墨重彩地铺陈了湖的意象。《浮现》的女主角多次潜入白桦湖的深处,她在湖水间体验到新的生命从体内生长出来,身体与大自然一样具有繁殖力和养育力。在丽莎的幻觉中,白色旅馆旁边有一口湖,它是洪水的来源,也是“精子寻觅子宫的入口”[12]( P. 19); 最后,她与母亲在湖边散步,体验到湖水是源自“爱之小溪”孕育的约旦河水,这象征丽莎对犹太人身份的重新认同。水是古希腊人认定的大自然四大元素之一; 在基督教文化中,以水洗礼是最常见的方式。相对于大海与江河,湖水更静逸、清澈、安全,更像母亲式的爱,更契合疗伤的作用。这两部小说都以湖水作为主人公的精神后盾,化用了湖水的纯净、融合和接纳之义。
结语
创伤叙事肇因于残酷的暴力与创伤事件,在世外桃源般美好的意象中收束,它与童话、戏剧或其他叙事一样,都诉诸于文学的抚慰与疗愈功能。
创伤小说的独特在于叙事形式的探索,在于打通精神世界与现实社会,这在《浮现》体现为叙事者打破各种二元对立,从拒绝自我到完全接纳的艰难过程,在《白色旅馆》是打破真实与幻觉、历史与虚构、理论与个案界限的勇气。主导叙事的动力不再是创伤事件的始末,而是创伤主体的精神历程,创伤导致的固置与强迫重复、破碎与分裂、麻木与失语,在这些独特的叙事架构中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叙事是治疗创伤的重要方式,因为语言是人类理解自我的主要途径; 言说意味着直面创伤并开启理解之旅程,经由语言引导的回忆,是认知创伤与重建破碎世界的重要心智活动; 经由叙事而重建的身份可以置换并超越那丧失了的身份。当今,精神创伤是时代之常见病症,如何理解和面对这一情境,是文学创作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导论讲演[M]. 周泉,严泽胜,赵强海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2][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后期着作选[M].林尘,张唤民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