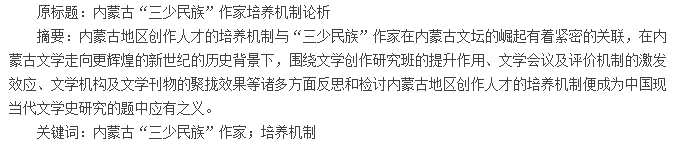
“三少民族”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异军突起是1980年代以来重要的文学现象。众所周知,最早引发文坛震动的是曾连续三次获得1981—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鄂温克作家乌热尔图,与此同时,鄂伦春族敖长福以及达斡尔族孟和博彦、阿凤等脱颖而出。此后,“三少民族”作家在文坛获得某种整体性的形象,更令人欣喜的则是除了上述作家在自己的文学园地继续耕耘外,还有大量“三少民族”作家以雨后春笋之势登上中国文坛。这种强劲势头一直持续,达斡尔族作家萨娜以及鄂温克族作家庆胜继续领跑新世纪以来的“三少民族”文学创作,“三少民族”作家在内蒙古文坛的崛起也成为新时期以来内蒙古文学的重要特征。“一个时期的文学特征,和文学体制、文学生产的方式关系很密切”,作家的生成除了自身阅历、天赋等主观原因之外,外部环境的推动、促发和影响不可忽视。如此,探究中国当代“三少民族”作家生成的培养机制就成为重要的文学史问题。
一、何谓培养机制
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看,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阶段,文学组织方式和文学生产方式呈现明显的一体化特征。虽然这种一体化特征在新时期以来有所减弱,但“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机构等等因素,不是‘外在’于文学生产,而是文学生产的内在构成因素,并制约着文学的内部结构和‘成规’的层面”。这一特点也体现在内蒙古文学中。以民族地区的文学实践实现党和国家的文化战略目标同样是内蒙古文学的基本诉求。在实现这一诉求的过程中,作家的培养和管理无疑非常重要。在1956年的内蒙古文联常委(扩大)会议中,就已经明确将“培养作家”作为工作的组成部分。
不妨将其“培养作家”的种种举措、探索和实践称之为作家培养机制。20世纪50—70年代许多蒙古族作家的出现和成功,已可看到这种培养机制的运行过程。如1953年玛拉沁夫到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1955年孟和博彦的电影文学剧本《嘎达梅林》研讨会召开,1956年敖德斯尔、朋斯克等赴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玛拉沁夫、扎拉嘎胡等被选派赴京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这些作家在经过明显的培养过程后都写出了在内蒙古当代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品。以玛拉沁夫为例,他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上学时受到名家指点,20世纪60年代的创作明显成熟,写出其代表作《茫茫的草原》;扎拉嘎胡在内蒙古大学文研班学习后从事专业创作,写出《草原雾》、《嘎达梅林传奇》等意蕴深沉、笔力雄健之作。1980年以来,较之蒙古族作家,以孟和博彦、乌热尔图、敖长福、杜梅、萨娜为代表的“三少民族”作家的大量出现以及成长、成熟的过程中似乎更能够明显看到这种培养机制强大的作用力和显著的效果。
今天看来,这种机制在实质上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方法、规则和体系乃至制度,这些方法、规则和体系在其运作过程中一般都有载体,常常是某种可见的形式或机构,实施过程中也有某种灵活性和动态性,但从较长的历史视域看有其相对的稳定性,并且由某一制度(方法)或是某些制度(方法)作用在作家身上时产生的合力而导致一定的效果、功能与意义。一般而言,这种培养机制在现实的运作层面上首先表现为对作家的直接影响,比如包括成立文学研究班,强化作家的文化底蕴,培养作家的自觉意识;当然,这种培养机制也表现为成立文学机构和作家组织,由此管理作家、制定创作计划;此外,文艺刊物“是文学创作和理论生产最后得以实现的重要载体”,文艺刊物作为园地在培养作家方面无疑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容忽视的是,作家培养机制的重要构成还包括完善文学评价机制由此激励作家,引导和推动文学创作。
二、文学创作研究班的提升作用
文学创作研究班是指集中选调有一定基础的文学作者,安排经过他们集中学习一段时期,提高其创作水平的作家培养方式。它曾在当代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命名,比如从最早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到后来的文学讲习所乃至1984年改称的鲁迅文学院。
内蒙古地区将具有文学讲习所性质的培训班称为文学研究班,1960年,内蒙古党委批准在内蒙古大学举办文学研究班,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文学研究班共成功举办6届,其中可明显看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文联的组织行为,并且这种培训方式也成为一种作家培养的不定期但常态化的组织形式。
内蒙古文学研究班对“三少民族”作家的培养从20世纪60年代肇始,在其设立之初的第一期文研班中的孟和博彦就是达斡尔族,同样是达斡尔族作家的巴图宝音则是第二期文研班的成员。可惜的是,这届文研班的学员毕业后即逢文革,影响了他们创作的进程,但在他们新时期勃发的创作热情中还是能够看到1961—1965年文研班学习的明显影响。以孟和博彦为例,文研班的学习不仅提高了他的文学素养,而且也提升了他的理论水平,文学评论成为他文学成就中重要的一部分,而文革后重返文坛的他也写出了《春的使者》、《小泉》等艺术手法更为圆熟、思想更为深邃的诗歌。
更明显与直接的影响是从1982年文革后第一届汉文文学艺术研究班在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开办(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在第一届学员的名单上有鄂伦春族作家敖长福,乌热尔图称其为“这个民族的头一位作家,是这一民族中第一位位借用汉字以艺术虚构的方式表述自己情感的人”。他在1982年的文研班学习及1985年赴京参加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讲习班之后写出了《猎村新貌》(1982年)、《孤独的“仙人柱”》(1983年)、《白桦林的回忆》(1983年)、《我们的山哟,白桦林》(1983年)、《阿美杰》(1985年)、《河边的小屋》(1988年)等有影响力的作品,奠定其文学史地位:“在鄂伦春族的创作文学中,敖长福是一个最重要的名字。”
尤其是《孤独的“仙人柱”》在敖长福的短篇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人物性格塑造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老猎人匡诺的出现“比此前所有人物都塑造得更为成功”,这篇进入文研班后写出的小说显然与内蒙古和国家两个层级的文研班对作家创作自觉、文化意识的全方位“刷新”密不可分。
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培养同样非常重要,在各级各类文研班中也活跃着女作家的身影。安娜和杜梅各是第一、二届文研班的鄂温克作家,苏华则是第二届文研班的达斡尔族作家。她们在毕业后发表的《金霞和银霞》(安娜)、《我的先人是萨满》(杜梅)、《母牛莫库沁的故事》(苏华)等作品中流露出的明显的文化自觉、政治历史省思意识,这恐怕也与文研班对其创作视野的开拓有密切关系。这些作家们后来都进入了鄂温克文学史及达斡尔文学史,文研班的进修生活是其创作路上极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文学研究班更为高级的表现形式是到中国作协或是鲁迅文学院进修,这一级别的进修对作家的影响可谓重大深远。在乌热尔图的经历中,1981年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进修一年,可以说让乌热尔图从家乡走向全国。求学期间他系统阅读中外名著,更重要的是得到老作家和老学者们的当面指教。众所周知,《七叉犄角的公鹿》就得到了王愿坚的指导,除了指出小说的缺陷,还撰写评论文章肯定其创作的独特处。后来乌热尔图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三连冠”的殊荣,出现创作上的高峰无疑与他进入文学讲习所后眼界开阔并进而具有重新开掘丰厚民族生活的能力和艺术技巧有直接的关系。萨娜到鲁迅文学院进修的经历则让她的创作呈现出明显的转向:从仅是表现本民族生活进而拓展到表现更具普遍意义的世俗生活。小说集《你的脸上有把刀》就是这种转向的明证。创作出现转向意味着作家更多元的尝试和更具创新的意识,其实没有必要评价这种转向的得失成败,作家的诗学实践本来就应当是多元和创新的。重要的是,转向之后,萨娜的创作显示出更为阔大的气象。这其中,鲁迅文学院的学习经历功不可没。
可以说,各级文学研究班对作家的作用主要是提升,提升的重要性在于点石成金。无论是在由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向作家转向的路途上,还是由一般作家上升为重要作家乃至经典作家,提升的意义都不容低估。就“三少民族”作家的创作来看,文学研究班的举办不仅有助于各民族书面文学的作家出现,而且培养出了其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一批作家,其文学史意义和社会价值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三、文学会议及评价机制的激发效应
“有关文学的重要会议,是传达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统一思想步调、布置当前任务、制定长远规划、矫枉纠偏等的主要形式。……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外部环境的变化,与重要会议的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在50—70年代文学会议往往是作家检验政治“正确性”的晴雨表,随着政治环境和文学环境的变化,对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而言,文学会议不仅能够帮助作家更清晰地分析和把握时代,而且也有助于他们把握文学发展的趋势。文学创作会议和笔会中,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学创作思想的作家们之间的彼此交流也有助于作家创作主观能动性的激发。
比如乌热尔图“1980年,作为鄂温克族惟一的一位作家走出大森林,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创作会议,使他大开眼界、获益匪浅”。作为培养“三少民族”作家的重要举措,1981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文联、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自治区分会和呼伦贝尔盟文联联合召开了一次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三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会议。达斡尔族的巴依尔(《玉石烟袋嘴》)和鄂伦春族的阿黛秀、白石、敖长福都是在这次文学创作会议上发现的新人,文学会议不仅是传达、交流文学讯息,更重要的或许在于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敖长福的成就已如前所述,阿黛秀的《第一场雪》就是她参加文学创作会谈后创作出来的,在塑造民族性格和人物的价值取向上比起早期的《星》和《林间小路》有明显的进步。“这批作者除少数因工作因素而没能坚持文学创作外,大部分都成为今日的‘三少’文学创作的骨干力量”。
这就见出文学会议具有的导向性、示范性作用及其实际效果。
1987年在鄂伦春自治旗召开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文学创作会是“内蒙古文联、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和呼伦贝尔盟文联达成一致协议,把发现‘三少’作者和繁荣发展‘三少’民族文学历史责任承担起来,决定自此之后每隔几年三单位联合举办一次全区性‘三少’创作会”,出作者和出作品是这次会议举办的主要目标。会上出现的当时异常年轻的达斡尔族作者苏莉很快受到应邀而来的《上海文学》的关注,而苏莉后来也确实写出了《红鸟》和“旧屋”系列。此后,文学创作会议的举办一直延续下来。其有效性在于:并非所有的少数民族作家都能获得自治区(省级)级或中央级会议的出席资格,设在少数民族聚居之地的会议的举办能发现更多的作家,并且也让少数民族作家意识到写作并非遥远之事,这类会议对作家的影响非常直接,且能让他们产生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认同感,作家身份的自我确认也在这个过程中缓慢发生,后续的写作因此会成为自然乃至自发之事。
必须强调,能够极大激发作家积极性的方式还有评奖制度。因其制度化的形式和评奖规则本身的科学性,任何具有专业可信度和学术认可度奖项的设置都应有其权威性。而这种权威性往往又有其极强也极为有效的导向和激励作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起的巨大的轰动效应并持续至今,他甚至让当代的很多中国作家都意识到自己离诺贝尔文学奖并不遥远。
这种导向和激励作用对少数民族作家同样有效。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主要有国家级的“骏马奖”,内蒙古自治区级的“索龙嘎”奖以及各类文学刊物或文学机构设置的奖项。前两项政府奖因其级别高和强大的影响力而成为作家广为人知的重要的传播平台;文学机构和文学刊物设置的奖项在影响力上可能不及前两者,但对作家被作家圈和评论圈熟悉也有重要的作用,它们也是评论界认可一个作家的重要信号。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一个真正的好作家往往能同时获得这两类奖项,如果他能坚持创作艺术水准较高的作品,则进入了一个获奖激发的后续创作、后续创作再获奖的良性循环中,他的作品显然会广为人知并引起研究的持续关注,他的示范激发同行的作用也会非常明显。
鄂温克作家乌热尔图的获奖对自身乃至“三少民族”作家的激励效应就非常明显。在乌热尔图1981、1982、1983年连续三年获得国家级的小说创作奖,标志着他的名字为主流文坛认可,其后乌热尔图在1985年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之后他不断求新求变、突破自我,继续写出《胎》、《灰色驯鹿皮》以及《萨满,我们的萨满》和《丛林幽幽》等风格变化明显、灌注着浓重的民族文化反思和民族形象有意识建构的文本,1993年“庄重文学奖”和1999年国家级的少数民族文学奖项“骏马奖”的获得既是对他突破自我之作的肯定,也标志着他已经是中国文坛中重要的专家。
乌热尔图获奖对其他刚刚学步的作家的激发则主要表现在鼓舞、影响。比如呼伦贝尔盟党委和行政公署在1983年乌热尔图获奖之后对他有晋升两级工资和颁发奖金的再嘉奖,这在当时是全区和全盟史无前例之举。这种奖励之中除了应当具有的导向作用,更有明显的激励后进的意图。将这种意图表达得更为鲜明直接的是1984年9月鄂温克族自治旗文化局和文联联合召开乌热尔图作品研讨会,“通报表彰乌热尔图为鄂温克民族文学作出的突出贡献,号召全旗人民向他学习,并奖给他一套民族服装”,无论直言指出还是未曾明言而依靠奖励本身昭示,总之,乌热尔图本人的创作成就及创作路向现在看来确实是带动了一批“三少民族”作家的创作,甚至有很多“三少民族”作家都将乌热尔图作为努力的方向和追赶的目标,比如达斡尔族作家苏莉就明确表示以乌热尔图为创作旗帜。这一榜样的作用在许多“三少民族”作家那里可能未曾明言,但“我盟(指呼伦贝尔盟———作者注)许多朋友大受益于乌热尔图的经验”这一当地文学刊物《骏马》主编者之语或许更能说明乌热尔图获奖巨大的带动效应。
不妨看看“三少民族”作家们的获奖情况,乌热尔图之外,敖长福以《猎人之路》获得1985年全国短篇小说奖;阿凤获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杜梅获得第三届和第六届两届少数民族创作奖;萨娜则是2005年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得主。此外,在内蒙古自治区级的获奖名单上也可以见到“三少民族”作家活跃的身影,比如巴图宝音、孟和博彦、乌热尔图、敖长福、杜梅、苏莉、萨娜、庆胜等,他们频繁在国家级和自治区级的文学评奖活动中获奖,同时还有呼伦贝尔市的同步政府奖励,这些奖励的激励作用不可小视,它从物质上和文学环境、文化空间上表达了对作家文学创作的肯定,而许多作家连续获奖就是奖励本身对作家激励作用的直接例证。或许更重要的是,奖项本身还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广泛重视。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文学会议和评价机制(奖项)对作家和地区文学发展的作用首先表现为扩大作家的文学影响力和美誉度,即令其广为人知,另外更表现为激发作用,这种激发作用不仅是指对作家本人的激发,还指带动了其他有志、有为的作家,从更长的历史视域看其确实影响深远,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本身的发展和某种文体的发展,“三少民族”作家的群体性出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而他们中的每一个作家,都可能会是未来更高级别奖项的获得者。
四、文学机构及文学刊物的聚拢效果
在1949年后的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机构或曰文学团体就是文联和作协。文联和作协的一个基本的也是主要的工作是团结培养作家、促进文学艺术繁荣。前述“三少民族”文学会议的召开就有其现实的推动力量,它是各级各类文学机构有意识培养“三少民族”作家的结果。
内蒙古文联和呼伦贝尔市文联发现作家的工作便是其自觉培养“三少民族”作家的重要举措,也是培养的当然前提。因为文革,1979年末呼伦贝尔市文联才恢复工作,这意味着作家培养工作在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才可能开展。
但幸运的是,内蒙文联和呼盟文联的一些有识之士如孟和博彦、张志彤、邓青和冯国仁等老作家们认识到在达斡尔、鄂温克和鄂伦春三个民族的自治旗寻找、培养“三少民族”作家的重要性,并在1981年春开始为期三个月的寻访工作。这项工作解决了现实和历史两重问题。出于现实的考虑,建国后直到文革结束,内蒙古地区的少数民族作家长期以来以蒙古族为主体与中坚力量,“三少民族”作家较少;另外,从历史上看,这三个民族的书面文学创作开始较早的是达斡尔族,鄂温克和鄂伦春族虽然有丰富的口头文学创作,但书面作家并不多,培养少数民族作家也就具有了解决历史问题的意味,这是文联开展这项工作的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意义。
对于作家来说,即便从最浅近的层面看,文联老作家们的工作也让他们真正聚拢起来。后续的文学创作会和修改作品的文学实践则明显提高了他们的艺术自觉。盟市级文联的工作不可能完全覆盖幅员辽阔的旗县地区,而在基层生活着或生活过的作家才可能真正拥有创作必须的生活和素材,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对少数民族地区而言,旗县级文联对作家的培养工作同样重要。“鉴于呼盟‘三少’作家的成就和第一次学习班的成绩与经验,内蒙古党委于1982年适时地决定在三个自治旗成立旗文联,以有利于发现和培养‘三少民族’文学人才”。旗一级的文联成立后,在各旗召开文学创作会、组织本旗的文学创作、团结和联络作家、扩大作家的对外联系等就成了当地文联开展工作的重要构成。
另外,文联的创立也有助于给作家们创作更好的工作环境。比如,众所周知,文革后刚恢复工作不久的呼伦贝尔市文联于1980年调乌热尔图进入本部门工作,1981年乌热尔图获得国家级奖项后被选举为文联副主席,这都为乌热尔图的后来1982、1983年连续获奖创造了当时能有的最好的外部环境。除了改善可见的物质环境和物质条件,文联的设立还有其精神指引的作用,这种精神指引不仅仅是指意识形态乃至政治方向的确立,虽然文联在设立之初就是传达国家文艺政策、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有效机构;对“三少民族”作家而言,文联团结和引领他们,让他们确认自己创作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正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新文学社团的建立促使作家们开始真正建设新文学,对“三少民族”文学而言,各级各类文联成立有助于作家们真正建设他们各自带有鲜明民族特质和地域风格的文学。甚至,因为长期以来“三少民族”文学的成就更多集中于口头文学和民间文学方面,这种文学建设就具有了开疆辟土的划时代意义。虽然一种新的文学或文体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文联的引领与聚拢在“三少民族”文学发展的起步阶段起到的是积极的、正面的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作家安身立命最终靠高质量的作品。作品发表和出版需要文学期刊,各级各类文联以出版不定期文学期刊的形式为作家们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更提供了传播作品的途径以及确立自己文学文化身份的可能。
文学期刊对作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甚至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新青年》曾对“五四”一代作家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鲁迅、胡适等作家的代表性作品曾在其上发表,《新青年》也因此成为一个文学时期的标志和旗帜。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而言,“几乎每一位少数民族作家,都是先在文学期刊、报纸的文艺副刊和综合性杂志的文艺专栏等上发表作品,然后再把作品汇集出版,分两个阶段走过来的”。可以说,是文学期刊扶持少数民族作者们走上成才之路,而作品在级别较高的刊物如《民族文学》、《收获》和《十月》等刊物的发表则有可能让作者成为作家乃至名家。
具体到“三少民族”作家,呼伦贝尔文联成立后出版了文学季刊《呼伦贝尔》,1981年第4期即以“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作者创作学习班作品选登”的专栏形式为“三少民族”作家登上“历史舞台”创造条件,同时还配发了参与“三少民族”作家发现工作的老作家冯国仁的论文《一束山花耀眼明》,该论文欢迎“三个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学青年登上文坛”,在三十年后看这是非常富于史感的论断,同时更准确地指出了该刊物的作用:培养“三少民族”作家的摇篮。安娜、杜梅、阿黛秀、敖长福等都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他们的处女作或是代表性的作品。《呼伦贝尔》在培养文学新人方面功不可没。
各地文联出版的刊物在培养“三少民族”作家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专门性”、“针对性”作用。鄂伦春自治旗文联较早创办了由当时国家副主席乌兰夫题名的《鄂伦春》,鄂温克自治旗文联则出版了《鄂温克文艺》,达斡尔自治旗也创办了《纳文慕仁》,这些刊物对培养民族作家的作用可谓将他们扶上马背,助他们在更大的文学疆域纵马驰骋。以《鄂伦春》为例,它在发刊词中就明确指出,“意在培养以鄂伦春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作者”;《纳文慕仁》更是成为达斡尔族作家荟萃之地,苏华、孟根、慕仁、孟大伟等都在其上留下了深刻的文学脚印,这些刊物也承载着他们自由先锋的思想与文学实验。
《草原》面对的是整个自治区的文学作者,即便如此,在培养“三少民族”作家上也是三十多年来费心尽力,苏华的《母牛莫库沁的故事》便发表在1991年第八期,当时《草原》给予此小说首篇位置的礼遇,同时还刊发曼德拉对该小说进行视角、语言等专业解读的专论。《母牛莫库沁的故事》后来也成为苏华的代表作。《草原》更曾设有“三少民族”作家专栏或是“三少笔会”专栏,极大地推动了三少民族作家的创作。尤其是1981年第12期的“三少民族”专号,杜梅对它曾这样评价:“这一期的‘三少民族’文学专号,看似简单,但是划时代的,标志着“三少民族”从此有了一批汉语书面作家。”
在《民族文学》、《收获》、《十月》等国家级的刊物发表作品则意味着“三少民族”作家创作可能达到的高度,更标志着他们开始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力。乌热尔图领跑鄂温克族文学,萨娜领跑达斡尔族文学与他们大量在国家级刊物发表作品密切相关,比如乌热尔图在《收获》发表的《小说三题》和《丛林幽幽》,标志着他后期小说创作对民族文化新的思索和更为自觉的小说艺术实践。萨娜更是多次在《民族文学》、《收获》、《十月》、《当代》和《钟山》等大型文学刊物以及作家出版社等权威出版社发表作品,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作家中的佼佼者,显示出主流文坛对她的创作成就的肯定以及她已经在内蒙古自治区文坛上达到的艺术水准,后来萨娜成为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与其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是相匹配的。这时,国家级的刊物对“三少民族”作家的意义是,在提供展示成就的场地的同时更提供一种资质或是保证,其直接作用就是让“三少民族”作家获得了少数民族代表作家或是重要作家的身份。这一身份的获得当然主要取决于作家自身的才能,但专业水准高、具有权威性的期刊的传播和认可在一个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文学时代其实异常重要。
五、“三少民族”作家成功与培养机制的关系
应该承认,并非所有作家的成功都是有意培养的结果,但这不意味着作家的成才不需要培养。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从来都不缺乏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作家成才情况,与此同时,也必须承认有意播种同样重要。从上述对“三少民族”作家成功原因的探析中不难发现,恰恰是多种培养方式形成的培养机制的合力,在各个少数民族族群中的文学新人被发现,后来经过一系列的实际工作让“三少民族”作家既获得作家身份,同时更在获得作家身份后自觉努力,向更高的发展目标努力。这些作家们后来又形成独立的创作队伍,决定了“三少民族”不仅具有了作家文学创作,而且这种作家文学还有着完全可以期待的未来和进一步发展的极大空间。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既然是有意播种,就应该探寻播种方法及其功能与作用,即培养机制主要由哪些部分构成,这些方法、规则乃至制度的功效如何。比如,如前在对内蒙古三少民族作家的成功的原因分析中就能明显看到这种培养机制的运行过程:文研班提升了作家们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准,几乎是点石成金般地让“三少民族”作家们有了向更高创作层面飞跃的内驱力,而各级各类文学会议和评价机制对作家起到的作用则是肯定和激发。同时,文学会议和评价(评奖)机制在很多情况下又意味着文学上的标准或是思想上价值体系,其导向作用不可忽视。而文学机构和文学刊物则为作家乃至作家群的出现提供了传播平台和空间,尤其是专门发表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文学期刊作为发表作品的物质载体又是文学机构有意识建构的一种传播空间,它们的出现是为“三少民族”作家的阔步前进而鸣锣开道。今天,历史上以口头文学和民间文学为文学主要成就的“三少民族”,出现作家、而且出现正在走向中国文坛的作家,与这种培养机制的运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另外,培养机制本身也在构成作家们文学书写的话语空间。对20世纪和新世纪的中国文学而言,任何作品都不是孤立的文本存在,作家的文学书写与其所处的文学话语空间密切相关。
当培养机制本身也是话语空间时,如何保持“三少民族”作家的独立性、独特性和差异性就成为推动“三少民族”作家创作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问题。毕竟,“三少民族”作家所具有的独立性、独特性和差异性,曾是这个培养机制开始运行最重要的原因,这是肯定培养机制作用时应该反思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