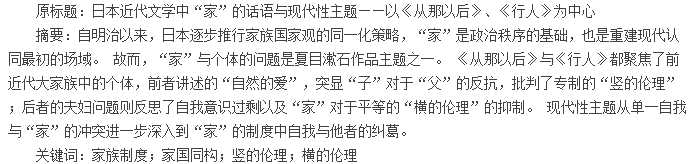
一、“家”与夏目漱石文学
日本战后著名家族社会学者森冈清美说:“人类社会不管哪里都有家族,通过世代再生产而维持社会发展。”日本属于家国同构国家,“家”是社会的基础,是确立自我同一性的最初场域,必然成为文学的话语资源。明治初期,二叶亭四迷的《浮云》与森欧外的《舞姬》作为日本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代表,描写的是明治知识分子都束缚于立身出世以光耀门第、振兴家运的家族思想中,亡父的设定隐喻着自我同一性的缺失。明治四十年代,自然主义的私小说甚至把笔端局限于琐碎、 阴晦的家族生活,田山花袋的《生》与岛崎藤村的《家》等都“限于屋内的光景”。日本近代文学的现代性主题交织着“家”的话语,包括自由恋爱与政略结婚、“新家”与“旧家”、父子冲突、夫妇关系等。实际上,明治时代颁布的户籍法与《明治民法》最终以“法”的形式确立家族主义的国体,“家”与近代天皇制压抑着追求自由民主的自我意识、 自我解放的诉求必然表达为“个体”对于“家”的反抗。
在这种时代语境中, 夏目漱石尤其注重对于“家”的反思。除了 《我是猫 》、《草枕 》等若干作品以外,夏目漱石始终把自我同一性置于“家”的语境中进行思考。《哥儿》的主人公在家中的境遇突现没有家督继承权的次子的悲哀。《虞美人草》讲述的是围绕家督继承问题的明争暗斗。《三四郎》的青年主人公追求自由恋爱以建立“新家”。《门》描写了夫妇理想的爱,《道草》、《明暗》的焦点也是“家”的纠葛。实际上,有关“家”与个体的主题是夏目漱石个人体验的升华,二度沦为他人养子的童年创伤使他十分清楚“家”对于自我的扭曲与压抑,因为个体只是实现家族延续的工具性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夏目漱石对于“家”与自我的反思有一个深化过程,批判的焦点从“家”的专制逐渐转向理性自我的局限性,集中反映于《从那以后》与《行人》的主题差异。《从那以后》(1909) 讲述长井代助为了以前的恋人三千代决心回归“自然”而与家族决裂的故事,《行人》(1913)则通过长野二郎的视角讲述了哥哥一郎与妻子阿直的夫妇纠葛。在两部作品中,前近代的“旧家”构成了背景,而探讨的主题由“自然的爱”转向“性的争执”。有关两部作品的家族主题,很多学者进行了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研究,丰富了作品的阐释框架。其中,石原千秋的解读最具代表性,在《漱石的记号学》与《反转的漱石》中全面考察了漱石文学中的家族符号。《作为反家族小说的〈从那以后〉》把解读焦点从三角恋爱转到家族符号,提出全新的见解:“确立近代自我的故事就是那些好像代助那样遭受‘家’的排斥的男子在 ‘家 ’的外部所演绎的 ‘家 ’的话语。”同时,《存在阶级的言语〈行人〉》写道:“长野家的言语由家族/非家族、男/女、父/母等各种各样的差异组成,处于顶端的则无疑是一郎。”这些解读点明了主人公在“家”的结构中的位置隐含的文化意义与主题效果。在同一个延长线上,三浦雅士的《恋爱与家父长制———〈行人〉注解》也总结道:“《行人》真正的主题不是近代知识分子的苦恼,而是前近代的家族制度问题。或者说,知识分子的一种丑态,他们在近代化的家族制度当中无法完成家族意识的近代化,只能躲进西方著作、艺术或者汉诗俳句。也可以说,这些知识分子成为家督继承者即家长造成的悲剧。”
这些文学评论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阐释框架,但是,两部作品的关联性与差异性需要进一步考察,通过解读可以知道两者的家族叙事各有侧重点,反映了不同的自我认同观念。在此,本文将结合叙事理论解读《从那以后》与《行人》家族叙事与自我认同的主题关系。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家”
明治文学对于“家”的关注与时代语境息息相关。随着户籍法、《明治宪法》、明治民法的颁布,原本盛行于武士阶层的“家”的制度推行到一般民众并成为国民国家的统治装置。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教育制度潜移默化的教化,“家” 的话语与天皇专制结合起来并逐渐渗透到国民意识,作为一种“传统”发挥压抑与序列化的功能。犹如川岛武宜所指出的:“明治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家族法的问题伴随着家族道德的问题一直在政治上十分重要。与之相应,家族这一社会制度,尤其是这一制度特定的———所谓‘家族制度’的权威主义家父长制———行动模式对于政治权力至关重要。”
“家”是天皇专制国家制度的基础,家族制度自然成为自我认同反思的起点。
1871 年,明治政府颁布了户籍法 ,翌年又实施了日本第一部全国统一样式的壬申户籍。与幕藩时期以村为单位的“村请制”不同,户籍法确立了“家=户”的体制,明确了“家”的范围、户主的控制权与家族成员的序列关系,“家” 走向均质化与标准化,变成国家统治体制的基本单位。1889 年,《明治宪法》的颁布标志着近代天皇制的确立。天皇的权威借助模拟直系家族制的“家”的制度进入国民意识,国家表述为一个大家族,天皇是日本国民的家长,彼此之间构成模拟的亲子关系:“国君与臣民之关系,犹如父母与子孙,即一国为一家之扩大,一国之君主指挥命令臣民, 与一家之父母以慈心吩咐子孙无异。”
从中可见以“家”为基础的国家体制即家族国家观的雏形。接着,1898 年 7 月 16 日明治民法的颁布与实施最终确立了日本近代家族制度。家父长制与家督继承制作为法律介入国民生活,前者以“户主”的身份对家族成员拥有绝对的权威包括“居所指定权”与“婚姻同意权”等,后者承继祖先崇拜观念并强调长子本位、男子本位的原则。通过《教学大旨》、《幼学纲要》、《教育敕语》 与修身教科书的教化,以忠孝一致、忠君爱国为核心的家族国家观从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全面发展。总而言之,家族国家观是明治政府制造的近代国民国家的意识形态,以家父长制的“家”的原理为基础,把国家视为“家”的扩展,把天皇与臣民比拟为父子血缘关系、宗家与分家的关系,把祖先崇拜的“孝”作为尊崇天皇的“忠 ”的思想基础 ,强调家国一致与忠孝一致 ,维护强化国家权力的统治。
如上所述,明治政府一心构建的“家”是近代国民国家统制国民的意识形态,带有浓厚的封建儒教道德色彩,压制着追求自由民主的自我。因此,个体与“家”的关系自然成为明治文学思考的基点之一,反抗专制的“旧家”与追求理想的“新家”反映了个体的现代认同思想。
三、《从那以后》:“弑父”的物语
有关《从那以后》的主题,传统评论归结为“自然的爱”。实际上,按照叙事理论,代助回归“自然”的冲动是一种“欲望”,具有“主题赋值”功能,从中衍生故事情节。《从那以后》采用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分别对应小说第一章的两封书信:第一封信来自好友平冈,指涉与平冈夫妇的关系;第二封信出自父亲长井得,反映与家族的关系。自第八章以后,两条线索发展为主人公与三千代、 佐川姑娘的纠葛。故事的高潮部分是第十四章,代助经过激烈的思想冲突决心向三千代告白而拒绝佐川姑娘。我们知道,三千代是昔日的恋人,而佐川姑娘是父亲一手安排的政略结婚对象,前者基于个人意志,后者属于“家”的意志。换言之,“自然的爱”是一个家族寓言,即执着于自由恋爱的“子”反抗“父”的专制。
与《三四郎》的青年主人公相比,《从那以后》的代助“超越了旧时代的日本”,带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与批判精神。他十分厌恶父辈盲目强调的忠君报国与武士勇气, 觉得只是漠视个体生命的封建道德,反而意识到牙齿、皮肤、头发等肉体的意义:“健康对于他来说,比别人具有更高的价值。”他批判明治的黑暗现实:“不幸的是,精神的困惫与身体的衰弱相伴而至,甚至道德颓废也接踵而来。整个日本看不到一丝光明。”同时,洞察父亲的虚伪道德:“与其煞费苦心地把黄铜装扮成黄金,倒不如老老实实承认本来就是黄铜”,“宁愿固守自我”。然而,代助的自我矛盾也十分清楚,既蔑视“父”的伦理又依赖家族经济维持“高等游民”的生活,沉浸于精神贵族的自由幻象中。事实上,代助大学毕业之后自立门户是父亲“打从儿子一生下来就制定好的整个程序的一部分而已”。根据《明治民法》第 732 条:“户主的亲属在其家者及其配偶,谓之家族。”需要注意的是,“在其家者”指的是观念性的户籍而不是居住地。换言之,代助作为家族成员并没有转籍的权力,始终没有摆脱“父”的控制,而“父亲总把代助当作自己太阳系里的一颗行星,坚信自己有权利永远控制着他的轨道”。在“家”的结构中,个体只是实现家族延续的工具:长子继承家督,次子只是长子的候补。但是,代助对于长井家的利用价值越来越低,因为哥哥诚吾早已继承家族事业, 侄子诚太郎也逐渐长大。随着情节的发展,代助的自由幻象走向破灭:一是“借钱事件”使代助意识到缺乏经济基础的生存破绽,身体的异化感觉暗示他的精神危机;二是“日糖事件”导致家族事业陷入危机,长井得利用“婚姻指定权” 安排相亲并威逼代助接受政略结婚。在“家”的结构中 ,“父 ”的伦理等同于 “家 ”的伦理 ,隐居的长井得在家族中仍然拥有绝对的权限。第三章集中聚焦了 “父” 的伦理,“父子骨肉”、“天生的情分”和“骨肉恩爱”等强调直系血缘关系,带有“旧家”的伦理特征。同时,养育之恩合理化了“父”的专制,反映了“孝”的意识形态:父母之于子的恩情在于使之降生于世,而父母之“恩”往往要求子之“孝”的履行。作为近乎宗教戒律的伦理,孝道成为家长权的基础,家族制度下的孝道几乎等同于专制主义下的臣道。在故事中,代助回归“自然”的最大阻碍就是父亲长井得,突显“旧家”忠孝一致的意识形态对于个体的压抑。
面对同一性危机,代助决心回归“自然”,向三千代进行爱的告白。在此,“自然的爱”包含着明治知识分子追求西式“新家”的理想,即基于自由恋爱、以夫妇为核心的平等家族模式。最终,代助拒绝政略结婚,否定了“旧家”的封建伦理,彻底摆脱“父”的束缚 ,完成了 “弑父 ”的象征仪式 。从祖先到子孙的纵向延续是家族制度存在的根本,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与祖先崇拜思想决定了家族世系的延续成为“家”的第一要义。“家”的利益凌驾于全体家族成员,权威集中于家父长身上,以父子为核心的“竖的伦理”起到支配性作用,成为家族压抑自我意识的起源。因此,在“家国同构”的语境中,作为“家父长=户主”,“父” 自然是明治个体反抗的首要目标,《从那以后》的父子冲突反映了子一辈反抗“父”的专制,现代性主题探讨的是专制的“竖的伦理”。
四、《行人》:“横的伦理”的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从那以后》 除了批判专制的“竖的伦理”,也提示自我意识伴随的利己主义的局限性,“自然的爱”不可避免地伤害了平冈,代助濒临失常的精神状态预示自我的挫折。 于是,“新家”的合法性危机成为《门》的主题,宗助夫妇背负着黑暗的“过去”,“理想的爱”伤害了阿米原来的丈夫安井。 自由恋爱反而暴露了现代认同日益走向唯我论、自我中心主义的困境,《到了春分时节》所描写的“懦弱的男性与无畏的女性”批判了囿于理性思辨的封闭自我,对自我意识过剩的批判与反思延续到《行人》的作品主题。
与《从那以后》一样,《行人》的故事也发生于传统大家族, 讲述了长野一郎与阿直的夫妇冲突,与自我认同息息相关的恋爱不再是单一自我的被动能指, 两性关系还原为两个不同自我的复杂纠葛,褪去“自然的爱”与“理想的爱”的神圣光环。在第一章中,“通过二郎的见闻,《行人》一篇的主题得到了提示”,也就是两性关系。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二郎的行动陆续引出若干男女关系:冈田与阿兼、佐野与阿贞、薄情的丈夫与“那个姑娘”,特别是佐野与阿贞的相亲结婚贯穿故事的大部分,呈现出传统相亲制度的细节,勾勒出夫妇问题的时代语境。有关爱情,一郎有着近乎偏执的理想:“无论如何,我都想要抓住女性的灵魂、心灵,也就是精神。”在此,“灵魂”、“心灵 ”与 “精神 ”都指向个体的自我意识 ,反映了自由恋爱的现代认同思想。可悲的是,与冈田夫妇、佐野夫妇一样,一郎夫妇也是传统相亲制度的产物,只是家父长一手操办的“家”的程序,原本就不存在什么自由恋爱或精神交流。 换言之,一郎与阿直唯有交流才可能产生“理想的爱”。然而,与精神贵族代助一样,一郎又耽于抽象思辨:“我一直想把嘴上说的事情付诸实践,从早到晚都考虑一定要付诸实践……但是,怎样才能从思考的自我变成实践的自我呢?请告诉我!总之,我是一个翻开地图调查地理的人。” 一郎的困境正是自笛卡尔以来唯理性主义导致的弊端,个体囿于自我思辨而疏离现实生活导致一种自我意识过剩。故而,一郎的猜疑与《过了春分时节》的须永如出一辙,他怀疑妻子爱上二郎, 甚至迫使二郎引诱阿直以验证她的贞洁。结果,夫妇隔阂由于二郎的介入进一步恶化,即使如此,一郎转而求助的竟然是心灵感应的研究。除了自我意识过剩,“家”的压抑机制也通过《行人》获得深刻的反思。实际上,《行人》的一郎是《从那以后》的代助的反措定,反思的问题是个体处于“家”的顶端将如何确立自我同一性。在《行人》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长子身份赋予一郎在“家”的结构中处于特权位置。按照明治民法的规定,长子是继承家督实现家族延续的第一选择,所以“父亲思想古板,总想赋予长子至高的权力”,一郎自然拥有仅次于父亲的权威,这一点也体现于一郎使用简体而二郎使用敬体的话语差异。随着父亲的隐居,一郎继承了户主的权限与地位处于家父长的位置,“竖的伦理” 自然支配了他与家族成员包括妻子的关系。
另一方面,“日本家族制度本身决定了妇女一生‘三界无家’的命运。所谓‘三界无家’,即女人降生人世后,由父母抚养,其家是父母的;长大成人出嫁后,其家是丈夫的;丈夫死后,家是儿子的。因此,女人一生的宗旨只有两个字:服从。”
阿直对此也有明确的自觉意识:“像我这样恰似父母种植的盆栽,栽种了就再也无法动弹,除非有人帮忙挪一下。只是一直静止不动,静止不动直到枯死,别无选择。”在长野家庭中, 阿直非同寻常的隐忍与沉默正是对“竖的伦理”的消极反抗。简言之,在“家”的结构中,户主与家族成员之间专制的“竖的伦理”压抑了夫妇之间平等的“横的伦理”,而一郎耽于自我思辨也是夫妇悲剧的根源之一。
明治以来,人们严厉批判传统“旧家”的专制伦理,赞颂自由恋爱,倾心于以平等夫妇关系为核心的“新家”。然而,两性关系借助“自由恋爱”、“新家”等文化符码反而没有得到彻底的反思,“自然的爱”、“理想的爱”淡化了代助、宗助与三千代、阿米的自我差异, 女性沦为自我认同空洞的理想能指。
由此可知,《行人》反思的原点就是《从那以后》,批判了渐行渐远的自我意识过剩问题, 深入解剖了“旧家”的话语机制对于“新家”的压抑,一郎夫妇的问题反映了“竖的伦理”对于“横的伦理”的压抑。“家”的制度是个体不幸的根源,一郎最终也醒悟地讲道:“不管嫁到什么地方,女性都会由于丈夫而误入邪路。我早已把妻子推向歧途,又怎么向对方索要幸福。女性一旦出嫁就失去了纯真,幸福也就不可能从她们身上寻得。”
五、现代认同与“家”
现代认同注重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价值层面,包括价值原则、道德信仰、政治制度、时代精神等,其核心是主体性问题即自我同一性。同时,有什么样的共同体构造模式就有什么样的个体自我认同方式。日本属于家国同构的国家,“家”是政治秩序的基础, 自然也是重建自我认同的最初场域。
《从那以后》与《行人》的意义源自对于这一时代机制的透彻理解与深入反思。《从那以后》的父子冲突关乎“竖的伦理”,批判了家父长的专制,《行人》的夫妇隔阂则反思了唯理性主义的自我弊端,也揭示了“竖的伦理”对“横的伦理”的压抑。前者的焦点在于个体反抗专制体制的自我意识,后者则把笔触集中在专制体制中不同自我的复杂关系,这是因为“自我的整一性必须经由对对立之物的扬弃而完成。对立之物,即差异、他者, 是自我意识的完成所不可缺少的。”
可以说,《行人》是对《从那以后》的进一步反思,一郎的自我意识过剩可以追溯到精神贵族代助,暴露了蒙上唯我论色彩的自我:“集中追求自我内部———个人的感觉、感情、情绪上的自由,以及在空想中的自我的充实。”代助借助文明批判等宏大话语遮蔽了自我中心主义的破绽,“自然的爱”也忽视了两性之间的自我差异,《行人》把一郎置于家父长的位置并突出了夫妇冲突,无疑是《从那以后》的反措定,从而深化了现代认同的主题。
参考文献:
[1]三浦雅士. 恋愛と家父長制———《行人》ノート[M]//小森陽一,石原千秋.漱石研究:第十五号.東京:翰林書房,2002:40.
[2]川島武宜. 作为意识形态的家族制度[M].東京:岩波書店,1957:6.
[3]井上哲次郎. 敕语衍义:卷上[M].東京:敬業社,1891:10-11.
[4]川島武宜. イデァ№ギーとしての《孝》[M]//イデァ№ギーとしての家族制度.東京:岩波書店,1957:90.
[5]鳥居邦朗.行人[M].浅田隆他. 漱石作品論集成:第九巻.東京:桜楓社,1991:2.
[6]王卓. 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83.
[7]王晓路,等. 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22.
[8]叶渭渠,唐月梅. 日本文学史近代卷、现代卷[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