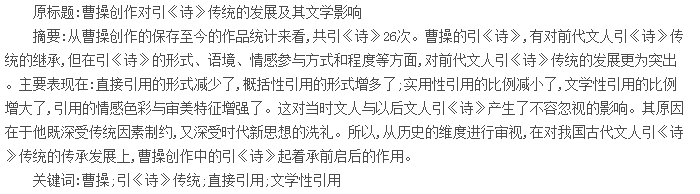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第二编中指出:“代表建安文学的最大作者是曹操和曹植,大抵文学史上每当创作旺盛的时期,常常同时出现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旧传统的结束者,一个是新作风的倡导者。曹操和曹植正是这样的两个人物。”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称曹操“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
在此他们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对曹操的地位,分别从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给予了概括。但学界却很少从文人引用传统的角度对此予以具体分析研究。那么曹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的创作对中国文学传统继承了什么?发展了什么?是如何继承与发展的?产生了怎样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值得我们去开掘的空间。本文从曹操的作品入手,仅就其创作中对引《诗》传统的发展及其文学影响进行专题探讨。
一
从曹操创作的保存至今的作品统计来看,共引《诗》26次,其中《小雅》16次,《大雅》5次,《国风》5次。我国古代文人引《诗》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如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左传》中记载的在政治、外交场合引《诗》、赋《诗》和《论语》中的引《诗》的情况。
这些引《诗》正如有学者已指出的那样:“检视春秋人物对《诗》文本的引用,则可以下一确切的断语:绝大部分引用都是‘权威引证':诉诸一个权威文本加强自己论说的正当性。……《左传》中出现最多的对诗的权威引证是正面陈述自己论说的情形。”
之后战国时期的《孟子》《荀子》等子书与其他文学作品,汉代文人史书、子书与文学作品,也有很多引《诗》的例子。这些引《诗》或直接引用原文,或引用篇名,或引用某一词语意象,或概括引用某些内容,大多借以正面陈述自己的论说,体现出明确的实用目的,较少文学性引用。但到了建安时代,这种情况发生了重要改变。作为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与领导者的曹操功不可没。从曹操创作引《诗》的情况看,也有直接引用原句、篇目、词语意象、概括其中的句子入诗入文的例证;有些引用也是借所引对象权威性来增强自己观点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但总体而言,曹操创作中的引《诗》,在对前代文人引《诗》传统继承基础上的发展更突出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诗》原文直接引用的形式减少了,概括性引用的形式增多了。曹操之前的文人引《诗》,以引原文为主,一般比较具体繁琐,较少概括性引用。具体而言有以下体现:
第一,多直接引用原句,或引用其中的几句,或引用其中的一句,或在原句的基础上稍做变化。如《左传·昭公十六年》载:“二月丙申,齐师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会齐侯,盟于蒲隧,赂以甲父之鼎。叔孙昭子曰:‘诸侯之无伯,害哉!齐君之无道也,兴师而伐远方,会之,有成而还,莫之亢也。无伯也夫!《诗》曰,“宗周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谓乎!'”
叔孙昭子就直接引用了《诗经·小雅·雨无正》中的四句诗句;韦玄成《戒子孙诗》的“明明天子”,则直接引用了《大雅·江汉》中的成句;梁鸿《思友诗》的“鸟嘤嘤兮友之期”,引用《小雅·伐木》中的原句而稍做变化。以上都是引用《诗》中的原句。
第二,摘用《诗经》中的某一词语,并加上“诗人”的字样。如宋玉《九辩》中“窍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素餐”出自于《诗·魏风·伐檀》;秦嘉《赠妇诗》其三中“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瑶琼”,“木瓜”“瑶琼”出自于《诗·卫风·木瓜》,都加有“诗人”的字样。
第三,直接用“《诗》曰”或“《诗》云”点出所引诗句。如《国语·周语中》云:“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颈。”其郤至之谓乎!……《诗》曰:“恺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礼,敌必三让,是则圣人知民之不可加也。……'”周大夫单襄公在借《大雅·旱麓》中的诗句对郤至进行讽刺时,直接用“《诗》曰”予以标出。再如《列女传·贞顺》颂赞息君夫人云:“夫义动君子,利动小人,息君夫人不为利动矣。《诗》云:‘德音莫违,及尔同死。'此之谓也。”,以“《诗》云”直接点出《邶风·谷风》中的诗句。这在先秦两汉文人的史书和子书之中比较普遍。
第四,直接引用具体篇名。如班固《咏史》云:“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
其中《鸡鸣》《晨风》皆为诗经国风中的篇目,被作者直接引用。
第五,直接引用《诗经》中的词语意象。如司马相如《琴歌》:“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其中“鸳鸯”来自于《诗·小雅·鸳鸯》中的“鸳鸯于飞”,“颉颃”来自于《诗·邶风·燕燕》中的“颉之颃之”。这是引用《诗》中的词语意象。
这些引《诗》一般直接明了,概括性不强,容易辨出,并且在曹操之前文人的作品中比较普遍。当然曹操之前文人引《诗》也出现了概括性引用,如张衡《定情赋》的“大火流兮草虫鸣”,是从《幽风·七月》中的“七月流火”和《召南·草虫》中的“喓喓草虫”概括而来。但总体来说,这种概括性引用较少,主要以直接引用原文为主。
曹操创作中的引《诗》,也有引用原文概括性不强的,但这种情况不占主导,占主导地位的是概括性引用。曹操创作中共引《诗》26次,对原文加以直接引用的8次,概括性引用18次。如《谢袭费亭侯表》中的“圣恩明发,远念桑梓”,则是概括了《诗·小雅·小宛》中的“明发不寐,有怀二人和《诗·小雅·小弁》中的“维桑与梓,必恭敬止”的句意;《善哉行三首》其一“智哉山甫,相彼宣王”,引用《诗·大雅·蒸民》一诗的主旨等,都是对《诗》的概括性引用。这说明文人引《诗》传统发展到建安时代的曹操,确实发生了由以前的以直接引用为主、概括性引用为辅,到以概括性为主、直接引用为辅的变化。
其二,与先秦两汉文人史、子着作中引《诗》的时间场景和语境不同。先秦文人史、子着作中的引《诗》多在政治外交与教育、说理等场合。正如孔子所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汉书·艺文志》也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突出的是《诗》的政治外交与伦理教化功能。如诸子散文中的引《诗》、赋《诗》,为了明理的需要,就多强调《诗》的说理教化和政治功能,不太考虑《诗》文本的本义,更较少关注《诗》本身的文学情感与审美价值。如《论语·学而》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在此我们通过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的对话语境,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对《诗》的伦理学阐释。《孟子》一书引《诗》35次,也多出现于政治外交和教育、说理场合,往往设置一个对话的场景,在与人对话过程中,为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个人抱负,把所引之《诗》作为观点的依据和载体,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并多以“《诗》云”“《诗》曰”予以标明。如《孟子·公孙丑上》云:“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孟子之所以引《诗·大雅·文王有声》的诗句,主要是通过周朝“以德服人”而得天下为其“仁政”思想作张本。《荀子》也出现了大量引《诗》的情况,共83次,尽管不像孔子、孟子引《诗》那样多出现在对话场合,但一般先讲故事或道理,然后引《诗》予以印证和说明,并常冠以“《诗》云”,结束语用“此之谓也”予以标示,即使不予特意标示,也予以进一步的解释,为读者准确理解所引《诗》的意义设置一个讲故事或说理的情节语境。
对此学界对荀子引《诗》的相关论着已有论述。《墨子》《韩非子》等非儒家的着作也出现了多少不等的引《诗》例证,其引《诗》的场合与语境大体与以上所举儒家着作引《诗》相仿,在此不再一一分析。
两汉文人史传中的引《诗》,也多是借《诗》在政治伦理层面的权威性来增强作品的感染力与说服力。如《古列女传》卷四《贞顺》:“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虏其君,使守门,将妻其夫人而纳之于宫。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见息君,谓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无须臾而忘君也,终不以身更贰醮。生离于地上,岂如死归于地下哉?'乃作诗曰:‘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听,遂自杀。息君亦自杀,同日俱死。”
故事中的引《诗》,出自于《王风·大车》。《毛诗序》认为:“《大车》,刺周大夫也。礼义陵迟,男女淫奔,故陈古以刺今大夫不能听男女之讼焉。” 但刘向却借引《诗》颂扬息夫人的贞节。其引《诗》的意义也是借助于特定的时间场景与情节语境来展现的。
曹操创作中引《诗》不同,其意义不是靠特定的时间场景与情节语境来昭示的。尽管也有个别创作的引《诗》,为了让读者理解所引《诗》的意义,以“《诗》称”“《诗》曰”予以标示,设置一个提示性的语境。如《以徐奕为中尉令》中的“《诗》称‘邦之司直'”,《求言令》“《诗》称‘听用我谋,庶无大悔”,就是如此,但这种情况较少。曹操创作中的引《诗》,在大多情况下主要是让读者通过文中自我书写的非情节语境来把握和理解作者所引《诗》的目的及意义。如《下州郡》“今吾亦冀众人仰高山,慕景行也”,化用《诗·小雅·车辖》中的语意,诗中的本义是指对有德者要像高山一样仰望,对高尚的行为就要效法,曹操则借以称赞杜畿的不阿权贵的精神。再如《苦寒行》“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诗·豳风》中《东山》,是相传周公东征,战士离乡三年,在归来途中,战士思念家乡写的一首诗;而《苦寒行》是曹操在建安十一年北上征伐高干时所作,在此作者主要借《东山》表达自己想归乡而未能的哀伤。在以上曹操创作引《诗》的例证中,既没设定特定的时间场景,又没创造含有人物对话或故事的情节语境,完全是自我的主观书写。所以,曹操创作所引《诗》的意义是依靠自我书写的非情节语境来彰显的。
可见,先秦两汉文人史、子着作中的引《诗》多有特定的时间场景,曹操创作中引《诗》一般则无;先秦两汉文人史、子着作中的引《诗》,为了彰显《诗》的意义,往往创造一种含有人物对话或故事或说理的情节语境,曹操创作中引《诗》呈现给读者的一般则是自我主观书写的非情节语境,较少借助于人物对话、故事、说理等情节来展现所引《诗》的意义。先秦两汉文人史、子着作中的引《诗》的时间场景、情节语境,是让接受者客观准确地理解引《诗》者目的及意义的重要条件,尽可能地避免主观情感的参与;而曹操创作中引《诗》的自我书写非情节语境,让读者通过自己的主观情感和审美参与来把握作者引《诗》的目的及意义。
其三,与先秦两汉文人辞赋、诗歌中引《诗》的语境也有区别。
先秦两汉文人辞赋、诗歌中引《诗》时所营造的语境与所引《诗》的意义多是一致的。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臣观其丽者,因称《诗》曰‘遵大路兮揽子祛'”,直用《诗·郑风·遵大路》中的诗句,汉代秦嘉《赠妇三首》其一中的“忧来如循环,匪席不可卷”,引用《诗经·邶风·柏舟》中的句意。为了让读者不产生歧义,作者分别特意营造了“观其丽者,因称诗曰”和“忧来如循环”的语境。这些例子中作者所引用的意义与被引用对象的原本意义是一样的,读者之所以很容易理解引《诗》的意义,其重要原因,就是引《诗》者有意无意为读者营造了一个准确把握所引对象原本意义的语境。
曹操创作中的引《诗》,多数情况下没有为读者理解所引《诗》的意义故意营造提示性的语境。其引《诗》的意义是否与《诗》的本意一致,一般没有明确的指向性。他所引用的《诗》的意义的彰显,不是靠设置的具有暗示性或启示性的语境来完成的,而是让读者通过自己的主观情感和审美参与来把握的。他所引用的《诗》的意义可能与《诗》的本来意义一致,也可能与《诗》的本来意义没有明显的外在关联。这在下文曹操引《诗》的情感参与方式与程度部分有具体分析,此不赘述。
其四,与前人引《诗》的情感参与方式和程度不同。曹操创作中的引《诗》多是主观的、情感的、审美的,以主观审美情感参与方式为主,常常蕴含着他对所引对象的新的理解。
前人引《诗》多以政治伦理为目的,这就决定了其情感参与方式多是政治的、伦理的,说教比较明显。当代学者林岗指出:“《诗》在春秋人物生活中的运用是多方面的。……《诗》是他们言行规范的神圣文本,它在所有文本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诗》承载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昭示了必须遵行的道德原则;它汇集了先祖的聪明智慧,启发了历代不易的真理。……更重要的是以其不可动摇的权威教诲,为这个社会提供言行的道德准则。春秋人物对《诗》文本的引用,正是反映了这样一个生活事实。”
尽管先秦时期文人引《诗》也出现了主观审美情感参与的情况,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赠我如此兮不如无生”,直用《诗·小雅·苕之华》中的诗句,借《诗》中主人公在生不逢时、处世艰难境况下痛不欲生的自伤之情,来表达男女相恋、赠诗传情的激动情感。但这类引用在先秦时期并不多见。
两汉时期,因受经学的影响与《诗》本身的经学化,文人作品中对《诗经》的引用具有浓郁的经学色彩。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游于六艺之囿,骛乎仁义之途,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驺虞》,弋玄鹤,建干戚,……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文中所引《诗》篇目是与五经并列的,诗义也是经学意义上的。直到东汉以后,像宋玉那样对《诗》句意的审美引用又出现在文人作品之中。如班彪的《北征赋》:“日晻晻其将暮兮,睹牛羊之下来。寤旷怨之伤情兮,哀诗人之叹时”,借用《诗·王风·君子于役》中的情景以抒情。不过这些对《诗》句意的审美引用,与对《诗》的经学引用相比,还是处于弱势。
东汉末年《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在引《诗》时改变了以前文人引《诗》的经学引用风尚,代之于抒情性与审美性的引用。《古诗十九首》中引《诗》多达36次,或是用于抒情的,或是为抒情服务的。如《行行重行行》中的“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引用《诗·秦风·蒹葭》中的句意,描写女主人公与心上人生活中相距遥远且充满险阻的现实,来抒发相思而又无法会面的惆怅之情;《明月皎夜光》中的“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概括《诗·小雅·大东》中的语句,来说明昔日的朋友有名而无实,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世态炎凉,抒发了作者对人情浇薄的痛心。这种引用相对于以前来说,是一大进步,使引用日趋文学化与审美化,突出了引用的文学性与审美性。但不可否认,这种引用还有需要完善与开拓的地方。其突出表现就是多为对被引用对象意义的直接和正面运用,较少对被引用对象意义的创造性引用或延伸性引用。即在引用时,缺少对被引用对象意义的新的理解。
在曹操创作中的26处引《诗》中,文学性和审美性引用有9处,这和前代文人相比,是一个大的发展。曹操引《诗》的文学性与审美性引用中,也有对被引用对象意义的直接和正面运用,这是对前人文学性和审美性引《诗》传统的继承。但需要我们关注的是,曹操引《诗》出现了对被引用对象意义的创造性引用或延伸性引用,赋予了被引用对象意义的新的理解。这是对前人文学性和审美性引《诗》传统的发展。这种引用多是建立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基础之上,多以抒发自己的主观情感为目的,情感的审美特征比较突出,是自己主观情感的主动参与,不是以说教者的口吻来进行政治训诫或伦理说教,而是把《诗》中的情感与自己的情感合而为一,达到了水乳交融。
如他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和“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直接引用《诗·郑风·子衿》和《诗·小雅·鹿鸣》的成句,把自己对贤才的思念说成犹如青年男女热恋时的思念之情,把自己渴望礼遇贤才说成犹如鹿得苹呼同伴相食的诚恳之情,来抒发自己渴求贤才、以礼待之的心情,显得真挚、热烈、自然。因为曹操在南征北战、戎马倥偬的生涯中,深深地感到贤能之士对其完成统一大业的重要,思贤若渴之情油然而生,而且这种情感非常强烈、深切,其程度不借助热恋中青年男女的刻骨相思与鹿得苹呼同伴相食的诚恳则不足以表达。所以,就自然地联想到了《子衿》和《鹿鸣》中的成辞。这种表达是作者在创作活动中通过联想,以自己的思贤之情与《子衿》和《鹿鸣》文本中的男女相思之情、鹿得苹呼同伴相食的诚恳之情相比附的结果。正如钱大昕所说:“或又疑《生年不满百》一篇櫽括古乐府而成之,非汉人所作,是犹读魏武《短歌行》而疑《鹿鸣》之出于是也,岂其然哉?”这虽然是对《生年不满百》引用古乐府成辞而言,但也说明了魏武《短歌行》引用《鹿鸣》成辞已达到了浑融自然的境界。再如曹操的《苦寒行》中的“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作者以周公自喻,借用《诗·豳风·东山》这一写远征军人还乡之作来比照自己当前行役的苦况。这些表达主要是通过作者在创作活动中情感体验的相互感发来完成的。质言之,创作主体首先因现实的情感体验联想到所熟悉的文学作品的情感,通过对以前阅读文学作品时的情感体验深化现实的情感体验,同时现实的情感体验又会促进对文学作品即文本中所表达的情感体验,这种双向互相深化的情感体验统一交汇于创作活动之中,其结果就是对《诗》的创造性引用与其新意义的诞生。就曹操的《短歌行》来讲,他通过在创作过程中对《诗》作品的引用,深化了对《诗》作品文本表达情感的效果的理解,同时又能昭示作者对该诗所表达的男女之情的深切体验,进而结合自己的创作活动与体验,对文学表情达意所达到的程度也有了切实而深切的体会。所以,与先秦两汉文人引《诗》的情感参与方式与程度不同,曹操引《诗》多是主观的、情感的、审美的,以主观审美情感参与方式为主,蕴含着他对被引用对象的同情之理解。
二
曹操创作中的引《诗》,在对前代文人引《诗》传统继承发展的同时,对当时文人与以后文人创作中的引《诗》风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尽管曹操创作中引《诗》仅26处,但其对建安其他文人引《诗》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建安其他文人创作中的引《诗》,虽然有其个人修养与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原因,但由于曹操当时既是政治层面的领导者,又是文学层面的领导者,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创作对其他文人创作的指导与引领作用。据我们统计,曹丕的创作引《诗》60余次,曹植的创作引《诗》110余次,徐干的创作引《诗》约27次,阮瑀的创作引《诗》约9次,应玚的创作引《诗》约13次,刘桢的创作引《诗》约14次,陈琳的创作引《诗》约34次,王粲的创作引《诗》70余次。
曹丕、曹植与其他文人创作中的引《诗》和曹操一样,以概括性引用为主,并且较少政治训诫和伦理说教,重视引用的抒情性和审美性。如曹丕《杂诗二首》其一:“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天汉回西流,三五正纵横。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分别引用《诗·小雅·四月》中的“冬日烈烈”,《诗·召南·小星》中的“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诗·召南·草虫》中的“喓喓草虫,趯趯阜螽”等词语,来渲染游子客外凄清孤独的气氛,使游子思归之意寄寓其中。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评云:“意取功名善全之士,比意新警,刻意作高古之调,杂引前人,并以抒其议论,故事事无不生动,此可以得使事之法矣。此等处极摹乃父。”
指出了他和曹操引《诗》的相似之处,也可看出所受曹操的影响。如徐干的《情诗》“踟蹰云屋下,啸歌倚华楹”,用《诗·邶风·静女》中的“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与《诗·小雅·白华》中的“啸歌伤怀,念彼硕人”,展示主人公因相思之情而引发的百无聊赖的情状。阮瑀的《琴歌》“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用《诗·卫风·伯兮》中的“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抒写知己之可贵。应玚的《报赵淑丽》“有鸟孤栖,哀鸣北林”,用《诗·秦风·晨风》中的“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以自况,突出了心理的孤独与忧郁。像这种引《诗》的方法在建安文人作品中运用比较普遍,此不一一列举。
在此我们重点强调的是,曹操作品中那种情感参与的引《诗》方法,即在引用时注入了自己对被引用对象意义的新的理解,赋予其新的内涵的方法,在曹丕、曹植兄弟与建安其他文人的作品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如曹植《朔风》中的“昔我同袍,今永乖别”,“同袍”出自于《诗·秦风·无衣》。其本意是旧时在同一军队工作的人之间的互称,在《诗》中是指挚友,而在曹植的《朔风》中,则借“同袍”表达兄弟之间深挚的手足之情,深化和发展了“同袍”的原有意义。《柳颂序》中的“予以闲暇,驾言出游”,引用《诗·卫风·竹竿》的原句。《诗》中的“驾言出游”目的是发泄作者内心无限的忧愁,但在曹植的《柳颂序》中,则变成了闲暇时悠然自适的游览,《诗》中的心理忧愁已荡然无存。如徐干的《室思》其三“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辞”,“洋洋”来自于《诗·陈风·衡门》。《诗》中的“洋洋”是指水的流动之貌,但徐干却用以形容云的流动。再如应玚的《公宴诗》“穆穆众君子,好合同欢康”,用《诗·大雅·文王》中与《诗·小雅·常棣》中语句,以文王之德喻朋友之德,以妻子之情喻朋友之情。又如“凤栖梧桐”出自于《诗·大雅·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其本意主言凤凰非梧桐不栖之高洁品格,但曹丕《猛虎行》中的“梧桐攀凤翼,云雨散洪池”之语,则借凤凰非梧桐不栖喻贤才非明君不事,故后世以“凤凰栖梧”喻贤才择明主而事。王粲的《赠士孙文始》“和通篪埙,比德车辅”,用《诗·小雅·何人斯》中的“伯士吹埙,仲士吹篪”,以埙篪的相互应和喻朋友之间感情的融洽和谐。其他如陈琳等人的作品中也有不少这种创造性的引用。这些引用使被引用的对象的意义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包含了引用者新的理解,情感内容更为丰富。
建安以后的文人继承了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等人的引《诗》传统。如正始时期阮籍《咏怀诗》其二:“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就是引用《诗经·卫风·伯兮》中的“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的句意,作者在此托以为喻,抒发自己知己难寻的感伤情怀;其《咏怀诗》十二:“夭夭桃李花,灼灼有光辉。悦怿若九春,折磬似秋霜”,是对《诗·周南·桃夭》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和《诗·邶风·静女》中的“说怿女美”语意的概括。这些都是对《诗》的情感审美引用的具体体现,表现出“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特征。西晋以后用典范围进一步扩大,《诗》照样是文人创作引用的对象。如傅咸《青蝇赋》:“幸从容以闲居,且游心于典经。览诗人之有造,刺青绳之营营”,引用《诗·小雅·青蝇》的诗意;他的《燕赋》:“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何诗人之是兴?信进止之有序”,引用《诗·邶风·燕燕》中的成句,都拓展了原诗的本来意义,也是对《诗》的情感性和审美性引用。到了南朝,用典成为文人创作的习尚,《诗》更是文人创作中所用典故的来源。如谢庄《月赋》:“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沉吟齐章,殷勤陈篇。”
引用《诗·齐风·东方之日》和《诗·陈风·月出》中的语意,赋中假托陈思王曹植于皓月当空之夜,赏月兴怀,命王粲骋藻赋月,“沉吟齐章,殷勤陈篇”,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远较原诗更具有审美韵味。作者托曹植、王粲之口,引《诗》抒情达意,可见深受建安文学的影响。
颜延之在其《庭诰》曾云:“观书贵要,观要贵博,博而知要,万流可一。咏歌之书,取其连类合章,比物集句。采风谣以达民志,《诗》为之祖。”南朝文人引《诗》情况,由此可见一斑。到了唐代的李杜,引《诗》依然是他们用典的重要内容。如李白《宣城送刘副使入秦》中的“君携东山妓,我咏《北门》诗”,《感时留别从兄徐王延年从弟延陵》中的“仙风生指树,大雅歌《螽斯》”,其中《北门》《螽斯》分别是《诗·邶风》和《诗经·周南》中的篇目,其引用的目的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情感。明人宋镰《杜诗举隅序》云:“杜子美诗,实取法《三百篇》,有类《国风》者,有类《雅》《颂》者,虽长篇短韵,变化不齐,体段之分明,脉络之联属,诚有不可紊者。”
?从艺术精神和题材内容上揭示了杜诗对《诗》的取法与借鉴。我们知道,李杜的文学创作深受建安文学的滋养,而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等又是建安文学的代表,所以他的引《诗》也会影响李杜作品中的引《诗》。
从正始的阮籍到盛唐的李杜,文人引《诗》风气不绝如缕。尽管我们不能说这种风气是受曹操创作中引《诗》的直接影响形成的,但其引《诗》对前人的继承发展,可以说为后代文人的引《诗》提供了借鉴。这也是建安文学对其后文学产生影响的表现之一。明代的徐世溥《榆溪诗话》云:“前汉诗不使事,至后汉郦炎《见志诗》,始有‘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及‘抱玉乘龙骥,不逢乐与和;安得孔仲尼,为世陈四科'之句。孔北海‘吕望'、‘管仲'两言耳,曹氏父子益张之。”
如果从古代文人创作中引用古人、古事、成辞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是有道理的。这也可从另一侧面透视出曹操创作中引《诗》的文学价值和意义。
三
曹操创作中的引《诗》之所以能够在继承前代文人引《诗》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他深受传统因素影响,这使其在创作中继承了前人的引《诗》传统;另一方面因其深受时代新思想的洗礼而孕育出的自由独立精神,使他在创作中引《诗》时,表现出自己的创造性和同情之理解。就曹操深受传统因素影响而言,可分为以下五个方面。首先,深受曹操家族中儒学传统的影响。司马彪《续汉书》曰:“腾父节,字元伟,素以仁厚称。 ……腾字季兴,……在省闼三十馀年,历事四帝,未尝有过。好进达贤能,终无所毁伤。”
由此可以看出,曹节、曹腾不仅具有儒家的仁厚之风,能够做到进达贤能,而且能够把此长期作为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的行事准则。这种好儒的家学传统,对曹操必然产生影响,故儒学也成为其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史载:“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张作耀先生在《曹操评传》导言中云:“曹操的诸多言论和行动,都受儒家的思想影响,根基属于儒家思想范畴,崇尚仁义礼让,主张以先王之道办教育,并以儒学的学说勾画自己的理想蓝图。”不仅如此,曹操还把《诗经》作为教育子女的主要内容之一。史云:“任城威王彰,……太祖尝抑之曰:‘汝不念读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课彰读《诗》《书》”。曹丕在《典论·自叙》中也云:“上雅好诗书文籍,……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
《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云:“年十岁馀,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曹操作为其家学传统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对儒家经典的学习与领会,特别是对《诗经》的学习与领会,为其创作中的引《诗》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在曹操生活的时代,尽管儒家思想受到一定冲击,文化思想领域呈现出自由宽松、多元并张的态势,但儒家的统治地位仍未被取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后,屡下诏令,推行儒学。如建安八年,“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者而教学之”;建安十二年北征乌桓,还师途中经过涿郡,派人祭奠儒学大师卢植,以彰其德。
这说明当时的曹操对儒学是热心奉行的,并把其作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之一。所以作为儒学重要经典之一的《诗》,必然成为当时文人重点学习与诵读的对象,曹操也不例外。
其三,对前代文人作品的引用是中国古代文人创作的传统之一。正如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事类篇》所云:“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鵩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
在此刘勰用简括的语言对从先秦的周文王到东汉的崔骃、班固、张衡、蔡邕等文人创作中的引用历史予以了总结,指出了汉末“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的引用风尚。生于汉末的曹操也必然会受这种风尚的影响。
其四,《诗》本身就具有浓郁的抒情性,蕴含丰富的情感内容,尤其是比兴手法的运用,易于使人产生想象与联想,从而彰显出较强的弹性和张力。
所以《诗》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产生以后,就被文人广泛引用,或借诗明理,或借诗言志。建安时期,文人对《诗》的文学性的认识比以前更深入了。杨修在《答临淄侯笺》中云:“损辱嘉命,蔚矣其文,诵读反覆,虽讽《雅》《颂》,不复过此。若仲宣之擅汉表,陈氏之跨冀域,徐刘之显青豫,应生之发魏国,斯皆然矣。……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着一书,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俦,为皆有愆邪。君侯忘圣贤之显迹,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未之思也。”
曹植《前录自序》也说:“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皜皜,与《雅》《颂》争流可也。”这种把《诗》中《风》《雅》《颂》作为衡量文学作品文学价值高低的思想观念,也必然反映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之中。
其五,汉代本经立义书写原则的影响。两汉时代,由于儒学的独尊,《诗》的经的地位的确立,本经立义成为文人的书写原则。刘熙载《艺概·文概》:“秦文雄奇,汉文醇厚。大抵越世高谈,汉不如秦;本经立义,秦不如汉。”皮锡瑞《经学历史》中《经学极盛时代》云:“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一时循吏多能推明经意,移易风化,号为以经术饰吏事。”
这种书写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无疑又加强了先秦文人的引《诗》传统。曹操也不可能彻底抛弃这种传统。曹植《武帝诔》云:“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着雅颂,被之琴瑟。”
所以这也成为曹操引《诗》的传统因素之一。
就曹操所受时代新思想的洗礼而言,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影响曹操思想的儒学,主要是东汉末年的古文经学。东汉末年的古文经学,在保持着儒家原有的以道自任、经世治国精神品格的同时,又表现出鲜明地贵理识、重证据和追求自由、关注个体的特征。一方面体现在当时文人对经学文本的理解上,既充溢着严谨之精神,又显示出不囿于一家的圆通意识和自由倾向,以及建立在自我主观体验基础上的同情之理解。如郑玄之所以兼注群经,就是因为面对当时“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的状况,为使“学者略知所归”,才“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的。其以道自任、经世致用之目的与严谨之精神不言自明。他自己在《六艺论》中亦说:“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
这种注经参照众家之说、择善而从、兼容古今文经之态度,就是其圆通意识的显现;但其“如有不同,即下已意”,则展示出注重自我理解的突出特征。另一方面,体现在当时文人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上,则彰显出不囿于传统儒学的鲜明个性。如郑玄虽以“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为己任,但他在袁绍手下做宾客时,针对诸多豪俊的“竞设异端,百家互起”,却能“依方辩对,咸出问表”,使豪俊们“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与郑玄相比,马融则更具有追求自由的个性。当邓骘召其为舍人时,因“非其好也”,遂不应命。既而饥困,乃悔而叹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资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
并于“绛帐”“女乐”中讲学,表现出旷达任性、贵生求乐的名士风范。可以说这是汉末文人那种追求自由独立、张扬个性人生价值观的典型显现。东汉末年古文经学所展示出来的新的特质,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先秦儒学和汉代神学化儒学继承基础上的超越和发展。曹操恰逢生活在这个时代,所以他也不可能不受这种古文经学精神的影响。这从他非常尊敬郑玄、卢植等古文经学大师就能明白。不仅如此,而且在光和三年六月,汉灵帝诏能通《尚书》《毛诗》《左氏》等古文经学者拜为议郎,曹操因“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
其次,魏武恰好处于思想上由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轨的时代。此时思想文化上的典型表征就是伊始于先秦时期的理性精神经过司马迁、扬雄、张衡、桓谭、王充和仲长统等人的继承与发展,终于冲破了两汉经学的神学迷雾,发出了烛照中古的理性之光,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自由宽松态势。曹操除受儒学影响外,兼受申商与刑名之学,甚至于道家、神仙思想的影响。陈寿云“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傅玄说“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 ,同时他还信方术,这些共同培育了曹操自由通脱的思想。这种自由通脱的思想与东汉末年古文经学表现出的对经学文本理解上注重自我主观情感体验、在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上追求鲜明个性等时代精神一道,为曹操以同情之态度去理解《诗经》文本增加了驱力,也成为他创造性地引《诗》的原因之一。
总之,建安时期的曹操,既深受传统因素影响,又深受时代新思想的洗礼。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促使他在创作中,在继承前代文人创作中引《诗》传统的同时,又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使文人引《诗》的文学与审美特征日益彰显,并对建安其他文人创作中的引《诗》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后代文人的引《诗》提供了借鉴。所以,从历史的维度进行审视,在对我国古代文人引《诗》传统的传承发展上,曹操创作中的引《诗》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其贡献和影响应予以应有的肯定和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