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塞尔·帕尼奥尔和夏沙·吉特里将戏剧与电影融
时间:2015-03-18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本文字数:10516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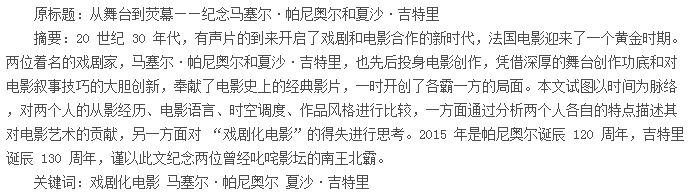
20 世纪 30 年代的法国经济低迷,政局动荡,社会分裂,法国电影也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激荡岁月。早期,面对美国电影的激烈竞争,在一片有声无声孰优孰劣的争论声中,它艰难地承受了从无声片向有声片的过渡。谁知山回路转,中期却迎来了诗意现实主义,书写了法国电影至今未能超越的辉煌一页。
在整个时期,电影和戏剧展开了更为紧密的合作,为电影工业的振兴注入了必要的新能量。更多的戏剧人才参与到电影创作中,只是很多人都落马了,马塞尔·帕尼奥尔( MarcelPagnol,1895 - 1974) 和夏沙·吉特里( SachaGuitry,1885 - 1957) 算是幸存的佼佼者。他们凭借自己的戏剧经验,创作了很多杰出的作品,丰富了电影表现手段,并且开辟了各自的独立电影王国,一时形成了一南一北的霸主地位。
两位导演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共同点,就是他们毕生都高调宣称戏剧艺术优于电影艺术。
然而,两个人都没有成为戏剧史家所钟情的剧作家,基本上都被定义为虽然曾经荣耀一时、但并没有独特建树的作者。相反,两人却是法国电影史上重要的、不可不提的编剧兼导演,一直以来都被人津津乐道。一冷一热,反射的是戏剧和电影的复杂关系。纪念他们,除了纪念他们为电影艺术所做的贡献,还希望借机对电影和戏剧的关系,特别是对 “戏剧化电影”这个词做一些思考。
一、缘自有声
帕尼奥尔和吉特里虽然都是半路出家,但是两个人的从影轨迹却不一样。帕尼奥尔对有声电影可谓一见钟情,而吉特里和电影是欢喜冤家,吵吵闹闹终成佳偶。他们的态度正好代表了那个时代戏剧家介入电影的两种类型。
和很多戏剧家一样,吉特里不承认无声电影具有和戏剧相等的艺术力。1912 年,吉特里写道: “我认为电影的影响是让人叹息的……它试图用剽窃和删减戏剧作品的方式和戏剧展开一场不高尚的竞赛。”
1923 年,他还写过一部独幕剧,嘲弄无声电影,招来诸如马塞尔·莱比尔( Marcel L’Herbier) 这些知名默片导演的不满。“我不能想象这样一种天才的发明竟然服务于这般的愚蠢。”
在他眼里,电影更多是一种科技发明,其主要功能是记录。所以,尽管他对无声电影冷嘲热讽,却早在1915 年就拍摄了纪录片 《我们国家的那些人》( Ceux de chez nous) ,将很多当时着名的法国艺术家收入电影。
至于帕尼奥尔,从 1916 年到 1927 年,年轻的他还只是一名英语教员,怀着对语言、对戏剧的热爱开始从事戏剧创作,很难想象他会对无声电影产生好感。
其实,在有声片到来之前,电影和戏剧的差别是很明显的。电影首先是一种视觉艺术,在默片时代,不论是追求画面性的先锋派,还是努力拓展电影叙事功能的商业导演,对此都有一种共识。正因为电影是特殊的、不可比较的,这门新艺术才可以在总体上与戏剧和平共处。然而,有声电影的到来使得电影和戏剧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了。在实践中,为了尽快适应新市场,会说话的电影更快地向戏剧靠拢,大量的戏剧演员、剧作家开始参与电影创作,很多成功的通俗戏剧被改编成影片,“戏剧化电影”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风尚。
帕尼奥尔就是这支大军中的一员,而且还是旗手。1930 年春,他的剧作 《马里乌斯》( Marius) 还在巴黎戏剧院热演,他的成名作《托巴兹》( Topaze) 还在欧洲各地巡演: 一个朋友推荐他去伦敦看了一部好莱坞有声片《百老汇的旋律》( Broadway Melody) ,帕尼奥尔立即被吸引住了,坚信有声电影将是戏剧艺术的未来。回到巴黎后,他即撰文为电影和戏剧的结合鼓吹呐喊: “有声电影消除了戏剧表现形式中绝大多数的传统限制,尤其是舞台带来的局限性……看看这个令人惊叹的发明会带给我们什么,我们将跨过舞台前的照明灯,围着舞台四下活动,我们可以将剧院的四壁敲碎,可以聚焦布景甚至是演员的某个部分。”
然而,他却意外地遭遇了来自戏剧界和电影界的两面夹击。戏剧界指责他背叛了高雅的戏剧,电影界虽然乐于见到一位成功的戏剧家对电影表示出兴趣,但是他们对有声电影这个新事物充满了疑惑和担忧,而且认为帕尼奥尔完全不懂行。
但是,帕尼奥尔没有舍弃。他带着门外汉独有的热情和创造力开始了自己的电影生涯,而且很快就开花结果。除了最开始的三部影片———1931 年的 《马里乌斯》、1932 年的 《托巴兹》和 《芬妮》 ( Fanny) —他的身份是“原作者”外,他在其他影片中都是编剧兼导演。30 年代可以说是帕尼奥尔创作的黄金时期: 《若夫鲁瓦》 ( Joffroi,1933) 、《安吉尔》( Angèle,1934) 、 《凯撒》 ( César,1934) 、《再生》 ( Regain,1937) 、 《傻冒》 ( LeSchpountz,1937) 、 《面包师的妻子》 ( LaFemme du boulanger,1938) 、《掘井人的女儿》( La Fille du puisatier,1940) 都是法国电影史、甚至世界电影史上优秀的早期有声故事片。
然而,在 1934 年左右默片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之前,关于有声电影的争论一直没有真正平息下来。而且,争论的焦点不再局限于电影和戏剧的特殊性,其意图还在于分出一个伯仲,也就是说戏剧和电影孰优孰劣? 在默片时代,电影艺术家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摆脱电影的机械性,发掘它的梦幻空间。而有声片之初,由戏剧改编的影片一度泛滥、粗制滥造,严重损害了电影的艺术魅力。电影似乎又要重新陷入复制现实、复制戏剧的泥潭。争论双方彼此指责对方对当时法国电影的衰败负有主要责任。导演勒内·克莱尔( René Claire) 即认为,“如果说1933 年电影的凄惨状态不能仅仅归咎于戏剧的影响,这种影响仍然是令人痛心的……戏剧来了,就像是爱管闲事的邻居一样。它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向它年轻的竞争者灌输它陈旧的法则和惯例,以至于电影如今在一种异类规则的束缚下萎靡不振。”
而在敌对的阵营里,吉特里是戏剧界反对有声电影的着名代表。1932 年末、1933 年初,吉特里做了系列讲座,题目赫然就是 “支持戏剧,反对电影”: “我觉得大多数的法国电影平庸得无法想象。”世事难料,到了 1935 年 1 月,吉特里却在一次采访中公开承认: “我喜欢电影。”
促使他转变的主要有三个因素: 首先是他意识到电影的地位日益重要。1935 年,电影诞生 40周年之际,为了表示和电影艺术的和解,法兰西学士院决定将保留剧目中的一部戏剧翻拍成电影,结果吉特里 1914 年的戏剧 《两副餐具》 ( Les Deux couverts) 被选中,吉特里还作为原作者受邀出席了该电影的首映宴会。其次,美国人想将他的着名戏剧 《巴斯德》( Pasteur) 改编成电影,这让他觉得还不如亲手操刀。最后的原因是他新娶了一位年轻的女演员 ( Jacqueline Delubac) ,并在她的影响下决心尝试拍摄电影。于是,1935 年他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 《巴斯德》,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两年之内他拍摄了 10 部影片,其中的好部都被认为是电影史上的杰作。
帕尼奥尔和吉特里最终都投身电影,或许还有一个共同的原因: 两个人都喜欢新事物、新技术,喜欢热闹赶时髦。吉特里很早就参加广播节目,为巴黎电台定期写专栏,还为广告写文章,电影只是他的另一个新玩具。而帕尼奥尔向来喜爱动手制作机械,比如他会拿着新机器在南方的群山里寻找水源,他在后来建立的电影王国里专门设立了实验室,进行电影技术的革新。有一些文人喜欢独处,隐居写作,而这两位则留恋于社交生活,是巴黎各种盛会的座上宾。
至于他们投身电影的时间先后,最明显的原因是他们和戏剧的渊源。1930 年的帕尼奥尔刚刚因为 《托巴兹》和 《马里乌斯》而声名鹊起,但是电影基本中断了他的戏剧创作。
他的舞台生涯很短,一共上演过 9 部戏剧,而且大多数还都拍成了电影,有的戏剧甚至后于同名电影诞生。相反,吉特里的戏龄有 50 年( 还不算他从小就在剧院里长大) ,而且从未中断过。就在 1936 年他从影不久,他就庆祝了自己第 100 部剧作的上演,当时他在戏剧界的外号是 “大师”( Matre) 。他一生主要的戏剧作品就有 100 多部,电影作品有 31 部,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改编自他的戏剧。
二、建功立业
在 30 年代,更多的作家和剧作家涉足电影,但是很多人来了又走了。帕尼奥尔和吉特里之所以留了下来,是因为他们战绩辉煌,是当时 “真正的领主,各自统治着一片独立的领地”,称他们南王北霸毫不过分。
从 1933 年开始,帕尼奥尔就基本建立起了自己的电影王国: 他不仅是编剧、导演,还是制片人、发行商,甚至拥有自己的摄影棚和实验室。为了有一个舆论的阵地,他还于1933 年底到 1934 年 9 月创办了一份电影杂志《影片手册》 ( Les Cahiers du film) 。当时的他是极少有的独立电影人,享有很大的创作自由,甚至有拍完就重拍的奢侈,比如 《梅吕思》 ( Merlusse) 和 《西卡龙》 ( Cigalon) 刚拍完,他就重拍了,因为他不满意前一部的录音,后一部索性把演员角色都给换了。还有《托巴兹》,帕尼奥尔前后拍了三个电影版本。
从影开始,他就反对好莱坞式的行业阶层,为提高作者的地位而奋斗。他曾经想在派拉蒙创建一个文学委员会,以便创立法国本土的制片业,以走出好莱坞的藩篱。这些努力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甚至有电影史学者宣称 “唯一一个在今天能和他媲美的是卓别林,理由是他和帕尼奥尔一样是唯一自由的作者兼制片”。
至于吉特里,他一直兼任几乎所有署名影片的编剧、导演和主要演员,制片人也是他选定的好友。这种独立性源自于他从来没有愁过钱。投资他的影片很少有风险,他的声誉以及一个忠诚的、有效的创作团队使得他的作品无论是在品质上、还是时间上都很有保障,因此投资人往往以入股他的影片为荣。
电影创作的独立性一方面说明他们的影片票房甚佳,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他们作品可以具有鲜明的作者电影的特色。要知道当时最好的电影人的抗争不是为了艺术家的身份,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自由。独立,是他们反对制片人和行业规范、反对社会或伦理审查的关键词。
不过,这两位作者电影人最大的共同之处还是对戏剧的热爱。帕尼奥尔虽然一度中断了戏剧创作,但是对他而言, “戏剧艺术将以另一种形式重生,并获得前所未有的繁荣”。
电影是另一种形式的戏剧艺术,是一种更加大众化的媒体。对于这一点,吉特里也很清楚。他们都把电影看作戏剧的一种新载体,可以让他们的戏剧作品传播得更广、更久。两个人的电影作品都曾被指责是 “戏剧化电影”、 “装进摄影机的戏剧”。平心而论,这种指责不无道理,因为这是他们做电影的部分真实原因。帕尼奥尔无疑看到了电影的巨大商机,他曾预言剧院都将关门,人们都会进电影院去看戏剧。
而吉特里也急于将自己的戏剧用电影保存下来。他会要求电影尽可能地忠实原剧,甚至会让想排演其剧目的剧团观看剧目的电影版,以便忠实于他对演员的表演和舞台布景的最初设计。
从某种角度看,这种照搬照抄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30 年代的有声电影很大程度归功于通俗戏剧、笑剧、传统剧目,还有杂耍歌舞以及现实主义的通俗歌曲。”
这两位成熟的剧作家凭借他们的戏剧经验,为初期的有声电影奉献了很多成功的戏剧改编作品,比如帕尼奥尔着名的 《马赛三部曲》和 《托巴兹》,还有吉特里在 30 年代拍摄的 9 部改编自同名戏剧的影片,虽然不能说皆是佳作,但至少每部都已经受了舞台的考验。这些影片故事情节紧凑有张力,人物形象鲜明,易于激发观众的情感和思考。电影正是吸收了像戏剧这样的传统艺术形式,才得以迅速成长起来。
他们的作品具有一个重要的戏剧化特征,那就是影片总是充满喋喋不休的对白。电影界里有一派,坚持要求弱化对白的作用,以保持电影的特殊性。导演希区柯克就曾说过: “对于我而言,一个编剧的主要罪孽就是当谈到要克服困难时就用 ‘我们用一句对白来解释’的话来敷衍。对白应该是众多声音中的一种,它从人物的嘴里说出来,但是人物的行为和眼神讲述了一个视觉的故事。”
但是,对白却是戏剧中首要的、基本的要素。戏剧家出身的吉特里和帕尼奥尔都痴迷于语言。“语言对于帕尼奥尔而言,就像色彩对于米开朗基罗那样必不可少。”他喜欢在拍摄时 “一直呆在采集声音的卡车里。拍摄最让他感兴趣的是听演员念对白。他会听演员念的是否准确,体会每一句对白的效果”。
而吉特里扮演的角色会滔滔不绝让搭戏的对手变成一个摆设。银幕上这种长篇对白、甚至是独白,有时候会让观众感到厌烦,因为观众通常期待的是更生活化的语言、更生动的画面。而戏剧语言却倾向于抽象夸张,照搬到银幕上就会显得生硬,这是两个人某些作品中共同的一个硬伤。
然而,他们的语言也有很多闪光点。对帕尼奥尔而言,是成也语言,败也语言。他的电影语言最成功、最独特之处在于保留了南方口音。对此,巴赞有过最精彩的评述: “在帕尼奥尔的电影中,口音不是一种取悦人的附属品、一个地方色彩的音符。它和文本是同体的,并由此和人物是同体的。他笔下人物的口音如同别人的黑皮肤一样。口音是他们语言的物质本身,是他的现实主义。因此,帕尼奥尔的电影和戏剧化是相反的,它通过语言进入电影的现实主义特征……帕尼奥尔不是一个转投电影的剧作家,而是有声电影最伟大的作者之一。”
口语特色可谓被抬高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地位。虽然帕尼奥尔清楚地认识到电影话语和戏剧话语的不同,比如他会提醒演员要注意用更自然的方式去发音,但他对话语的偏爱让他的电影手段最终难逃过于单一的宿命。连巴赞这样为他的影片辩护的评论家 ( 他曾说指责 《马里乌斯》和 《面包师的妻子》唯一的缺点是不像电影,就如同谴责高乃依没有遵守三一律) 也要承认,“帕尼奥尔对电影技术的忽视程度让人无法接受,他无法驾驭自己的灵感,作品中的糟粕和精华并存。”
特别是到了后期,虽然帕尼奥尔一直喜欢把摄像机搬到大自然中去 ( 这也是他前期为人称道的重要的现实主义特征) ,但是影片中的大自然始终没有单独成画,没有获得独立性,而是沦为舞台上的一块背景画布。只要比较一下帕尼奥尔的《山泉玛侬》和克洛德·贝里( Claude Berri)1986 年的同名翻拍影片,就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帕尼奥尔只是单纯地把演员从舞台搬到了自然背景中。从这种角度讲,帕尼奥尔将电影打回了次等艺术的地位。
同样,吉特里笔下的人物也往往以语言见长,大段的独白屡见不鲜。不过和帕尼奥尔相比,吉特里有更多神来之笔。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个骗子的日记》 ( Le Roman d’un tri-cheur) 。影片改编自他的小说,除了几个场景有对白,其他的话语几乎都以画外音的形式出现。影片开始,一个人正在写回忆录,然后他的声音就开始扮演不同的角色: 时而是故事的叙述者,介绍故事的背景,来龙去脉; 时而是个评论者,揭示主人公的内心想法; 时而又是故事中的各色人物,客串他们的对白。此外,画面和声音的关系也是或一致或对立。这些手段赋予了画面和声音以极大的独立性,不但时间和空间的广度大大加强,而且刻画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仅凭这一点,这部拍摄于1936 年的影片就充满了现代感,让我们恍若看到了 60 年代新浪潮电影的大胆实验。此外,这种手法在吉特里的历史题材影片中被部分采用,一个画外音承担着重要的叙述功能,将历史事件进行跨时空组合,使得他的每部历史题材影片都具有极大的时间跨度。同时,这种声音是一种明显的主观视角,时时地把作者吉特里的历史观印入他的作品。
的确,霸气是吉特里影片中声音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每部电影都是他的一个声音。这种强烈的控制欲充分地表现在电影的片头。吉特里为他的每部电影都设计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片头,而且每个片头都有吉特里作为影片作者自述的一段介绍,或是介绍创作团队,或是介绍影片的创作过程。最有意思的或许就是 《坎特纳克村的珍宝》 ( Le trésor de Cantenac) 的片头。故事中的人物来到吉特里家中登门拜访,希望他把村里发生的故事拍成电影。吉特里听完故事,当即就叫来拍摄组的主要成员和演员们。在过道里,故事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演员擦肩而过。而吉特里不仅扮演了作为作者的自己,还是故事的一个主角。于是观众就看见两个穿着不同服装、有着不同身份、却有同样一副嗓音的吉特里在办公室里对面对地坐着! 吉特里显然对自己富有磁性的嗓音充满了自恋般的自信。就像每部戏剧开场的那声铃响一样,这个声音在提醒人们: 演出就要开始了! 您就要进入吉特里的世界了!
声音的运用上,已经不难看出帕尼奥尔和吉特里电影表现手段对戏剧的继承和发扬。这些手段可能使他们的电影更具有 “戏剧化电影”的外壳,但是不可否认,这对于襁褓中的有声电影来说,实在是一种贡献。
戏剧和电影的另一大区别在于时间和空间的安排。戏剧由于舞台的限制,必须采取一些抽象的方式来展现时空变化,而电影可以通过流动的、迅速转化的画面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固定的时空、单一的场景常常被指责是戏剧化电影的弊病。在帕尼奥尔和吉特里改编自戏剧的影片中,这个特点都很明显。但是,传统戏剧在场景调度上的丰富经验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吉特里在把戏剧的场面调度运用到电影这一点上颇有创举。在他众多的历史题材影片中,场面调度担负了时空转化的功能。比如在《跛子魔鬼》 ( Le diable boiteux) 中,同一个办公室里接二连三地迎来了路易十八、拿破仑、查理十世和路易·菲利普,上演了拿破仑百日、波旁复辟以及七月王朝建立的好戏。还有 《如果要讲述巴黎》 ( Si Paris nous étaitconté) 使用了一个摇镜头,画面中相邻的街道里依次走过了 13 世纪从布汶大获全胜的菲利普·奥古斯特的军队、亨利四世进驻巴黎的军队以及 19 世纪从奥斯特里茨凯旋的拿破仑军队。历史的相似和时间的流逝就在一个单一的空间里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有些时候,这种舞台式的场面设计大大增加了影片的趣味性。
比如在 《坎特纳克村的珍宝》中,为了展现重获生机的乡村,作者安排一队欢快的年轻人骑着单车依次排队从一列大树间蜿蜒穿过。再比如在 《一个小偷的日记》中,主人公为了躲避警察的追踪,时常化妆出行。影片使用固定视角,让乔装改扮的主人公多次出入一家饭店的旋转门,甚至还对着镜头向观众挤眉弄眼。电影史上经常引用并赞扬奥森·威尔斯( Orson Wells) 的 《公民凯恩》 ( 1941 年) 中的一组镜头,通过凯恩和妻子共进早餐的同一地点的几个类似场景来体现夫妻感情的日益淡化,其实,吉特里在 30 年代就广泛使用了这种手段。
帕尼奥尔的场面调度手法很好地说明了戏剧和电影之争的时间流变。在他初涉电影的时候,戏剧化电影备受争议,他也有意识地避免过于单调的、戏剧化的场景,除了把摄影机搬到大自然中,他还刻意加强时空的流动性。比如在 《芬妮》中,当芬妮得知自己怀孕后,从诊所出来,茫然地走在城市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影片采用了长镜头远焦距跟拍,反而凸显了一个女子在人群中的落寞和孤独。但是随着有声电影站稳脚跟,戏剧化电影也不再是众矢之的,帕尼奥尔影片中的镜头却更加固定了。
影片 《托巴兹》是最好的例子。即使不算1932 年由他人导演的第一个版本 ( 这个版本由派拉蒙一位有经验的有声电影导演执导,加入了诸如室外镜头、衔接镜头之类在当时被认为是电影特有的手段) ,1936 年和 1950 年的两个版本也有所区别。如果说第二个版本还有一些外景和空间变化来点缀,第三个版本几乎完全照搬了同名戏剧的结构,是一部十足的室内情景剧。
三、一南一北
一南一北指的是两人鲜明的地域性以及作品风格。帕尼奥尔往往被形容为一个南方作家,作品中浓郁的普罗旺斯风情可爱迷人。无论是他自编的影片,还是改编自让·吉奥诺( Jean Giono) 文学作品的影片,都是以南方风土人情、特别是农民为对象。即使是以城市为背景的影片,比如马赛三部曲,描写的也是一群淳朴的普通人,城市是背景,大海成为诱惑,就像在其他的影片中,农村是背景,平凡而根本,是希望之地,而城市是诱惑之域,充满了危险和机遇。有的评论家,比如巴赞,甚至将帕尼奥尔唯一一部城市影片 《托巴兹》的失败归结于导演不善于处理城市主题的影片。地域性已经成为帕尼奥尔的标签,连对他颇有微词的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都承认,“他的影片在国外取得巨大的成功”,“尽管帕尼奥尔有毛病和局限,但是他说明保持民族特色才能更好地进军国际舞台”。帕尼奥尔曾经说过: “如果我是画家,我只画肖像画。”
人物始终是帕尼奥尔作品的中心,除了 《重生》,他的影片都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其中又以女性主人公为主。这些女性大多是芬妮的翻版,都是善良、纯真和坚强的正面形象,都是为了爱情可以奋不顾身的痴情女,虽然有时她们拥有的只是一份盲目或者虚假的爱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爱情故事中常常有两个特殊的角色,其重要性和光彩甚至会盖过主人公。一个是费尔南德 ( Fernandel) 经常扮演的暗恋女主人公的纯真汉,这个善意的“第三者”一般都具有更丰富的内心世界,且被费尔南德演绎得活灵活现。另一个就是由莱缪 ( Raimu) ( 《马赛三部曲》、《掘井人的女儿》) 或者亨利·普彭( Henri Poupon) ( 《安吉尔》、《傻冒》、《娜伊丝》) 扮演的父亲形象。
在这个角色身上集中了舔犊之情和家族荣耀的矛盾。面对犯了不光彩错误的女儿,父亲往往表现出同样多的温情和绝情。绝情是因为社会伦理道德要求他惩罚自己的孩子,而人性又让他的绝情也带着温柔。正是这一点,让他的作品摆脱了地域的限制,具有了更深刻的普遍价值: “和让·吉奥诺的作品一样,他的作品深植于特定地域群体的光线、声音和情感中,却并不雷同于民间传说。它所表现的一小块土地并没有封闭在传统中。相反,它希望成为整个人性的小宇宙。这就是它的优点和力量。”
与此对应的是帕尼奥尔作品中一贯自然清新、温情脉脉的风格,不求惊世骇俗,不求激情澎湃,更像邻里之间谈论家长里短,朋友之间调侃轶事趣闻。以平淡见长,从这个角度讲,称他是电影现实主义的先行者并不为过。
吉特里的影片中很大一部分的主题是两性家庭伦理。但是,这些影片的背景基本都是城市,而且如果说帕尼奥尔笔下的多是农村的好女人,吉特里则更钟情城市有产阶级的坏女人。水性杨花是她们普遍的毛病,所以常免不了有一个戴绿帽子的丈夫。虽然帕尼奥尔的影片也出现过这种角色,但是两个作者的态度颇为不同。在帕尼奥尔的影片中,帕尼斯前妻的背叛只是被老朋友们偶尔拿来调侃的谈资; 而面包师虽然企图自杀,更多的不是出于被村民耻笑戴了绿帽子,而是伤心妻子离去,最终他还满心欢喜地迎回了妻子,让她回心转意。然而在吉特里的影片中,作者给这些丈夫们的建议却是同样去偷情,而且是和更年轻漂亮的女人去偷情。吉特里不是在讲述爱情故事,而是在描绘两性之间可能的关系,是激情 ( 《四人舞》 [Quadrille]) ,是欲望 ( 《德兹雷》[Désiré]) ,瑏莹是快乐 ( 《好运》 [Bonnechance]) ,也是嫉妒 ( 《多阿》 [To]) ,是厌恶 ( 《两只白鸽》[Aux deux colombes]) ,是仇恨 ( 《毒药》[Le Poison]) 。吉特里在影片中对女人奉献浓情蜜意的同时,也对她们的可恶之处大放厥词,以致招来了鄙视女性的骂名。
此外,父子关系也成为吉特里三部影片的主题: 《我的父亲有理》 ( Mon père a raison) 、《演员》( Le Comédien) 和 《德布罗》( Debu-rau) 。但是,这些角色都是以他的父亲吕西安·吉特里( Lucien Guitry) 为原型的,是为了纪念 “他的”父亲,纪念一个着名的戏剧演员,而不是塑造一种父亲形象。和帕尼奥尔明显不同的是吉特里还拍了为数不少的另外两种题材: 历史故事片和犯罪片。前一类有《王冠上的珍珠》、《香榭丽舍溯源》、《跛子魔鬼》、 《如果要讲述凡尔赛》、 《拿破仑》和《如果要讲述巴黎》,后一类有 《毒药》、 《一个老实人的生活》、 《凶手和小偷》和 《三个成双》。这些影片基本都是在二战后拍摄的,相对于前期的情节剧,这些影片的基调普遍悲观,直白地表现历史的不公正和人性的丑恶。
如果前期的吉特里是轻佻和嘲讽的,那么战后的他更多的是尖刻和幻灭。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作者的人生境遇发生了重大变化。战前,吉特里的名声可谓炙手可热,他的戏剧在剧院场场爆满,他在装满了艺术珍品的私人宅邸里接待着国内外的各界名流。但是,因为在二战期间和德军有所交往,信奉贝当元帅,他在解放初期被囚禁,财产被抄没。虽然很快被释放,但是声名大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一个不受宠的人。为了自我辩解,吉特里把历史影片看做一种阐述自己的历史观和爱国理念的载体。热爱法兰西,这点在吉特里身上是一贯的、坚定的,问题是他的道路是保守的右派道路。早在 1938 年,他的《香榭丽舍溯源》和让·雷诺阿的《马赛曲》
几乎同时上演,而一右一左的历史观截然不同。吉特里的历史精英论一直主导着他的历史影片。此外,1950 年的 《坎特纳克村的珍宝》更典型地高调歌颂了劳动、忠诚和家庭这些维希政府的口号。相对当时盛行的左派主流思想,他保守得甚至有点反动。同样,几部犯罪片更是没有惩恶扬善的基本道德底线,罪犯凭借狡诈和欺骗的手段,摆脱了仇人的追杀、警察的追捕、法庭的审判,得以逍遥法外。更甚者,吉特里在讲述中,没有惋惜和谴责,而是带着罪犯一样的玩世不恭。
和吉特里的大起大落相反,帕尼奥尔的一生平安顺利,功成名就。一个健全家庭里的好孩子,学校里的优等生,经历了短暂的教师生涯,然后在戏剧界成名,通过电影致富……特别是二战以后,帕尼奥尔的个人声誉达到了顶峰。1946 年他被封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还受到国内外电影人的肯定和追捧。比如意大利导演罗西里尼对他说: “电影新现实主义之父,不是我,而是你。如果我没有看过 《掘井人的女儿》,我永远拍不出 《罗马,不设防的城市》。”
而奥森·威尔斯也公开承认受到过六个导演的影响,其中就有帕尼奥尔。在南方自己的领地里悠闲踱步的帕尼奥尔什么都不缺了,什么也无需证明了。但是,随着他电影手段的固步自封以及电影生产环境的改变( 个人越来越难以单独承担昂贵的电影制作了) ,他的电影生涯也将画上句号。即将诞生的是一个小说家帕尼奥尔。
一南一北,一热一冷。帕尼奥尔的作品似乎总洋溢着南方明媚的阳光,温暖宜人。而吉特里的作品擅长嘻笑怒骂,常透着北方冬雨的一丝凉意。风格即人,有风格方能摆脱匠人的身份,进入作者的行列。不论是帕尼奥尔还是吉特里,他们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们确立了一种作者风格,不可复制,所以独一无二。上世纪50 年代,当他们同辈的老艺人们被新浪潮的年轻一代斥为老朽过时的手艺人,他们却依然屹立不倒,正是因为风格立人。在年轻一代眼中,他们不是手工匠,而是真正的作者,是艺术家。
结 语
在吉特里的 《巴斯德》中,有一句台词:“先生们,我知道我没有使用你们所熟悉的那种风格。”帕尼奥尔和吉特里就像从戏剧界杀进电影圈的两匹黑马,他们的成功说明戏剧和电影不仅仅是对手,还可以是朋友。固执于它们的不同是狭隘的,更应该看到作为一种叙事艺术,它们具有很多的互通性。或许要改变的,更多的是我们的观影习惯和偏见。我们相信这两位艺术家曾经演绎的 “戏剧化电影”
的传奇在今天依然充满着生命力,特撰文以纪之。
- 相关内容推荐
- 上一篇:中国元素和美国价值在《功夫熊猫》中的体现
- 下一篇:“父子亲情异化”与日本动漫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