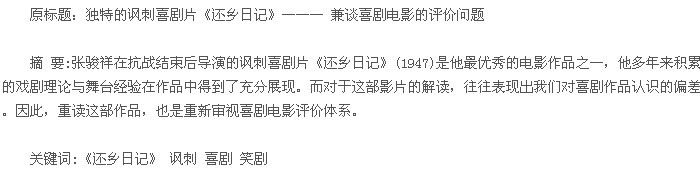
《还乡日记》是 1947 年出品的优秀讽刺喜剧片,也是战后“中电”出品的一系列讽刺喜剧片的开始。
该片编剧、导演张骏祥,长期从事戏剧研究与教学、实践,这是他第一次参与电影编导,是有充分的理论准备的。在《还乡日记》的创作中,我们看到了张骏祥的喜剧观念的呈现方式,具有不落窠臼而又不拘一格的创作特色。
一
民国时期讽刺喜剧片多描写社会中上层生活,主要有两种,一类是改译国外讽刺喜剧,将其改造为中国化的故事。抗战前主要作品如史东山导演的改编自俄国作家果戈理(Николай Гоголъ)所着《巡按》(今译《钦差大臣》)的《狂欢之夜》(1936),孙瑜导演的改编自英国作家詹姆斯·巴雷(J·M·Bar-rie)所着《可钦佩的克莱敦》的《到自然去》(1936),沈西苓导演的根据爱尔兰作家希恩·奥凯西(SeanO’Casey)所着《朱诺与孔雀》改译的《摇钱树》(1937)。抗战时期及战后的几部改译喜剧片多出自商业导演之手,如擅长歌舞片的方沛霖导演了改编自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哀(Moliere)名作《悭吝人》的《夜长梦多》(1943),擅长商业娱乐喜剧片、演而优则导的郑小秋导演了根据法国喜剧家腊比希(Eugene La-biche)作品《迷眼的沙子》改编的《欢天喜地》(1949)。这些讽刺喜剧片多由“国泰”、“大同”等规模相对较小的公司出品,出于资金回笼的需求,对影片的票房尤其看重,在增加商业卖点的同时,往往讽刺力度被大大削弱。这一类型的改译讽刺喜剧片的胶片除《摇钱树》外,目前已无留存,仅就同源的改译话剧剧本来看,这些喜剧本的矛盾冲突主要集中于中产阶级的客厅,并有意放大了男女情感纠葛和家庭矛盾,在对现实反映的深广度上远不及同时期的批判喜剧片。
第二类是原创的时事讽刺喜剧片,从社会现状中直接取材,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讽刺性相对较强。
抗战前时事讽刺喜剧片的主要创作者是欧阳予倩,有《小玲子》(1936)(编剧)、《如此繁华》(1937)(编剧、导演),显示了他特有的知识分子的现实视角。战后时事讽刺喜剧片以“中电”出品为代表,张骏祥编导的《还乡日记》和《乘龙快婿》(1948)是其中翘楚。此外,国泰、大同、中制等公司也制作了不少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讽刺喜剧片。与中电取材战后生活大环境的视角不同,这些影片多以对人性道德弱点的讽刺来代替对社会现象的揭示与嘲讽,虽然少了一点时代意义,却更具普遍性。较好的作品如国泰的《一帆风顺》(1948)、“中制”的《挤》(1949)。当然,这些影片为吸引观众,也会极力渲染男女情感纠葛、刻意安排曲折的情节,这部分转移了观众对讽刺对象的关注。
民国时期的讽刺喜剧片都以戡破丑恶为其审美理想,显示了知识分子的现实关照视角,在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面前,“高尚的精神和情操无法在一个罪恶的和愚蠢的世界里实现它的自觉的理想,于是带着一腔火热的愤怒或是微妙的巧智和冷酷辛辣的语调去反对当前的事物”,于是“讽刺”成为张骏祥等有良知的电影创作者高扬的旗帜。《还乡日记》不仅将讽刺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战后政府昏庸无能所造成的混乱怪诞的社会现象,也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了喜剧形式下蕴含的悲剧本质。不过,与当时的很多讽刺喜剧,创作者在一样讽刺批判现实中丑恶现象的同时,对意欲建立起的“应该是怎样”的理想状况的认识是不清楚的,这也常常使其表现在模糊暧昧的结尾上。
二
张骏祥认为“凡是引观众发笑的就是喜剧”。他又严格地区分出“喜剧”和“笑剧”两种形态,认为笑剧“在精神上,它与喜剧相近,但在外表上,它显得比较粗犷而荒诞”。在今天看来,张骏祥文中所论及的“喜剧”、“笑剧”,事实上都能够归入宽泛意义上的喜剧范畴,尤其也都是构成喜剧电影“喜感”的重要因素。在《还乡日记》中,张骏祥娴熟地将各类“喜剧”、“笑剧”手法杂糅融合,形成既“理智”又极富喜剧性的风格。
张骏祥加入“中电”后创作的两部电影《还乡日记》和《乘龙快婿》(1947)都以“还乡”后的境遇为题材,这也是战后电影复兴的 1947 年不断被重复的一个主题,如《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和《天堂春梦》(1947)。而张骏祥的作品却并未让“还乡者”深陷生存的泥淖之中不能解脱,而是让他们充当抗战胜利后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的观察者,以构建影片冷静客观的独特视点。《还乡日记》中的老赵与小于,因抗战离开都市八年,他们原本憧憬着战争结束后安宁的生活,而战后的上海却处处与他们想象的生活截然相反。作者在这一对人物身上赋予了天真乐观、理想主义的特征,使得影片暂时疏离了忧伤与悲苦,而现实却让他们一再失望、一再受挫,兜了一个圈,他们又回到了鸽子笼一般的阁楼上。张骏祥正是用这样一个回到原点的怪圈,将战后上海各种荒诞现象汇集其中。影片通过这两个人既是经历者又是旁观者的身份,完成了对社会现象的展示与荒诞本质的揭示。
张骏祥从亨利·伯格森“笑与无情相伴”的观念出发,提倡“喜剧诉之于理智”,“喜剧的导演不但不该唤起观众情感的反应,并且应该竭力避免这种反应的发生”,“一旦观众对角色起了怜悯,生了同情,他们就不能再笑他”。可以说,张骏祥设置的这两个旁观者的角色,正是给作品带来理性视角的重要安排。他们由大后方回到阔别八年的上海,他们看到,租房子要“顶费”、黄金十两为一条、“接收大员”接收房子也接收女人……对这些事情充满了陌生感、十分惊奇。观众则与这两个人物一道,完成了对片中离奇的现实状况的冷静审视。
张骏祥认为:“悲剧的导演与作者着力的是唤起情感的接触,使观者同情于主抗角色,把自己置身于他的地位;喜剧的则着力于机智的冷眼,角色都被化成渺小的动物,观者地位超越于角色,于是看着这群东西蠢顽不灵荒乎其唐不觉哑然失笑。”。这也是他“理智的喜剧”的又一重要体现,而具体方法是将这些固执或贪婪……失去了匀称、变成亚里士多德所谓“不如我们的人(Men worse than we are)”的角色加以卑屈(Belittlement)。在《还乡日记》小于、老赵的视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丑角的登场。如片中小桃这个角色就是被夸张地“卑屈”化的。较之老龚、老洪等众多战后喜剧电影中经常出现的接收大员这类形象相比,小桃并没有大奸大恶。她轻信而天真,具有天生的正义感,同时又是一个十足市侩气、庸俗化的女性。影片中她一出现就因为琐碎的物质利益与“接收大员”丈夫老洪口角斗气,甚至执意要买两只脚镯,并不惜撒泼耍赖、大打出手。而在最后的混乱“群架”中,她不仅唯恐不乱地手舞足蹈,而且还不时插上一手。在观众的审视下,这一被“卑屈化”的人物,辗转于两个卑鄙的男性之间,她毫不觉醒、俗气地为了一点点利益而与男人闹得不可开交等行为都显得十分可笑。
当然,作为创作者,张骏祥深谙这些离奇讽刺的喜剧性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悲剧性本质。《还乡日记》中小于与老赵的经历,投射了太多张骏祥自身的经历和情感,在看似充满笑声的剧情背后,沉重与悲情喷薄欲出,使作品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情感色彩。我们可以设想,该片结尾为丑陋的接受大员们安排了一个遭受惩罚的结尾,也是这种愤怒得到宣泄的简单却又十分痛快的表现。同时,影片中也处处以悲观的“文老太爷”和深谙社会现实的黄胖子等人来质疑小于老赵的理想主义,小于、老赵最后真的如他们所料一无所获,可以说,这又是对小于等人视点的纠正与补充。
《还乡日记》给我们的另一感受是喜剧性的丰沛,在影片的任何一个时间段内,无论整体情境的营造、人物形象的定位,还是影片中的种种细节及构成的节奏,都充满了喜剧性,将喜剧做到了“最大化”。
这不仅来源于张骏祥对荒诞现象的深刻体察和举重若轻的喜剧表达,也来源于其对于“笑剧”呈现方式的熟稔。
张骏祥认为,令观众笑的一个诀窍就是“保持一个轻快的速率……简而言之,使整个场面平滑自如地进行,流利迅速地开展,使观众目不暇接,连一个停下来推想估计的当儿也不留”。在《还乡日记》中,张骏祥集中于“房子”构建喜剧情境,在老赵与小于“投靠”朋友黄胖子的过程中,影片就构织了连绵不断的喜剧情节,对抗战后文化界人士的窘迫生活状态予以展现。为了营造层层接近真相过程中的喜剧效果,影片构建了四个“落差”:先让老赵与小于来到一栋十分体面的公寓楼,满以为黄胖子生活条件十分不错。而两人在一层一层寻不到胖子的过程中,不仅疑虑加深,自身也狼狈不堪,而好不容易爬到了“8 楼”,却发现黄胖子住的不过是一个动一动就会碰头、摔跤的低矮阁楼。这与公寓精致高大的外形形成了鲜明的落差。而影片接着又在阁楼的局促上大做文章,小小的转不开身的阁楼中,居然住了 3 个人,床是轮流睡的,桌子也要睡人,这再一次造成落差。窘迫的生活状况在阁楼被进一步的展现,他们一应生活用品都要用绳子从楼下用“升降机”“钓”上来,而这群年轻人的衣食状况也是捉襟见肘。“还乡”后所见的奇异的生活现象得到了充分的喜剧化呈现,而这与其后“接收大员”们的生活状况又形成对照。
张骏祥也十分注重喜剧效果的节奏性,他曾经说过:“笑的分配要匀(记着,不是均),要有个节奏。”
在上述段落的喜剧营造中,我们也能充分体会到张骏祥对于节奏的充分把握,这种喜剧节奏是依靠精心的喜剧细节、经由巧妙地积累与释放来构建的,“在开端是必须收敛,不急于求功……逐渐地加紧,迅速的趋向顶点”。在老赵与小于一层层爬楼寻找胖子的这一长而缓慢的段落中,他们先是遇见了一位绅士模样的人,询问时此人一言不发,用手杖指指上面;第二次两人敲开一户人家的门,一个佣人模样的人用了十分简洁的回答:“胖子? 楼上。”这使用的是上海方言。在这两次询问中,都强调了“胖子”的体貌特征,而到了第三次,两人又敲开一家的门,这次出来的恰恰是个胖子,老赵还是照前面一样询问,但在正要说到“胖子”一词时,忽然意识到眼前正是一个胖子,不禁一时语塞,只好用手势比划出体型魁梧之义。这种细节构建在喜剧电影中很少见,这也与张骏祥长期从事话剧创作与导演,注重舞台现场效果有关。同样的精致细节也出现在两人找房的过程中,在不断重复与房东见面、谈判中,房东的面貌各不相同,且每一个都极具个性,为影片要表现的复杂而漫长的找房过程增加了喜剧感和讽刺性。
张骏祥在解放后曾撰文批评国内电影的对话问题。他认为:“我们的银幕上的人物太爱唠叨,我们的电影里的对话不够生动,不够恰当,缺乏动作性,缺乏弦外之音……”对照张骏祥的喜剧电影创作,我们的确不得不叹服他的作品对于语言、情节、节奏的精准考究,这出于他对于喜剧“笑”的规律的把握。他曾论述到“笑剧对于一个导演,是一块试金石,笑剧的导演需要纯熟的巧技和高雅的风趣。技巧不够,可能显得笨拙累赘,一盘散沙,风趣不足,可能使全剧降至俗劣,低级趣味的胡闹”。
三
对喜剧本质的充分认识使张骏祥在喜剧电影创作中表现出不拘一格的创作手法,对于各种喜剧方式与技巧大胆地“拿来”。他对各类喜剧手法的综合运用,体现出了在四十年代喜剧电影对于喜剧手法综合运用的深层次探索。而对《还乡日记》的评价中比较集中的问题,一是研究者都普遍认为“打闹”段落过分了;二是认为张骏祥在该片中对现实的讽刺力度不够到位。这两点评价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我们对于喜剧电影,特别是讽刺喜剧电影评价标准中的一些倾向。
一般来说,我们都将“打闹”段落作为较为低级的闹剧的基本手段,大量跌倒、追逐、打闹与剧作上的伪装、奇巧一样,是闹剧的基本特征。在张骏祥的戏剧形态划分中,他将闹剧(Melodrama)视为“家道早已败落,变得性情粗野趣味低落”的“失掉灵魂的悲剧”,认为“笑剧是喜剧的表亲,闹剧是悲剧的近戚”。他十分明确地将喜剧分为“喜剧”、“悲剧”与“笑剧”、“闹剧”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层次,并且承认前两者艺术性较高而后两者则较低。但同时他也提出,在考虑使用哪种方式时,两者在美学品质上的高下对于编剧的意义要大大高于对导演的意义,而且,“同是跌打翻滚,其趣味之高低却可以分出无数等级。也许一分一厘之差就可以从妙趣跌入下流”,而“导演者尽管处理的是低级喜剧,在趣味上仍必求其雅尚,不可下流,不可俗劣”。此外,他也深刻地认识到不同的喜剧美学形态对于观众来说有时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因此,“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仍然可以欣赏低级的笑剧,有些自命风雅之士以为低级喜剧就是下品不值一顾,那只证明他们的趣味狭窄而已”。
《还乡日记》就恰恰体现出了张骏祥对于“喜剧”与“笑剧”乃至“闹剧”这几种戏剧方式从导演和剧作角度的深刻理解和自如的驾驭。而在以往对于张骏祥喜剧电影的研究中,批评最多的也是他作品中打闹成分过多,认为这“是过火的地方,甚至影响了演员的表演”,“过于冗长的打斗场面又使得影片情节变得拖沓起来,影响了整个影片的节奏,变成了一场闹剧”。而事实上,打闹段落不仅没有破坏该片的整体和谐,而且是影片高潮不可或缺的方式,同时也体现着张骏祥睿智而彻底的喜剧精神。
《还乡日记》以喜剧手法表现荒诞的战后生活现实,尤其是老龚、老洪等人为了房子、女人而上演的“接收”丑剧,在影片中已经进行了充分的描摹。因此,在影片接近尾声时以撕破了脸、大打出手让二人的丑恶嘴脸充分暴露,并没有丝毫过火。相反,不如此,不足以构成一个比前面更加激烈更加荒诞的喜剧情境。而两人在如此打斗之后,居然奇迹般地握手言和,并且荒唐到极点地要共用房子、共用女人,闹剧的段落就不仅是人物塑造的必须手段,也是保持剧作顺畅合理的必要因素了。
同时,张骏祥在片中尽量避免对于打斗段落的“过火”表观,对于老龚的第一次被打,只是以被打伤寻求帮助来表现,而在最终大打出手的段落中,也多以小于、小桃的表情间接地表现其过程,同时有意将镜头视角抬高,只拍摄空中飞舞的投掷物体,并穿插了黄胖子等人在房子外面的镜头而省略了大部分具体的打斗场面。而李天济先生饰演的“老二”在打斗中发现一个与自己十分相像的泥塑小鬼,并狠狠地将其砸烂,更是这一过程中的神来之笔。最为重要的是,这一绝非为笑闹而刻意为之的闹剧段落,正体现了恣意放纵的彻底的喜剧精神,在一个荒唐可笑到令人发指的世界里,人们找不到身体与心灵的栖息之所,那么,既然毫无改造的希望,就索性酣畅淋漓,彻底地砸烂它,再来重建一个全新的世界吧!
张骏祥解放后对于《还乡日记》的创作目的进行论述时,他自述是“想借此讽刺当时反动派到处接收的混乱状况”。该片作为优秀的喜剧电影作品,一再被评论界肯定的也是其“讽刺”价值。而在张骏祥的喜剧观点中,他却并未将“讽刺”视为高明的喜剧手法,他认为讽刺是一种“有意的言辞滑稽”,即创造滑稽效果的主观语言手段,并对其喜剧效果持保留态度。不能否认的是,讽刺在喜剧美学层面上的确属于一种较为高级的形态,而同时作为一种能够直接诉诸于观众情感的审美效果,讽刺也带有极大的社会功利性。在我们以往对于喜剧评判的标准中,讽刺的美学性和功利性至少是被同等看待的,在某些时期,后者往往还占据上风。
而反观张骏祥在《还乡日记》一片中对于讽刺的拿捏,我们会发现他极好地控制了喜剧的“理智”对于“讽刺”的驾驭,他并未为讽刺而一味在作品中填塞入更深广的社会现实,也并未将老赵与小于的经历世俗化为一个能引起更多同情怜悯的传奇性故事,而是着力于以丰富多样的喜剧方法来构建接连不断的“笑”的情境,让观众在笑声中完成对于丑恶的认知。相较于讽刺性浓烈而趋于“正剧”的喜剧电影,张骏祥的喜剧片无疑能为更广大的观众接受。他自己也认为,“常有人说中国观众不爱看喜剧”,是因为“中国观众不能接受过于纤巧的滑稽”“如果喜剧对于一般观众不知所云”,“即使场中有三数个大学教授之类对于剧中滑稽完全领略,于事也毫无所补。笑是社会性的东西,是依赖群众心理的东西,结果怕是只有这三数个人也觉得索然无味”。
《还乡日记》也常常被拿来与张骏祥的同时期作品《乘龙快婿》比较。在以往的所有评论中,都体现出这样一个较为一致的倾向,即创作于《还乡日记》之后的《乘龙快婿》比前者更大胆,暴露问题更多,喜剧手法上也更高明。
无疑地,《乘龙快婿》在涉及的社会现象方面较之《还乡日记》“要广阔丰富得多了”。它采用了自《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等影片为起始的、借用商业化的故事为外壳来获得带有社会批判意图的言说空间的喜剧电影惯用手法。同时,这也使深刻而理智的喜剧手法被表面化的现象呈现与一个规整的风俗故事所替代了,精致而高明的喜剧智慧大大减少。可以说,在《还乡日记》中,张骏祥体现出了自由的喜剧创作态度,而在《乘龙快婿》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聪明且功底深厚的创作者对于既有喜剧电影创作方式自觉地迅速地学习。这两部作品中的故事也恰好隐喻了这两部作品的两种定位:《还乡日记》好比是一种刚刚来到电影创作领域的毫不领世情的创作,而《乘龙快婿》则在一度生疏后很乐意地接受了既有创作规范的收编与整顿,成了真正的“乘龙快婿”。这种自觉地与主流靠拢(商业形式也好,文艺的意识形态要求也好)的态度在张骏祥其后的电影创作生涯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作为一个难得的具有深厚理论素养和实践功底的知识分子创作者,张骏祥的这种“自觉”却让我们深深为之叹息。
张骏祥认为“笑是与社会的进化和一般人民的知识程度有关的”,这是他针对普通的戏剧(电影)观众而言的,涉及到的是作品普遍的欣赏问题,而对于专业的喜剧评论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对于张骏祥作品尤其是《还乡日记》的解读,恰恰体现了我们在喜剧作品的解读上的一些倾向,重新理解张骏祥作品,不仅是对某一个作品评价的纠正,也是对喜剧评价体系的一种审视。
参考文献:
[1]黑格尔. 美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张骏祥. 喜剧的导演[J]. 学术季刊,1942(1).
[3]张骏祥. 笑剧的导演[J]. 演剧艺术,1945(1).
[4]张骏祥. 电影的对话[J]. 中国电影,1957(7) .
[5]张骏祥. 闹剧与感伤剧的导演[J]. 文章,1946(3) .
[6]程季华. 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