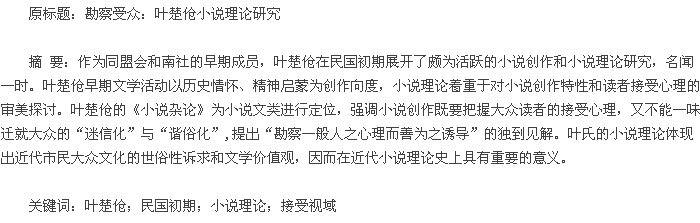
清末民初,江南处在对外开放的前沿,经济和文化活动异常活跃。随着报社、书局、学校等公共文化机构的出现,小说创作得以作为一项独立的职业萌发,并出现了一批职业作家。与上海大都市毗邻的苏州,一批文人在“南社”的旗帜下,麇集奔走,开启民智,宣传革命。此时,外国小说翻译与本土小说创作颇为兴盛,文坛对小说作品(包括通俗小说)的学术研究也应运而生。迄至今日,黄人、徐念慈、苏曼殊、包天笑等人在小说理论方面的实绩,得到了学界的重视,而学界对叶楚伧这位当时颇有名气的文人,却缺乏足够的关注。由于近代政治的烟云遮蔽,学界对叶楚伧小说理论的研究,暂付阙如。为此,笔者聚焦于叶楚伧的《小说杂论》,彰显他的小说受众理论及其接受美学话语,并探讨清末民初小说接受观念的人文历史之因素。
一
叶楚伧(1887-1946)出生于苏州周庄镇的书香世家,1903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不久转入浙江浔溪公学,翌年考入苏州高等学堂。毕业后赴广东汕头主持《中华新报》笔政,以文字鼓吹革命。他分别加入同盟会和南社。民国成立后,叶楚伧在上海主编《太平洋报》《民国日报》《民立报》副刊,积极从事文化启蒙活动。1920年以后他步入政坛,出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和宣传部长等要职。从文人到政要,这种起伏变化的人生路径,引人注目,也受争议。但综观其为文、为官的生涯,叶楚伧终不脱书生本色。
就早期身份而言,叶楚伧是个活跃多产的文人。小说创作是叶楚伧文艺活动的重心。他创作了《古戌寒笳记》《如此京华》等章回体长篇小说,以及《蒙边鸣筑记》《壬癸风化梦》等中、短篇小说作品,使用过叶叶、小凤、湘君等笔名。叶氏为人潇洒倜傥,富有“剑胆箫心”“诗心风流”的文学情调。民国着名作家张恨水曾说:“叶楚伧才大如海,心细如发,白话文言,均超上乘,似盛唐才子,而其意气纵横,假酒助勇,则又似李青莲。”
这种认识与评介,部分反映了叶氏作为着名文人的精神风貌。可以说,1920年以前,叶楚伧在报界与文坛,成就斐然,影响较大。
除了小说创作外,叶楚伧还致力于小说理论的研究。《小说杂论》是叶楚伧在民国七年(1918)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上的系列文章,加起来有数万言,后收入《小凤杂着》(新民图书馆1919年出版)。《小说杂论》属于清末民初的“小说话”类型。“小说话”是以短小精悍的漫话方式来对小说进行评议的杂文体式,由系列文章构成,与近代报章杂志相结合,带有现代随笔批评的特点,比古代诗话、词话更具学术讨论性和时代在场性。
故在清末民初的一二十年间,各种报刊上的“小说话”风靡一时,到处可见,报载“小说话”的名称有:小说丛话、小说小话、小说闲评、说小说、小说余话等。叶楚伧把自己有关小说研究的文章,命名为“小说杂论”,显然是试图在“小说话”的基础上,对小说文类进行一种多元性、综合性的论述。
从时间上看,叶楚伧的小说创作在先,小说理论在后。较之古典小说,叶楚伧把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称作“新小说”,意指此类小说具有新的创作队伍、描摹对象、表现方式和受众群体。叶楚伧既是通俗小说的实践者,又是小说文类的论述人。《古戌寒笳记》以朝代转换、英雄情怀为历史向度,杂糅中国传统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的元素,悬念迭出但绝非娱乐性的奇侠小说;《如此京华》以社会批判、精神启蒙为思想向度,揭露了北京官场的黑暗内幕,其逼真的讽刺性,超越了当时的黑幕小说;《蒙边鸣筑记》借鉴了近代侦探小说的成分,有言情内容却与民族命运攸关。叶氏小说以通俗的文言写作,表现的却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振荡与现实危机,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
由于叶氏的小说创作正是近代“鸳鸯蝴蝶派”盛行的时期,又与“鸳鸯蝴蝶派”的包天笑、郑逸梅等作家相交甚密,再加上“不脱吴儿山温水软之习”,故当时曾被归为“鸳鸯蝴蝶派”.其实,叶氏小说作品不论是内容的错综复杂,还是情节的曲折多变,都达到了一种雄浑、深邃与巧妙的境界,对当时流行的通俗小说有所突破。叶氏的小说理论与小说创作具有某种统一性。他着重于小说创作特性和读者接受心理的审美探讨,推崇近代多重文化空间中的言情小说、社会小说、神怪小说、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等文类创作及其杂交组合。叶氏认为前三种小说为中国所固有,后三种则属于外国小说之传入。各种小说类型满足不同读者的欣赏兴趣,作家可以专精一类,或有机组合几种类型,最大限度地发挥小说的接受效应。
清末民初的小说繁荣,带来创作潮流的变换更替。吴地文人范烟桥曾经指出:“随着读者的口味而时相转换,汇成‘潮流'.有时哀情小说成了潮,有时是社会小说成了潮,有时又是武侠小说成了潮……一个潮起来,’五光十色‘、’如火如荼‘,过了一个时期,潮退了,也就’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又换了一个潮。”[2]169在叶楚伧生活的时代,新与旧、雅与俗尚未区分,社会文化空间呈现出混杂暧昧的特征。叶氏是具有“小资”情调的报人。当时,报纸期刊等现代传媒对人们的城市生活方式乃至生活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上海被辟为“租界”,十里洋场,纸醉金迷,报纸期刊逐渐成为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培育了为数不少的自由撰稿人和较为庞大的小说读者群。作为橐笔卖文的职业文人,叶氏蟠胸千卷,灵府不俗,有“独立书斋啸晚风”的气概。郑逸梅回忆,叶氏有酒癖,每餐必饮。在《民国日报》副刊当主笔时,他在办公桌上放置白兰地酒一杯,花生米一包,边饮酒边撰文。叶楚伧状貌魁梧,而为文却很秀丽,被戏为“以貌求之,不愧楚伧;以文求之,不愧小凤”[3]127.可见,叶楚伧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理论研究,是与时代状况和个人性情密切相关的。
叶氏的小说评论有两个重点。一是重视古典章回小说的优良传统,认为“《水浒》之妙,在辞微义严;《三国演义》之妙,在辞义俱严。辞微义严者,必待读者之探索;辞义俱严者,则无待于是。” [4]
叶氏继承了“以意逆志”的古代诗文评的传统。二是赞赏近代通俗小说作家的精品杰作。例如《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叶氏认为均属“佳作”而独树一帜,因为它们以清明去芜杂,以本色去浮艳,艺精技巧,雅俗共赏。
小说的创作分寸、艺事得失,是叶氏忖度的问题。叶楚伧强调小说创作应该引导世俗,美化文心,药治士风。他对通俗小说的接受要求,做了具体的性状考量。对于言情小说,作家要考虑接受效果,严加情淫之辨,以正面文章写男女间之至美爱情,不渲染色情。对于社会小说,作家要考虑社会效果,多为无告者呼号,少替强盗骗子做辩护。对于政治小说,作家要考虑社会正义问题,贬褒并施,彰显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叶氏提醒小说家需注意作品行世之影响,对社会、对读者持负责的态度,那些借言情、黑幕进行诲淫诲盗的小说商,无异于私贩鸦片。如此注重小说的社会效果,可谓用心良苦。
二
研究小说,首先必须定位。叶楚伧肯定小说具有“势力”,小说能发挥特有的社会作用,小说之普遍作用力是一般的教育所不能完成的。小说有两大作用:一是“窥察今古”.小说历来是时代的镜鉴,时代盛衰可从小说中找到线索。例如,今人能在《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中看到世态人心、人际关系与历史境相。二是“入人之深”.
小说能够予人以影响,能够作用于人心。民间流传的“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的俗谚,表明两部小说中的计谋与勇敢的故事,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效应。但是,小说毕竟不同于有史记性质的列传的特点。叶楚伧界定了列传与小说的区别:列传记载精微,小说叙述显豁;列传贵在真实,小说之言可放诞;列传的传主多为单个人,小说所涉内容包罗万象;列传记叙尺度较严,小说描写则求神似;列传复述传主的来龙去脉,小说则不必详细交代主人公的生死结局。如此,叶楚伧既阐明了小说与历史的关联,又厘定了小说自身的属性。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诗词曲)、文(散文)向来是两种主要文体,小说处于边缘地位。梁启超在20世纪初倡导“小说界革命”,打破了这一格局。小说作为近代文坛的一种火爆的文体,为当时的有识之士所青睐。在叶楚伧之前,吴地学者黄人在执教东吴大学时所着《中国文学史》中就强调小说是文学之主力,服膺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理论,但是他觉得对小说的社会价值之认识,须保持一种冷静裁判的立场,“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昔之于小说也,博弈视之,俳优视之,甚至鸩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今也反是:
出一小说,必自恃国民进化之功;评一小说,必大倡谣俗改良之旨”[5]288.黄人反对极度轻视小说或无限夸大小说的偏向,力争给小说以恰当的定位,即小说既不能承受生命之轻,也不能过度地承受社会之重。黄人冷静地对待清末“小说界革命”思潮,在《小说小话》中,力图探寻小说的审美价值。
在借鉴黄人小说理论的基础上,叶楚伧对小说进行了更为公允的评估:“小说之道虽小,而人间之不可无此之物,与经史无异。不过一则形而上之,为国家之光;一则形而下之,为人民之铎耳。吾今见有人读小说而讳之曰笔记杂着,此大不可也;有人作小说而讳之曰游戏消闲,尤大不可也。其必讳之者,是即不是小说者也。虽然,其视小说也,既若是之重,则其辨之亦必甚严。”[6]84叶楚伧认为小说是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作品,今人需要严格辨别其性质。小说创作若要获得大众的青睐,必须做到文本与读者的会通。
一是小说创作需要讲究艺术特色和创作技巧。叶楚伧认为作家必须把握两点:其一,性格的描摹。施耐庵的《水浒传》描摹人物惟妙惟肖,鲁达之爽快、武松之雄俊、杨志之郁勃,石秀之精灵等等,皆出类拔萃。由于作家“相其才,度其性,别其遇,以体贴揣摹之”,故这些人物“同为强盗,而仪容性情之不同如此,遂翕然赞叹其揣摹之精,而不知施之乖觉绝世也”[6]80.描摹人物的仪容性情,虽然是小说家第一难事,但施耐庵以其实力能克尽之。今日作家,例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可谓活画出官场之丑态,然而亦只有一副面孔,创作手法稍逊于施耐庵。小说创作的关键,在于写好人物的个性。人物个性既表现在行为举止层面,又表现在人物语言当中。《水浒传》在用人物语言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做得非常好。例如,李逵对张顺说道:“你莫在岸上遇我。”张顺回答说:“我在水里等候你便是了。”两人这番对话,其实是话中有话,都是毫不客气地炫耀自己,一个强调岸上的本领,一个强调水里的功夫。各人自有各人的强项。充满性情与性格的对话,预示两人开打过程将会精彩。如此人物语言描写,颇能见出个性,相当出色。其二,情节的拟构。小说创作要达到扣人心弦的艺术效果,则“须先构一奇特之局,如天地之布置山川然,潆洄峥嵘,令读者如入山阴道上”[6]88.《三国演义》描写赵云过五关斩六将的情节,波澜迭起,引人入胜。
二是小说创作要有引人入胜的美感属性。叶楚伧认为作家需要臻达三个方面。首先是格局之妙。小说作者须有气度,“苟能胸罗万里,足遍九州,为指陈形势,体会人文,经营一局之小说可也,为闺房儿女之小说亦无不可也,且无一不得其妙也。何则?其取也精,则其用也宏,宜无所施而不可也”[6]80.小说创作,须要内外匀称,交代明畅,疾徐有度,动静有致。叶楚伧随之揭出一条小说原理,即作文之道,首重布局,格局既定,一气呵成,终得佳作。其次是景象之美。叶楚伧赞赏《水浒传》写景摹物自有特色:黄泥岗之烈日,草料场之积雪,蜈蜙岭之月色,景阳冈之斜阳,皆非庸手所能写之。而鸳鸯楼外之残月,孔家庄之微风,则尤为他人不可及。此种景象刻画,自然又具真趣,让人身临其境,领略天地造化。再次是回目之精。叶楚伧觉得小说家要讲究章回体小说的回目。一般来说,作者创作时,拟构回目次序,然后撰写小说,写完小说再订正回目。曹雪芹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红楼梦》第三十五回标题“白玉钏亲尝莲叶羹,黄金莺巧结梅花络”,词句凝练,工整对称,无一字无来历,毫无牵强,既绮丽,又贴切,充分显示出作者的写作功力。叶楚伧认为自己创作的章回体小说《官僚丑史》第三回的标题“钗光钿影,绿暗红稀”,虽词藻艳丽,但未能反映出官场黑幕,似可再推敲。最后,与小说章回目录相关的,是小说的命名问题。命名的要点,必须凸显小说的亮点,若过于纤丽,则将影响作品的审美质感。叶楚伧称赞近代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书名恰当,质朴明晰。在具体的拟构过程中,小说命名的方式有正有奇,不能拘泥一种方式而论。重要的是,小说家能够奇正相应,摆脱窠臼,不流于狐禅野道。
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学从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型都处于过渡状态,进取的胆力和明辨的精神常常成为文学研究的机杼。“先驱”与“才子”们都为之奉献着心力与才情。与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晚清“小说界革命”论者相比,叶楚伧对小说的特质以及职能的看法,似乎更客观公正,更周全辨证,且具历史和美学的视野。他谙熟小说义理,力图建构一种接近小说本位的艺术观念:既肯定小说的社会历史职能,又重视小说的文本美学价值。
三
虽然接受美学作为学派出自20世纪60年代德国学者尧斯、伊塞尔的倡导,但在此之前,中外学界与文坛并不缺乏采用接受美学的视角来研究文学者。因为在整个文学活动系统中,“存在着至少三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艺术作品的创造问题,它的接受问题和评价问题。诉诸我们审美力的对象,产生于什么环境,包含什么意图,创造者期待它产生什么感受,实际结果如何,在不同时代和地区,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都会阐释这些问题的真正涵义”[7]25.实际上,文学作品是为了读者的阅读而创作的,其功能和作用也只有在接受活动中才能实现。文学的历史效应并非建筑在一种事后的、人为编造出来的“文学事实”的联系之上,而是存在于读者对作品的接受过程之中。
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历史接受现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有言:“明季以来,世目《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为’四大奇书‘,居说部上首。在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虽故发源于前数书,而精神或至正反,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8]195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大行其道之关键,是“义”的化身。这个“义”更多的是江湖义气。施之以恩,报之以德,款之以情,还之以义。这“义”,正是小民们所企求的天地之人道。从百姓的角度,需要仗义正直、扶善反恶的主人公。故那些彰显“正义”的小说作品为何兴盛不衰,就不难理解了。
小说经典总是在过去与现在、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张力关系中存在的。叶楚伧的小说观念具有犀利的接受美学视角。在他的心目中,小说作品既要体现作家创造的特性和意图,又要注重作品对读者的影响和效果。叶楚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剖析了小说作品的创作与接受问题。
第一,小说创作要掌握大众读者的接受心理。叶楚伧深谙大众读者接受心理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认为小说创作之始,作家就要考虑读者接受的两种“心结”:“纯真化”与“通俗化”.就创作风格而言,小说家当中,有追求“纯真”风格的,即“专做正面文章者”;有追求“通俗”风格的,即“专做侧面文章者”.《三国演义》与《说岳全传》,是从真实的历史人物出发创作出来的,一些读者从真实的正面读之,予以欣赏与接受。关羽、岳飞等英雄人物几乎无人不知。《红楼梦》是纯真的正面与通俗的侧面兼顾的作品,但有一些读者弃其侧面,读其正面,贾宝玉、林黛玉成为了历史上反抗封建专制的先驱。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大部分“读者仅能读正面文章”.因此,作家欲影响这些读者,须考虑他们的接受心理。
但是,小说作家又不能局限于“纯真”化,还应走向“通俗”化。《白蛇传》和《三笑》走的是摆脱纯真,追求通俗的路子,虽然作品相当俚俗,但其普及范围非常广泛。现代作家有必要借鉴其创作经验,以解决创作中的“纯真”与“通俗”的关系问题。
在尊重大众读者的欣赏爱好的同时,叶楚伧又反对小说创作一味迁就大众读者的不良现象:
“迷信化”与“谐俗化”.他发现大众读者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即他们虽然崇敬忠贤人物,但往往不能落实到现实生活中,以之为模范;他们虽痛恨奸贼,但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引以为戒。例如,关羽应当为忠勇的模范而得到尊崇,但一般的老百姓爇香祭祀关公,目的是求签算命或拜神祛病。
而且,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公被视为斩妖之法师,甚至被拜为剃头匠的祖师爷。更有甚者,一些老百姓把关公视为月下老人而拜为媒人。这些偏狭的盲目崇拜,都使忠贤主人公陷入离奇、神秘之境地。再如,公众痛恨秦桧等奸臣,铸造了数尊跪状铁像,置于岳坟前,用来示众和谢罪,本当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但现在的一些老百姓抱着嬉闹戏弄的态度,面对铁像,以一泡热尿浇之。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让奸臣受千秋之罚,而是祈求来年之色头(色头与湿头同音)。这些“迷信”与“谐俗”行为,显然起不到应有的健康的社会效果。叶楚伧不免感叹:“作小说即敷陈忠义,铸鼎象奸,穷工竭力,其结果亦不过替社会添几个妖庙邪神耳!”[6]90在很大程度上,大众的接受行为影响着以他们为对象的文学的发展。
“迷信化”与“谐俗化”,属于褊狭的公众心理与接受行为,势必掣肘小说的接受效果。
叶楚伧拈出大众接受心理的负面现象,是为了“平心静气,求一挽救之方”,认为只有抓住“心结”,才能走向“心解”.叶楚伧叩问“心结”,旨在了解与掌握读者复杂的接受心理,注意与警惕“一时谐俗之心”.在小说接受问题上,他强调“勘察一般人之心理而善为之诱导”[6]92.此种观念,关涉小说“俗化”过程中如何“化俗”的重要问题。
叶楚伧的高明之处,在于指出小说创作要追求艺术的本真,以真化俗,化性起伪。当然,叶楚伧既看到大众读者“谐俗之心”的一面,也注意到“读者亦未斯无特长”的一面。他觉得大众读者的长处在于:一是辨别是非能力甚明;二是终身记忆弗忘;三是传播之力迅速。这是他对大众读者的判断力、记忆力、传播力的总体肯定。读者大众的接受心理与小说作品的接受效果有着某种内在联系,“作小说而有志于移风易俗者,当审察国民之优点在,因而鼓舞之;弱点在何处,因而警戒之”[6]92.这样做,无疑会有助于小说家找准作品作用于读者的“穴位”,促进小说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的启蒙教育。
第二,小说接受要探索适当的途径。在小说接受问题上,叶楚伧把小说的接受现状与小说的效果统一起来,探索读者所处的历史社会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价值观、教育素质和道德理想。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引导读者(尤其是学生)阅读小说作品。
民国初期,中国教育会的个别负责人认为一些小说作品“扰乱人心”“败坏风俗”,致函各大报社,禁止刊登这类小说广告。叶楚伧不赞成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禁绝一切的做法,认为与其不准学生看小说,不如从而提倡之,因为假如学生要看小说,学校当局即便想禁止也禁不住。即使禁之于校内,也不能禁之于家中。如果以为学生在校内看小说足以淆乱心志,败坏道德,那么,学生在家中看小说不是会造成同样的结果吗?既然学生读小说之势不能禁绝之,则学校当局不如引导学生正确阅读小说作品,多读中国古典小说和西译小说名着,作为课余消遣,裨益学生的成长。
为此,叶楚伧提出两条途径:一是学校建立读书会,引导学生阅读小说。他回忆自己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时,学校建有读书会,会中所置书籍,新小说占居三分之一以上,杂志占居三分之一,自修课后,学生以会员证借阅,读之津津有味,受益匪浅。二是建立小说鉴赏机制。现今小说作者太多,鱼龙混杂。叶楚伧设想的办法是把小说作为正课加入大学文学系课程当中,培养一批小说研究人才,对中外小说展开积极有效的鉴赏与批评,促使小说事业兴旺发达。
第三,小说阐释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叶楚伧主张建立正确的小说阐释与接受方式。对于《石头记》(《红楼梦》),叶楚伧提出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阐释法,“今世之谈《石头记》者,寻章索义,穿凿附会,乃如汉儒之治经,真足以令人绝倒席上也”.他反对一味稽考本事的“索隐”法,“夫小说之有寄托固也,然不过大旨如此而已。若曰人人有隐名,事事有暗谜,则虽白尽孔夫子头发,亦未必能成。毕竟曹雪芹非圣人,如何有此本领?而今之人评《石头记》,于穿凿之中,又俨然分洛蜀之党,嚣嚣终日,意若甚得,不知非特绝倒席上者有人,即曹雪芹有灵,亦将抚掌大笑,谓’吾始愿不及此矣‘”[6]82.叶楚伧的此种观点,是对当时的红学研究的不满和讽刺,提醒阅读者、阐释者、研究者回归小说本质,不要片面地以“索隐”的眼光看待《红楼梦》。
难能可贵的是,在小说的阐释与接受问题上,叶楚伧凸显了小说的文学本体地位:“是小说,则当以小说读之,此亦天经地义也。一部《石头记》,我只认定是一部《石头记》,不是十三经、二十四史。《石头记》中一人,我只认定是一人,不是别人,既省无数冤枉精神,得无数小说乐趣,而安分守己,不负古人,是何乐而不为?而必鞠躬尽瘁,造无中生有之文,作强派古人之孽哉!”[6]83文学作品是由文本构成的艺术世界,文学的真谛,主要依作品表达的文本形象来论断。叶楚伧认为《红楼梦》中的主人公,是曹雪芹搜集生活素材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出的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而不是作者本人的自传或记事。叶氏这种文学阐释观,不仅对当时的“红学”研究的“自传说”具有纠偏的意义,而且对我们现在一些“红学”专家热衷于索隐猜谜而不能自拔,也有警戒作用。
从接受美学的视域来看,文学创作与读者接受,两者不能分离,它们双向互动,一起支撑整个文学活动的空间与系统。叶楚伧的小说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在中国近代文艺的背景下建构了自己的小说接受之理路。“报业”起家的叶氏,对公众的心理与社会的舆情,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他重视小说的受众,但不是文学上的民粹主义者。
他指出:“作小说而有志于社会,第一宜先审察一般阅者之习惯,投其好以徐徐引导之。”[6]88这种小说观念,辩证地阐释了小说创作与接受的路径。
“投其好”是要满足读者的心理需要与审美爱好;“引导之”是把读者的鉴赏活动引入健康发展的轨道。用今天的话来说,“投其好”是追求“大众化”,“引导之”是趋于“化大众”,两者结合起来,小说事业方能繁荣。叶楚伧所主张的“投其好以徐徐引导之”的小说观,不仅要摸准大众的接受心理,更重要的是,试图为受众提供积极的价值引导。此种小说理论话语,析理精准,义臻圆通。
四
叶楚伧的《小说杂论》迄今未能得到学界的重视,一些研究清末民初的小说理论的学者往往忽略之。原因有二:一是叶楚伧早年属于试图跨越新旧的、温质的“蝙蝠型”文人,后来从政,在政治上又是一个较为复杂的人物。或许是由于党派之争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叶氏被人为地疏漏在近代文学史之外。二是叶氏的小说理论文章,散见于《民国日报》副刊、《小凤杂着》以及《叶楚伧诗文集》之中,需要研究者足音轻叩,吹尽黄沙始得金。笔者以为,在清末民初的众多的“小说话”中,叶楚伧的《小说杂论》,描摹性状,循理力证,谈文说艺,杂而不乱。他对小说的社会功能、小说的历史源流、受众的接受心理、小说的美学技巧、创作的接受效果等问题,均有比较清晰的勘察。负重而不失灵动,耽美而不失隽永。此种小说理论体现出近代市民大众文化的世俗性诉求与文学价值观,这是近代文化思想及其启蒙变革的另一种“现代性”.我们不妨放眼扫描叶楚伧小说理论的时代背景。近代中国小说的勃兴,是文学界的一件大事。
叶楚伧小说理论的出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有着密切的关联。清代末年,朝政日非,国势危殆,人心思变。当时的立宪派或革命党人,试图利用小说作为宣传工具,濬发民智。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杂志,专门刊载小说,其《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把小说视为文学之最上乘,盛赞小说对近世中国社会的改良作用,成为轰动一时的重要论文。梁氏还在《新小说》杂志,特辟“小说丛话”一栏,强调小说的“新民”作用,实际上是把“小说”予以“大说”.小说家吴趼人说:“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着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
清末时期掀起了一股译介域外小说的热潮,而且推动了本土小说的创作。现代学者阿英在《晚清文学丛钞》一书中统计,仅1907年,国内翻译小说就有130种,本土创作的通俗小说有60余种。今人王尔敏剀切地指出:“学界先知之开新倡导刊布小说作品,背后的思想动力来自甲午战争之危亡意识,一致重视启牖民智,促醒民心,决非文家偶然即兴之思想,自是文士反应敏捷,一致同声力倡。” [10]227民初的小说,承接清末“小说界革命”而来。叶楚伧致力于小说创作和理论研究,均受此种文化场域的熏陶。
就全球范围而言,小说的飚兴,亦是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影响读者大众的文化事件。读者大众与小说兴起之间的关系,是中外学界关注的问题。
美国学者瓦特认为小说之所以能在18世纪的英国兴盛起来,当时占优势地位的报刊印刷媒介以及中产阶级的读者大众的欣赏趣味、文化程度、经济能力有着关键性的促进作用。[11]230-235当然,近代中国小说的兴盛,要晚于西方,并受到西方影响,属于一种输入式、后发性的膨胀。今人范伯群指出,近代通俗小说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繁荣滋长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与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12]18.此种概括,非常准确。小说创作与小说理论成为叶楚伧驰骛文坛的篇什,确实与近代都市的崛起、作者与读者队伍的壮大,以及传播网络的推动有关。叶楚伧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学者或士大夫,而是在近代都市生活背景下诞生的、重视“新小说”文体的知识分子。
当然,叶楚伧的小说理论也存在一些局限,例如,理论架构尚嫌粗疏,不够细密,对近代本土小说作品的解析不多。《小说杂论》在文体上属于“小说话”,话语半文半白,体现了近代文化过渡时期的话语特征。但在“小说话”的面影下,叶氏小说理论悄然搏动的是现代的接受意识。叶氏本人熟悉小说创作之道,茹古涵今,吐纳文艺,故能结合时代变迁,较为全面地考察小说的艺术属性,深入捕捉受众的心理和规律。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梁启超、夏曾佑等人的小说理论偏重政治社会学阐释之不足。因此,叶氏的小说理论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张恨水。小说闲评[N].申报,1921-02-12.
[2]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M]//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香港:三联书店,1980.
[3]郑逸梅。南社丛谈 历史与人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4]小凤。小说杂论 十四[N].民国日报,1918-08-16.
[5]黄人。黄人集[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6]叶楚伧。叶楚伧诗文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7]杜夫海纳。当代艺术科学主潮[M].刘应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
[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9]吴趼人。月月小说序[J].月月小说,1906,(创刊号)。
[10]王尔敏。中国近代文运之升降[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1]瓦特。小说的兴起[M].北京:三联书店,1992.
[12]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