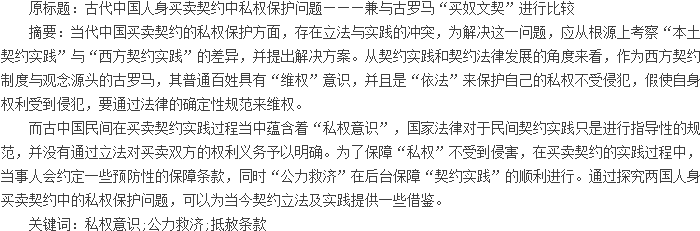
当代中国的契约实践,在立法、司法方面基本移植的是西方的契约制度与观念,这些制度与观念最早源于古罗马。无论是古中国,还是古罗马,其契约制度与观念在发展中融于其本身的文化系统,并在文化的传承中影响至今。所以,当裹挟着古罗马法律文化基因的西方私权保护方式被移植到中国来时,成长于中华文化系统中的中国人觉得陌生,认为与自身私权保护的观念与方式相去甚远。所以,如果在立法、司法实践中忽视本土私权保护的观念与方式,那么,在实践操作中就会遇到障碍,就会出现东西方契约制度与观念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一冲突,应该从根源上考察“本土契约实践”与“古罗马契约实践”的差异,从根本上提出解决方案。人身买卖契约是买卖契约实践的一个方面,通过探究两国人身买卖契约中私权保护的发展脉络及特征,可以为当今契约立法及契约实践提供一些借鉴。
一、人身买卖契约中私权保护语言表述的差异
在古中国,人身买卖契约中私权保护的语言表述,往往强调民间的“私力救济”,并曾出现过“官有政法,人从私契”的套语,最后,又回归到国家公权力指导和保护契约实践,但不干预的状态。当然,这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第一阶段,确定了私有制之后,民间开始具有契约意识。不论贵族、平民,还是奴隶,都能意识到契约文书对自己、对他人行为的约束和影响。同时,因为契约实践而使利益遭受侵害后,会寻求公权力的救济。虽然这部分内容在契约文书当中没有体现,但这确实是国家的一个职能。第二阶段,随着契约实践的增多,百姓的契约观念在逐步提高,在买卖奴婢的过程中出现了违约处罚的条款。这时,在契约实践当中,出现了“私力救济”方式。第三阶段,国家的公权力越来越强大,一方面保障契约实践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却为了其他的目的,开始干预正常的契约秩序。所以,百姓为了维护自己的私权利,开始在契约实践当中增加了抵赦条款,“官有政法,人从私契”的套语出现了。第四阶段,国家公权力退回到指导与保护的角色中。
相比较而言,古罗马的人身买卖契约文书中没有出现“官有政法,人从私契”的套语,而是出现了明显“依法维权”的句式。公元139年的古罗马“买奴文契”就完整记录了这一情况。为了便于说明,原文摘录如下:
买奴文契巴托恩之子马克西姆通过契约从……维尔松之子达齐处以205迪那里为自己购买一个名叫帕西娅或者随便过去叫什么名字的六岁女孩。经证明,该女孩身体健康,无恶习与欺诈,也非逃亡或者流浪者。倘有人从法律上对该女孩或其部分身价提出要求,使巴托恩之子马克西姆或此项财产的所有者不能合法占有之。则须按巴托恩之子马克西姆的要求交付以购买该女孩时的身价,维尔松之子也负有同样的义务。维尔松之子达齐表示,他已从巴托恩之子马克西姆那里收取了购买该女孩的205迪那里。
本契约于高尚的提图斯·埃利乌斯·恺撒·安敦尼与布鲁图斯·普列森图斯执政第二年之3月16日订于卡尔塔。参与签约者:(略)。
古罗马“买奴文契”的诸条款中,权利确认性条款所占比重很大。首先,确认买卖标的———一名六岁的女孩;其次,确认该女孩的自然属性,即身体健康状况、习惯是否良好等;再次,确认该女孩的法律属性,即是否是所有权存在瑕疵的客体。更为重要的是,该条款主要从法律的角度来证明和确认这些权利,比如,“经证明,该女孩无恶习与欺诈”,“倘有人从法律上对该女孩或其部分身价提出要求”,“此项财产的所有者不能合法占有之”。这些材料从一个角度说明,古罗马的普通百姓具有“维权”的意识,并且是“依法”来保证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假使自身权利受到侵犯,也要通过法律这一确定性规范来维权。
从契约时间条款的记录上来看,该契约文书订立于安敦尼王朝第四任皇帝提图斯·埃利乌斯·凯撒·安敦尼执政的第二年,即公元139年,此时国家稳定、社会繁荣,被称之为罗马的黄金时期,奴隶买卖也很频繁。这种频繁的人身买卖发生在普通市民或庄园主之间,其中包涵了古罗马普通百姓的契约实践情况,这种契约实践情况与古罗马法学家的奴隶买卖契约理论相比,更加鲜活,更加直观。将其与古代中国普通百姓的人身买卖契约实践进行比较,更容易找出不同国度、不同背景之下契约观念发展的路径。
二、古中国百姓的“私权意识”
迄今为止,在古代中国人身买卖契约文书中没有见到“从法律上”、“合法占有之”这样的字样,那是否说明,古代中国人在观念层面上没有意识到国家法律能够维护自己的这方面权利呢?答案是否定的。
下面我们看一件周孝王二年,一名叫曶的奴隶主买卖奴隶的契约资料,这份资料订立于公元前883年,较古罗马的这份“买奴文契”早1022年。其主要内容的译文如下:我曾以马一匹,丝一束,交于效父,以订赎汝之奴属五人。汝不从约,许我曰命还马于我。命效父还丝。(即限之臣属。)与效父又约我于王参门改订券契,改用百寽之债以赎该五人之奴隶。并相约如不出五夫,则再相告。并将原金退还。
在这项买卖奴隶的交易过程中,买主曶与卖主限最开始达成了合意。曶以五匹马和一束丝作为对价,欲买属于限的五名奴隶。双方达成合意后,因当时买卖奴隶的交易在公行进行,所以买主在公行的信用担保下,将马与丝交付给了公行之人,但卖主限并未马上交付奴隶,而是毁约,让公行之人把马与丝都还给买主曶。双方又重新选择一个地点,订立了一份契约文书,即要求买主曶改用金属货币来买这五名奴隶。同时,还约定如果限凑不够五名奴隶,不能交付,则再告诉曶,并把曶的金属货币退还给他。在这项奴隶买卖契约文书当中,完全没有提到法律保证的内容。但实际上,在买主曶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曶选择了以公力救济的方式来维权。他找到了法官井叔,井叔是这样解决这件民事争议案件的:限乃王室之人,不应卖约既成而不付。应勿使有贰言。经井叔判定,曶获胜讼,终得购定五人,用羊、酒及丝三寽为贽以招致之。并命败诉者之赠胜诉者之(限之臣属)。以矢五束,即五百矢也。……既败诉,亦自无异词。
买卖契约文书是伴随着买卖行为而出现的,在中国周朝的时候,人们在进行买卖的时候已经习惯将买卖关系进行规范性的记录,如在《周礼》中记载《周官·小宰》的职责时,就有:“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其第六项是“听取予书契”。一旦买卖双方有争议,就可以出示契券文书来理论,如《周官·小宰》的职责“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的第七项就是“听买卖以质剂”。唐代贾公彦,在《疏注》中阐述:“七曰听买卖以质剂者。质剂谓券书,有人争市事者,则以质剂听之”。这说明,在周朝,买卖契约文书在财产所有权的流转过程中起到了保证作用。为了预防在利益驱动面前出现争议,所有的买卖都要立下契约文书。虽然契约文书的用语中没有关于法律保障内容的出现,但实际上国家公权力并不会置之不理,而是会以另外的方式来维护当事人的私权利。
现存较早的,体现人身买卖活动的文献还有一件,即西汉王褒写的《僮约》。这篇文章记录的是他在四川时亲身经历的事,即:蜀郡王子渊,以事到湔,止寡妇杨惠舍。惠有夫时一奴名便了,子渊倩奴行酤酒,便了提大杖上夫冢巅曰:“大夫买便了时,只约守冢,不约为他家男子酤酒也!”子渊大怒曰:“奴宁欲卖邪?”惠曰:“奴大杵人,人无欲者。”子渊即决买,券之。奴复曰:“欲使便了,皆当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为也!”子渊曰:“诺!”
这位名唤“便了”的男子,是寡妇杨慧家的奴隶,因主仆不睦,常有纠纷。这一天王褒去渝上办事,路过杨慧家,打算在她家休息一会儿,就请杨慧家的奴隶便了去买点儿酒来喝。该奴隶不想去,就找了个借口,说我家主人买我时契约文书中没写让我给别人买酒这一项,所以你的这个命令我不能遵守。王褒听了之后很生气,马上问主人杨慧,这个奴隶你卖不?杨慧说,此人不听话,想卖,但没人买。王褒马上就要写买奴隶的契约文书。便了说,你想让我做什么,都得写在文书上,不然,我不承认。王褒马上写了一份买奴契:“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决卖万五千。奴当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
接着明确规定了奴隶必须要做的若干项劳动,以及奴隶不能享受的生活待遇等。最后写道:“奴不听教,当笞一百。”这份契约文书写完后,马上读给便了听,便了无话可说,再也不能狡辩!他使劲儿叩头,并自打耳光。辛酸泪直见滴,清鼻涕长一尺说:“如果真照王大夫说的办,还不如早点进黄土,任凭蚯蚓钻额颅!早知这样,真该替王大夫打酒去,实在不敢恶作剧。”
可见,在普通奴隶的意识中,也存在契约观念,认为契约文书中约定的内容具有约束力。
作为通俗文学作品流传下来的《僮约》,可能并不是王褒真的要买奴隶便了,而只是想教训他一下,或只是针对当时的主仆纠纷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僮约》,除其中所反映的普通奴隶对于契约文书的认识确实值得思考之外,我们还看到,王褒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他写的买奴契约文书,应该是符合当时契约文书结构的。但这份买奴契约文书中丝毫没有提及国家公权力保障的内容,这说明,古中国汉代契约文书结构当中仍然没有提及国家公权力保护问题。那么在现实中,如果所买的奴隶出现了问题,如何处理,老百姓会寻求国家公权力的救济吗,答案是肯定的。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中记载:“告臣:爰书:某里士五(伍)甲缚诣男子丙,告曰:丙,甲臣,桥(骄)悍,不田作,不听田令。谒买(卖)公,斩以为城旦。受贾(价)钱。讯丙,辞曰:甲臣,诚悍,不听甲。甲未赏(尝)身免丙。丙毋(无)病医窬(也),毋(无)它坐罪。令史某诊丙,不病。令少内某、佐某以市正贾(价)贾丙丞某前,丙中人,贾(价)若干钱。”
也就是说,如果奴隶不听话,奴隶主会把他交给国家的某个机关来处理。
汉魏之后的晋也遗留下一份买卖奴隶的契约文书,即“西晋元康(公元290-299年)间石崇买奴券”。在全文前有序曰:“闻谓吾曰:‘吾胡王子,性好读书。公府事一不上券,则不为公府作。’”
可见,在古代中国的早期,契约文书虽然较为粗糙。如,西周的买奴契中根本没有提到所要买的奴隶的名字,汉代的《僮约》和晋石崇的买奴契约文书中压根就没有买奴的价格。但可以明确的是,奴隶已经具有一定的“契约意识”,在其人身关系发生转换时,能够认识到契约文书确定的内容才是值得相信的,才能支配他的行动。同时,普通的百姓也在买卖奴隶的交易过程中特别重视契约文书的效力。虽买卖契约文书当中没有关于“公力救济”内容,但实际上,国家公权力确实在背后起到了保障的作用。
三、古中国契约实践中“私力救济”的发展
自东晋、十六国时期开始,买卖奴隶的契约文书又发生了变化。这些契约文书中,除买卖双方当事人姓名、奴隶的价格等基本要素都齐全之外,开始出现私力救济的用语,如:“罚中氈十四张入不悔者”。
俄藏契约文书当中有一件“前秦建元十三年(公元377年)七月廿五日赵伯龙买婢契”。其全文如下:元十三年廿五日赵伯龙从王念买小幼婢一人,年八,愿贾中行赤氈七张,氈即(毕),婢即过,二主先相和可,乃为券书,成券后,有人仍(认)名及反悔者,罚中氈十四张,入不悔者。民有私约,约当,书券侯买奴,共知本约,沽半。
还有一份南北朝时期北凉承平八年,大概是公元450年,高昌石阿奴的一份卖婢券,其“私力救济”条款如下:若后有呵盗认名,仰本主了,不了,部(倍)还本贾(价)。二主先和后券。券成之后,各不得反悔。悔者,罚丘慈锦七张,入不悔者。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为信。券唯一支,在绍远边。
倩书道护在这两件契约文书当中,都出现了预防性私力救济的条款,一个是“成券后,有人仍(认)名及反悔者,罚中氈十四张,入不悔者。”一个是“若后有呵盗认名,仰本主了,不了,部(倍)还本贾(价)”。这一条款折射出的现象是,当买卖标的物,即奴隶出现所有权瑕疵的时候,第一种解决方案是,依据契约文书预先约定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如果这种方式行不通;第二种解决方案才是寻求国家的公权力救济,虽然这没有写在契约文书当中。而且,对于这种私力救济的方式,预先约定的违约金是带有惩罚性质的,即是双倍返还对价。这说明,从这时开始,契约的功能开始多元化,不仅是记录买卖行为的凭证,而且开始具有了保证功能、惩罚功能,目的是为了保证标的物无瑕疵,避免自身权益受到侵害。
与古代中国的这两件契约文书相比较,古罗马的“买奴文契”当中并没有类似的规定,而且当奴隶的人身权利属性出现瑕疵的时候,也不是惩罚性的罚二倍,只是返还身价就可以了。当然,这份“买奴文契”存在的时间相当于中国的东汉时期,早于古代中国的这两份契约文书,但通过考察罗马法学家的论述,发现他们对于违反买卖契约的行为也要处以罚金,但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数额。如帕比尼安在《问题集》中写道:“当事人约定———未采用要式口约———如果违反此简约则买受人须支付一笔罚金。如果出卖人仅有报复的目的,则不允许其为此简约而提起诉讼。如果出卖人已向他人做出了罚金承诺,且如果买受人不遵守该简约就将使出卖人招致这笔罚金。”
通过比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古中国没有法学家专门来论述与契约有关的法律问题,但是普通民众已将契约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通过预设性的条款予以规范。说明契约观念的发展历程与表现方式因具体地域的不同而不同,也进一步说明,古代中国根植于民间的契约观念能够很好地维护百姓的私权不受侵害。
四、“私力救济”与公权力的博弈
自隋唐以后,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制逐渐加强,同时,社会矛盾也开始加剧。为了笼络民心,国家不定时地颁布赦令,来免除民间的债负,或豁免一定时间段被迫卖身的奴隶。也就是说,国家公权力开始干预民间的契约实践。在契约实践中,买卖契约文书记录着所有权的流转,而所有权本身是完全的、对世性的权利,买卖双方都需要稳定的预期,不能使这种权利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当中。尤其是人身买卖的契约关系,人是有感情的,一旦将权利的归属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不仅会使买卖关系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也会使主仆身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当中,买主的利益将受损。所以,民间的百姓为了避免人身买卖关系当中这种不确定性因素,在契约文书当中会特别约定这方面的预防性条款,即:“有恩赦流行,不在论理之限。”为了便于说明,现列举一件敦煌的契约文书,即:丙子年(公元916年)王阿吴卖儿契。
赤心乡百姓王再盈妻阿吴,为缘夫主早亡,男女岁(岁)小,无人求(救)济,供急(给)依(衣)食,债负深圹(广)。今将福(腹)生儿庆德,柒岁,时丙子年正月廿五日,立契出卖与洪闰乡百姓令狐信通,断作时价干湿共叁拾石。当日交相分付讫,一无玄(悬)欠。其儿庆德自出卖与(以)后,永世一任令狐进通家家仆,不许别人论理。其物所买儿斛斗,亦。或有恩勅流行,亦不在论理之限。官有政法,人从私契。恐后无凭,故立此契,用为后验。
同时期买卖奴隶的契约文书当中,并不是所有契约文书当中都有这类的抵赦条款,如唐朝开元二十年(即公元732年),高昌田元瑜卖婢市券当中就没有类似的语言。为方便考察,举契约文书如下:开元贰拾年捌月日,得田元瑜牒称:“今将胡婢绿珠年拾叁岁,于西州市出卖与女妇薛十五年,得大练肆拾疋。今保见集,谨连元券如前,请改给买人市券者。”准状勘责状同,问口承贱不虚。又责得保人陈希演等五人,欵保上件人婢不是寒良口诱如后虚妄,主保当罪。勘责既同,依给买人市券。
练主用州印婢主田元瑜胡婢绿珠年十三保人瀚海军别奏上柱国陈希演年卅二保人行客赵九思年卅八这份买卖奴婢的契约文书从格式来看,有“用州印”的字样,原件当中也确实有官印存在,而且通过“今保见集,谨连元券如前,请改给买人市券者”的内容,能看出这是一份在集市上经过正规牙行买卖奴婢的官契,在官契当中没有“或遇恩赦流行,亦不在再来论理之限”之类的抵赦条款,这似乎更符合实际情况,毕竟牙行给出的正规市券是不能与国家的法律或皇帝的谕令相违背的。
从元朝开始,国家在颁布赦令的时候,不再干预民间的买卖关系。所以,在民间人身买卖契约文书中不再有“或有恩勅[流]行,亦不在论理之限”的抵赦类条款。为了便于说明,下面举一个明代“卖男契书的格式”:某都某人,今亲生男立名某,年登几岁。为因家贫,日食无借,或因欠少官粮,情愿托中引到某宝,得酌(酬)劳银若干。立契之日,一并交足。本男即听银主抚养成人,与伊婚娶,终身使用。朝夕务要勤谨,不敢闪懒惰。如有此色出,自某支当,跟寻道还。倘有不虞,系即己命。本男的系亲生,并无重宜(叠)、来历不明等事。今欲有凭,立文契并本男手印为照。
既然是“卖男契书的格式”也就是说,在当时进行人身买卖的时候,经常以此为蓝本,因此在民间适用得很广泛。另外,在明代以后,民间的人身买卖契约当中,再也看不到抵赦条款。这说明,古中国民间的私权意识与契约观念在与国家公权力博弈的过程当中,获得了发展空间,国家公权力不再干预民间契约实践,而是充当保护人的角色。
所以从古中国的契约实践和契约法律发展来看,民间的“私权意识”蕴含在买卖契约实践过程当中,国家法律对于民间契约实践只进行指导性的规范,并没有通过立法对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予以明确。为了保障“私权”不受到侵害,在买卖契约的实践过程中,当事人会约定一些预防性的保障条款。
当这些“私力救济”的保障性条款失效,或保障不利的时候,国家公权力会干预,为当事人提供“公力救济”。但是,如果国家的公权力扩张,对契约实践进行了不必要的干预,那么,民间的契约实践会产生抵抗。也就是民间在契约文书当中订立“抵赦”条款,当国家公权力干预无效,则最终会退出干预,从而形成“私权意识”引导“契约实践”,从而培养“契约观念”。另外,“公力救济”在后台保障“契约实践”的顺利进行。所以,古中国与古罗马在人身买卖契约实践的外在表现形式上存在差异,对于争论问题所上升的理论化程度也不同,但解决的是基本相同的问题,取得的都是适应社会且令百姓满意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霍存福.论中国古代契约与国家法的关系[J].当代法学,2005,(1):44-56.
[2]巫宝三.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387.
[3]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乜小红.俄藏敦煌契约文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王启涛.王褒《僮约》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4,(6).
[6][古罗马]优士丁尼.买卖契约[M].刘家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97.





